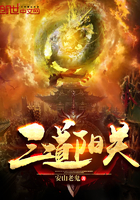离开茶摊,徊鸢前脚迈上马车,李怀瑾后脚就拨开薛值扶着她的手,跟着跳了上去。
徊鸢顺了他一眼,放下已经撩开车帘的手,从另一边跳了下去,自顾牵起马与薛值并行。
于是,吃了瘪的李怀瑾在江沅面无表情地注视下,同样牵了马。
林中有风,树影斑驳,一直在固守县没见到太阳的李怀瑾,有种重见天日的感觉,心情很是美妙,一边骑马一边哼着小曲。
曲折的小路上有踢踏的马蹄声,似在给他的小曲打着拍子,三个沉默的人也因此变得轻松起来。
“江沅,你们殿下的心情一直这样吗?”徊鸢深思着道。
“像这样好的…”江沅想了想,“没有过。”
徊鸢摇头道:“不是说今天这么好,我的意思是他的心情一直这么有病吗?”
江沅嘴角抽了抽。
李怀瑾还像没听见一样,嘴里的小曲正哼的宛转悠扬,飘荡在林子里,好似深林中的被泉水敲打的玉石。
“小小姐,”薛值突然出声,唤回她陷入沉思的思绪,“冗州必定不安生,单凭我们四个人,不好应付。”
一问再次让她又陷进深思中无法自拔。
方清明能买凶杀人,只会再买更多的人。冗州是他管辖的地界,李怀瑾是五皇子,他到了冗州,方清明不敢怠慢。一旦李怀瑾在州府境地出了什么差错,方清明肯定得吃不了兜着走。
但她和薛值呢?
方清明早就看她和她的兄长不顺眼了,一路派来的杀手也都是冲着她二人的。若是李怀瑾真有诚意保她二人自然是最好不过,但以李怀瑾飘忽不定的性子,很难断定。
她能知道他们到冗州会发生什么,唯独不知道李怀瑾下一步会做什么事。这个李怀瑾,是她的盲区。
沉思中,李怀瑾的小曲停了,他的马也慢下来,渐渐与她齐平。
等徊鸢反应过来时,李怀瑾正笑眯眯的满脸宠溺的欣赏她认真的侧脸,她一抬脸对上他认真又泛着光的眼眸,一股灼热感涌上脸颊。
转而暗忖,李怀瑾的这张脸配上他这个性子当真是个祸害!
“徊鸢,当初父皇有意为你我赐婚,我还觉得一个刚及笄的女娃,乳臭未干的没什么意思。”他笑颜如花的对上薛值紧了又紧的眉心,他笑道,“我有点改变主意了呢!”
撕拉一声长枪出鞘,刃如霜冷光乍泄,枪尖直抵李怀瑾脑门。
“别动不动就动刀动枪的,我不想多杀一个人。”李怀瑾两指一捻夹住枪尖。外人虽看不出,但两人分明都在拼着内力。
“那也看你杀不杀得了了。”薛值握着长枪的手紧了三分。
徊鸢十分头疼,拉住马缰将马慢下来,从俩人中间退了出去。她忽然夹紧了马腹,一声轻喝,白马扬长而去。
而那两人,还没松手。
江沅的头也很疼。
“殿下,该走了。”
李怀瑾不听。
“薛副将,人走远了。”
薛值也不听。
江沅也夹紧了马腹,驾马离去。
丛林中仅剩两人时,李怀瑾松了手,薛值收了长枪。
望着徊鸢离去的方向,李怀瑾淡漠道:“功高盖主,是父皇最忧心的。”
赫多一家在父皇在位的后两年里并不顺,他觉得这跟他当初拒绝与赫多家女成婚有很大关系。因为旸乌将军战功赫赫,父皇想要拉拢,适才有了赐婚一说,被皇子拒婚后,虽说错在他,可徊鸢当时的处境也很艰难。
市井里的流言蜚语他见识过,将只是懒散的他传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狗皇帝,便是流言之过了。
他努力回想了一阵子,所有人都以为皇子不愿娶、皇上收回成命就意味着赫多失去盛宠,自那后写赫多家的折子越来越多了,吐旸乌将军口水的也越来越多了。
至于最后怎么处置的,他当初根本没在意。旸乌将军是不是弹劾他的百官之一,他也不知道。
错,就是在此时犯下的。要么改,要么想办法弥补。
薛值冷冷看了他一眼:“就算是六殿下也好,总比五皇子让属下更能接受些。”
“他也就是知道带带兵,哪比我强?”李怀瑾有点怀疑人生。
薛值瞥了他一眼,中肯道:“哪里都强。”
听言,李怀瑾差点被气笑了。:“藐视皇亲是要被杀头的。”
即便如此,他还不是不得不承认,比起李怀琛的兢兢业业、踏实肯干,他确实相差甚远。但对于深宫里与群臣斗智斗勇那一套,李怀琛绝对比不过他。
上辈子落得被人当街打死的下场,并不是因为他傻,只是因为他太喜欢散漫了。
这辈子他已经暗下决心,绝不做闲散之辈,他一定要竭尽全力让李怀琛登上龙座!
思罢,他驾着马匆匆追上去。
望着马蹄绝尘而去,薛值兀的一声长叹。
—————
冗州州府受灾远不及固守县那般严重,几人一路走来,从满地断瓦残垣,到见到个别完整屋子,最后到了州府境地,倒塌的房屋屈指可数。街上人来人往的,丝毫没有受了灾的样子。酒馆照样人满为患,街边的小商小贩依旧卖力吆喝,不管怎么看,都不像是地震后的。
抵达州府境内,已是夜晚。
李怀瑾找了一家看着装潢最富贵、店面最奢华的酒楼,领着江沅进去,朝店家要了间天字号上房,又点了一桌子好酒好菜。
菜一端上来,李怀瑾狗腿地拉徊鸢坐下。但他没坐,徊鸢生怕这人有什么鬼主意不敢坐,半推半就的磨叽了好半天,李怀瑾差点没了耐性,差点又要跟薛值打起来。
最后还是徊鸢颇为识趣,依他的意思坐下来。然后几乎是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双白玉筷挑了一柱子菜放在自己碗里。
“五皇子殿下您这是…”
“自然是给你赔礼道歉,毕竟上辈子我是竭尽全力豁出老脸,生怕娶了你。”当然,这话李怀瑾是绝对不会说出口的。
李怀瑾看她吃了一小口,笑着对她道:“一路来你也着实辛苦,起初你一万个不情愿来找朕,如今,是不是也被朕的节操感动到了,变得这么客气?”
徊鸢一口饭菜毫不留情地喷了出来。
薛值赶紧递上一张方巾给她擦嘴。
李怀瑾脸一黑,什么意思?
“五皇子殿下……确实与传闻中的不太一样。”
李怀瑾点点头,也对,徊鸢若是知道了他当初的寝殿被几十个舞女围得水泄不通的话,绝不会说这种话了。
“我与薛哥哥虽远离都城,可对宫里的事也是时时挂念着的。我们所听所闻,皆是五皇子殿下不分忠奸善恶、纸醉金迷、贪婪好色、嗜杀成性。”
李怀瑾自然是清楚的,生前关于他的传闻多了去了,不是没听过,只是不愿理会罢了。石井街道里都把他传成吃人肉喝人血的大魔头了,流言到了这种地步,不去管反而是连好事。
“那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徊鸢看了看他,沉默地埋头吃饭。意思不言而喻:本小姐懒得说。
李怀瑾不深究,不就是好形象吗?早晚都会有的。比李怀琛比不过,区区副将薛值,他还比不过吗?
“罢了,不说这些了。”李怀瑾又挑了一柱子菜送到她碗里,“你也好些天没好好吃口饭了,多吃点。”
徊鸢无言看着窗外,目光落到来来往往的人群之上。虽说是天灾,眼下的百姓似乎还是很愉悦的。
李怀瑾向她轻轻一瞥,“方清明搜刮地皮,良田无收,理应民不聊生才是?”
“官府贪腐,最受苦的该是百姓,可现在看,冗州的百姓似乎是很幸福的。”
“的确。”李怀瑾赞同道,“冗州不管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大雍最繁华的地方,不过,看似繁荣,却是水深流缓。他们口口声声说的暴政,无非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朝廷让他们缴税,让他们服兵役,是为了强国强兵,他们占着大雍的土地,用着大雍的一草一木,饱了不知衷心于朝廷,饿了却只知道等着朝廷赈灾放粮,不想付出只想着收获,哪有这样的道理。”
徊鸢只得沉默,因为此时他说什么都不对。
李怀瑾太息:“我一开始是如此的想的,可如今又活了一次,到了冗州,才发现许多事情并不如我想的一般。我的苦心他们看不到,离他们最近的州官、县官贪赃枉法,远在都城,谁也看不到。”
他站在窗前,任着行人来去匆匆与他的视线擦肩而过,他只是静静地站着。风中,这样一席落寞沧桑的长衫孑然而立,静止不动。
落花落叶,无声无息,随着秋风的追随,终是化得一地尘埃。
徊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即便对他了解还不深,可他也绝非一言不合就开始失魂落魄之人。一时间她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些繁荣都是表象,王朝已腐,何堪重击。也不知道这样的天下还能撑多久?”李怀瑾一笑,笑的妖妖艳艳的,“凌源送粮,应该快送到了吧?”
终于转移了话题,徊鸢赶紧应他:“算算时辰应该……”
“我之所以换个话题谈起她,不还是因为你完全不会安慰人吗?”李怀瑾斜她一眼,“我都说了这么多伤心话了,你起码也说一句‘你是个好人’吧?”
徊鸢一脸被拆穿后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