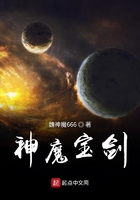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一座村子恰好位于地狱入口。那里的土壤完全不适合种庄稼,矿产也不丰富。因此,村民能够赚取的微薄收入主要来自旅游团,而且仅够勉强维持生计。这里所说的旅游团,可不是身穿夏威夷衫[1]的富裕美国人,也不是咧嘴而笑、看见任何会动的物体都要拍照留念的日本人。因为,像乌兹别克斯坦这种破地方,对那两个国家的人能有什么吸引力呢?我所说的旅游团,是完完全全的本地旅游团。
来自地狱的人长相各异,很难对他们进行准确的总体描述。胖或瘦,留或不留八字须,等等——总之,什么样的都有。如果非要说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行为方式。他们既文雅又礼貌,从不少你一分钱零头,或占你任何便宜。他们从不讨价还价,而且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从不支支吾吾。他们走进店里,问清价格,讲明要不要礼品包装;除此以外,再无废话。他们从不久留,过完一天,就返回地狱。此外,你绝不会看见同一个人两次,因为他们每隔百年才走出地狱一回。情况就是如此。这是规矩。就像在军队,你每隔两周才能休息一个周末;或在担任警卫任务时,你每隔一整个小时才获准坐五分钟。对地狱中的人们来说,也是如此:每隔百年休息一天。就算这事儿真有什么解释,也没人记得了。到目前为止,这更像是一种惯例。
安娜打记事起,就一直在祖父的杂货店干活儿。除本村村民,没有多少顾客光临;但每隔几小时,就会有一个散发着硫黄味的人走进店来,买烟、巧克力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其中一些人会买很可能他们自己从未见过、只是听其他罪人[2]说起过的东西。因此,安娜偶尔会瞧见那些人费劲儿地打开一听可乐,或试图吃下未去除塑料包装的奶酪——诸如此类。有时,安娜会试着和他们搭讪、交朋友,但他们完全听不懂安娜的语言——无论你管那种语言叫乌兹别克语还是别的什么。最后,交流往往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安娜指着自己,说“安娜”;那些人指着他们自己,含糊不清地说“克劳斯”“苏英”“史蒂夫”或“阿维”,然后付钱并匆匆离去。当天傍晚,安娜偶尔会再次瞧见他们:在附近徘徊,或逗留在某个街角,凝望傍晚的天空。但第二天,她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安娜的祖父患了一种会让他整晚睡不到一小时的病。祖父告诉安娜,他总是看见那些人在黎明时,通过他们家前廊旁边的那个洞口返回地下。也正是从他们家前廊上,他瞧见安娜那个极其混蛋的父亲,醉醺醺的,哼着非常龌龊的歌儿,像其他人一样,通过那个洞口,走下地狱。再过九十几年,安娜的父亲应该也会回来,待上一天。
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可以说,那些人是安娜生活中最有趣的部分。她诧异于他们的相貌和奇装异服,会猜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才堕入地狱。因为实际上,那些人的光临,是她生活中唯一值得一提的事。偶尔,在店里感到烦闷时,安娜会想象下一个走进店来的罪人长什么样。她总是想象他们长相很英俊或行为很古怪。每隔几周,她真的会遇见一个长相英俊的魁梧男子,或一个执意不打开罐头就要吃罐头里食物的古怪家伙。接下来的几天,她和祖父会一直谈论这个人。
有一次,店里走进来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安娜知道自己怎么都得和他在一起。他买了白葡萄酒、汽水和各种辛辣调味品。安娜没算东西总共多少钱,只是抓住他的手,把他拉向自己的屋子。那个男人对安娜说的话一个字也听不懂,但仍跟着她往前走。他尽了全力;等两人都意识到他做不到,安娜就抱住他并露出灿烂的微笑,确保他明白这事儿并不重要。但这并没有用,他为此哭了整整一夜。自他离开的那一刻起,安娜每晚都会祈祷,希望他能回来,希望一切顺利。安娜为他祈祷,多过为自己祈祷。安娜把这件事告诉祖父后,祖父笑着夸她心地善良。
两个月后,他回来了。他走进店里,买了一个五香烟熏牛肉三明治。安娜冲他微笑,他也回以微笑。祖父说那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人尽皆知,他们每隔百年才能出来一回;还说这个人肯定是他的双胞胎兄弟或什么人。安娜自己也不完全确定。不管怎样,在两人上床后,一切就真的进展良好了。他似乎很满足,安娜也一样。安娜突然意识到,也许自己并非只在为他一个人祈祷。后来,他走进厨房,找到他上次忘拿的袋子——里面装着苏打水、调味品和葡萄酒。他利用那些原料,为安娜和自己调了一种酒:冒着气泡,喝起来既辣又凉,是酒红色的。那是一种来自地狱的汽酒。
天破晓时,他开始穿衣服,准备离去。安娜叫他别走,但他别无选择似的耸了耸肩。他走后,安娜祈祷他会第三次回来,如果真是他的话;如果不是,那就希望某个酷似他的人会来,来让她犯同样的错误。几周后,安娜开始呕吐。她祈祷自己是怀孕了,但最后证明,只是感染了病毒。大概就在此时,村里的人开始议论纷纷,说那个洞口将从里面关闭。安娜听了非常担心,但祖父说,这只是无聊之人散布的谣言。“没什么可担心的,”祖父笑着对她说,“那个洞口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不管魔鬼还是天使,都绝没有胆量关闭它。”安娜相信祖父的话。但她记得,有天夜里——毫无缘由,甚至不是在睡梦中——她突然感觉到,那个洞口消失了。她只穿着睡衣跑到屋外,却高兴地发现,那个洞口还在。安娜记得,接下来的一刹那,她极度渴望走进洞里去,感觉就像那个洞正在把她吸进去。这或许是因为,她深深地迷恋那个特别的来客;或许也是因为,她真的很想去见见自己那个混蛋父亲;或许更是因为,她不想继续孤独地待在这个无聊的村子里了。她把一边耳朵对着从洞口冒出来的寒气,并勉强听见,从洞的深处隐隐传来人的尖叫声,或流水的声音——究竟是什么声音,难以分辨。那声音离得非常遥远。最后,她回床上睡觉了。几天后,那个洞口真的消失了。地狱仍存在于地下,但再也没人从地狱出来。
自那个洞口消失后,维持生计变得越发困难,生活也变得远比以前乏味和沉寂。祖父去世了,安娜嫁给了鱼贩的儿子,两家店合并成了一家。小两口生下几个孩子;安娜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尤其是关于那些身上散发着硫黄味、走进杂货店的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会吓得孩子们哇哇大哭。然而,安娜会继续往下讲,尽管她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