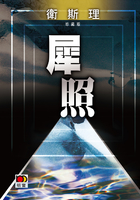我说,我从来都没有跟你们讲过自己的事你怎么知道我过得不开心呢?
父亲还没有说话,正在往鸡的尸体涂盐的母亲说,哎呀这还不明白哪?人老了就精,鬼老了就灵。
我和父亲愣了一下后忍俊不禁。
我说,可是爸爸你今天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
父亲收起了笑容,说,现在电视上又是非典又是战争这些东西,今天这里死了多少人,明天那里又爆炸,你父母都是几十岁的人了,不定哪天说去就去了,你说现在不说以后要是没有机会再说怎么办呢?
父亲说出这样的话令我吓了大跳,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像个二十年前进城的农民一样背着一个异常夸张的大麻袋回到城里来了。一麻袋的亲情像喜马拉雅山一样把我高高地托向云层的深处。
我终于明白到,有些东西会伴你一生一世,谁都无法割舍得掉,譬如亲情;有些东西始终会像天上的风筝一样可望不可及,那条细细的长线明明在自己的手上但你永远也无法知道下一刻风筝会飞向何方,它什么时候会挣脱线的牵扯没入他方,又在什么时候会一头从高高的天际跌向大地,譬如爱情。
从车站出来,我本想马上从出租车回家,但脚步却不听话,拐进了旁边那间音像店,买了一张齐豫的CD。我知道我已经有了再听《走在雨中》的勇气。然后又买了张《阿炳全集》。虽然后来我只听过一次这张《阿炳全集》就把它放在CD架上招惹灰尘,但毕竟我已经拥了一张二胡曲。
小朵倾囊而出也只能拿得出二万元,其中一万元是家里的,一万元是她自己的私房钱。小朵不敢跟娘家人讲马达的事,所以她只好以生意周转为由向大哥借了一万元。她原本是要向大哥借二万元的,但大哥不肯,说他觉得西湖茶庄看上去不像能挣钱的样子所以最多只借一万元。那么,这剩下的七万元,得由我们这些马达的好朋友们来帮他想办法了。我只能把欧阳雪留给我的二万元借给她。把这二万元借给小朵后我自己就只剩下二三千元生活费了。从拥有二万多元一下子降到二千元,我觉得我一下子失去了底气。
当然,如果我有三万或者四万元,我也同样会把所有的钱都借给小朵而令自己变成一个没有底气的人。江维听说我借二万元后也表示可以借同样的数目。江维的经济基础是我们这些人中最好的,但他说他其实是个空壳子,看上去风光其实冷暖自知,他方方面面的花费挺大,前些时候老父亲生病花了了他们兄妹几个每人好几万,孩子还准备送去广州的贵族学校读书还要准备一大笔钱,现在老人还在深切治疗部,还需要用多少钱谁的心里都没有底。小林和小依合起来出一万元。他们说真的是没有钱了,他们的钱本来就不多,过一段时间还要办一件大事要花很多钱。万纤刚刚买了房子,也没什么钱,所以只能拿一万元出来。
算来算去,还差一万元。但也只能是这样了。
我刚刚坐在出租车上就打了个电话给小朵,说我一会就把钱拿过去给她。小朵说她很是过意不去还是她过来取好些。小朵一再坚持她到我家里来取钱,我只好让步了。反正马达不在,去到茶庄也没啥意思。
真没想到我刚刚回到家门外小朵就已经等在那里了,像飞着过来的一样快。我倒是颇觉意外。
小朵看上去有点憔悴。深蓝色的中袖毛线衣配浅蓝色的筒裙,加上脚上那双布鞋令小朵看上去像个可爱的村姑。她身上的玲珑浮凸却是显现得很好,很到位。小朵的身材不错嘛,我想。
小朵一边“咯咯”地笑着一边一样样地帮我把麻袋里的东西放进冰箱。我说,真是没有办法啦,我们家里一对老土的父母养了我这样一个老土的儿了。
有两个装鸡的保鲜袋破了,盐和别的一些什么透过麻袋渗透到我的衣服上来。不知道的时候没什么特别的感觉,知道衣服上有东西后我浑身不自在。小朵说,哎哟,衣服都弄脏了,还有些油腻,赶紧脱下来,用洗洁精来洗。我说好的,我一会就洗。小朵说一会就洗不干净了,快去脱了我来帮你洗。小朵这个贤慧的女人,伺候马达这个大老爷们惯了,以为我也像马达一样是个大老爷们。但她的话里有一股别人无法抗拒的力量。我回到房间换了衣服。
我想起上次万纤到这里来,我换衣服的时候她溜进房间来到我身旁的事后,就想,如果我要跟小朵赤膊上阵,会不会也像上次跟万纤那样出现“婚姻外阳痿”呢?然后轻轻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在心里骂了一句我他妈的猪狗不如。
好久没有和万纤联系了。
换了衣服后我还是能闻到自己身上有一股古怪的味道。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有点神经兮兮的。这味道让我不自在。只好洗澡了。天气还有些凉,洗过澡后,湿湿的头发贴在头上有些不舒服,就用电吹风把头发吹干了还在上面抹了点摩丝。我看到镜子里面是一个精神、干净的我。我对这个时候自己的形象比较满意。但是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把自己弄得马上要到外面去一样。
我挑了一套素色的家庭便装。然后我回到浴室的镜子前。妈的,越看越觉得自己像个知识分子,人模狗样的。
小朵在阳台里洗衣服。她先是用洗洁精把衣服上的油腻洗干净,然后叫我把其他脏衣服也放进洗衣机里一起洗。她说这样洗就不用浪费,不用重复洗两次。
我说,就是我真是个浪费的人。
小朵说,你呀,有时候像个孩子一样,真是要找个人来照顾你才行——哦,你穿得这么漂亮?
我一时糊涂,又要犯贱。我说,小朵你来照顾我就好了,我不要别人的照顾。我没有喊她嫂子而是喊她的名字。我知道她是好朋友马达的女人,但我还是有点克制不住。后来我回忆起这些的时候把这个责任推到了母亲的身上,是她在这几天里让我吃了太多营养丰富的食物,使我精力旺盛,本能无限膨胀。
小朵假装生气瞪了我一眼。
小朵这个眼神令我的心荡漾了一下。赶紧收摄心神。却又有些不甘。
越看就越觉得小朵顺眼。憔悴也是美的一种嘛。
我想,或者她是因为男人不在身边的时间太长了才会如此憔悴的吧。
诱惑。我在诱惑小朵。小朵似乎也在诱惑着我。
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近期以来,小朵也像我一样是孤身一个,她也渴望着与人诉说。我似乎肯定了一样在心里盘算着,我想如果她没有这样的心,完全没必要到我这里来的;如果她没有这样的心,她大可以取了钱后马上离去而不必像现在这样留在这里既跟我聊天又帮我洗衣服,一进门我就给了她存折并且告诉了她密码。
我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我不是马达,没有勾引早已经属于别人的女人的经验。但是,有哪个天生是什么都懂的呢,经验和社会经验是一点积攒起来的嘛。我想给小朵讲一个黄段子但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就那么站了几十秒后我佯装到阳台那头去去拿抹布要搞卫生。小朵来抢我手上的抹布让我到屋里坐着,她说这些活她今天包了。我们的手碰到一起了。哦,行了,手既然已经接触了故事就开始了,我顺势捉住她的手不放。我们的呼吸同时变得有些不正常。我们都是老实人,分明知道对方心里的念头却又都不知道如何选择最佳的表达方式,就这么僵在阳台上。洗衣机“呼”的响了一下,开始往外排水了。小朵笑了一下,我也笑了起来。我像个很有勇气的男人一样不由分说把小朵拥入怀抱。小朵的挣扎很轻很轻。我感觉到她身体的饥渴。她的饥渴与我的饥渴相比毫不逊色。小朵曾经当着我和万纤的面说她在这方面的要求并不高,现在看来不甚准确。我想,她那个时候要求不高是因为马达在身边,这些都是唾手可得的。
令我惊奇的是小朵闭着眼睛安静地与我完成了整个过程。从我开始脱她第一件衣服开始,她的眼睛就没有睁开过,也没有发出过任何一点声音。而她的身体,柔弱如水。
还好,这一次进展得很顺利,因为万纤而造成的心理阴影已经成功地被可爱的小朵击败。我有点厚颜无耻地想打个电话给万纤,我有点想跟她重新再来一次。我没有把小朵想象成欧阳雪,更没想象成万纤,小朵就是小朵,一个广东北部的姑娘,一个四岁小孩的母亲,我好朋友马达的妻子。
休息了一会后,我又要了一次。很久没有这么畅快淋漓过了。第一次的动作粗暴而狂野,第二次讲究了策略和技巧。小朵对我的表现不予评价,但我能感觉到她是很满意的。我想,这段时间以后,她的孤独比我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身体的孤独,灵魂的孤独。
后来,我再度跟小朵在一起的时候,在半真半假的情意绵绵之后我问过她为什么享受人生无尽乐趣时为什么要闭着眼睛,她说,人家跟你还不是很熟嘛。再就不肯多说了。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在后来的几次里,她跟我已经是熟能生巧了还是跟第一次一样闭着眼睛不肯睁开。我又说,那你跟马达在一起时也这样吗?小朵打了我一下,说,讨厌,你提他干嘛?你自己呢?你跟欧阳雪在一起的时候也这样大白天也要这个吗?我哑然失笑,真是一个机锋暗藏的女人啊。
小朵到洗手间里梳理了一下头发,整理了一下衣服就自行回茶庄了。我说要送她回去她却不让,还略带幽默地扬起手中的我刚才交给也的存折说,我现在都是有钱人了,未必还没钱打车?
我到洗手间里准备洗澡。虽然一个小时前我才冲洗过自己的身体。
洗脸盆旁边的电吹风还连着电线。一个小时前,我心里不停地在犹豫不决中盘算着如何把小朵摆平,忘记了把插头插掉。一个小时前,我心里七上八落,一个小时之后心旷神怡。突然我想起了江维,我不愿意作这样的猜测,但还是猜测了。在以后,只要单独跟小朵在一起,我就很想问她拿钱去给江维让他去帮她活动时,是否也跟江维胡搅一通。我真的是很想知道答案,但又开不了口。我想,还好我没有问,若我问了,我会看不起自己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发觉,我其实并不了解以前一直都了解的朋友,譬如小朵,譬如江维。我都认识江维快十年了,才发觉自己对他的了解仅仅限于他在哪里上班,他的家在哪里这些,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完全不知道。
小朵告诉我,这余下的一万元后来江维认领了,即江维一个人出了三万块。江维说,他实在是希望马达能早日出来,就跟老婆商量多出一万元。我想告诉小朵,就算是多拿五万块钱出来江维这个家伙也是有的,问题是他愿意不愿意。我没有讲是因为觉得江维就算一分钱都不肯借给小朵也在情理之中,谁知道这借出去的钱什么时候能要得回来呢,现在因为借钱而令到朋友反目成仇甚至告上法庭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手刚刚接触到电吹风就被打开了。是电线湿了,漏电。我吓了一大跳,手指有种发麻的感觉。还好,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洗澡,脚下的地是干的,我拖鞋和脚都是干的。
我心里有那么一点不安,毕竟那是我好朋友的妻子,更为要命的是我的好朋友现在失去了自由。然后,数月以来孤独的身体得到满足后的喜悦冲淡了这一切。我任由微热的水从脖子上面滑落,温水去到脚下已经变冷。随着清洗过我肮脏身体的水没入下水道的还有我的压抑,一部分的压抑。
我没有就这个问题多想,也没有对自己进行道德评判,我没有这样的习惯,再说,这样的事,又有谁能分得出一个对错呢?如果我一定要给自己的行为画上一个符号,那我就显得太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