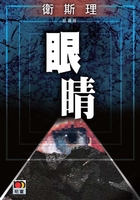我没有和万纤去她的新家,我实在是有些懒。吃完饭后,万纤跟我回家,找到以前那些设计师的名片,打电话帮她约了两个我印象好的就算完成了任务。万纤正准备把几个设计师的资料抄下来,我把所有的资料往她手里一塞说都拿去吧,我留着这些也没什么作用。要是上次搞卫生想起这些,我早就都当垃圾扔掉了。
万纤可以回家去了,可是她还是坐在那里不动。
我说万纤你还不回家,我想睡觉呢。万纤说,四方我发觉你变了很多,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情味了。我说是吗?可是我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善良了。
你看了我的那几个小说了吗?万纤问。
我说看了,挺好,写得挺好。说实话,万纤交给我看的四个小说,两个短篇,两个中篇,都是行货,非常普通,可能是她做报社的编辑时间太长了,写出来的文字也变得很报纸化。
但你总得给我提个有实质意义的意见吧?万纤显得有些恼火。
我说,这样说吧,你的文字太一本正经,太直白了些,语言平实,不故作高深,看起来不累人,但总的来说太准确了些,用词过于直接、准确,有点像在写散文,甚至有些像写政府报告。
哦。万纤作沉思状,说,请继续发表意见。
我有些无奈,说,比如说吧,你写到那个妓女的时候,说她把自己弄得浓妆艳抹,说嫖客没选择她,在老鸠的强力推销下仍然不选择她。我觉得你这样写有些酸,也太正常了,这是大多数嫖客的选择标准呀,你这样写好像欠缺了点新意。所以我觉得你不妨写得俏皮一点,你说那个嫖客说“我不喜欢她,因为她的屁股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屁股”不就行了吗?你何必用那么多的话去描写一个嫖客的心理活动。
万纤说,我没有去嫖过嘛。
我说,真是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太好为人师表了,一个不留意,又在我自己的家中班门弄斧了。
万纤却还不放过我,她说,你看寄给哪家杂志好?
我说,随便哪家吧,你找几本杂志来看看,觉得哪本杂志合适就寄给哪一本吧。
你能帮我推荐一下吗?
我说,我?万纤你不要笑话我了吧,我算老几?再说,我确实是认识几个编辑,但都是泛泛之交。
你总有些关系不错的编辑朋友吧?
要说关系比较好的只有几个杂志社的编辑,《十月》《当代》《青年文学》《长江文艺》《中国铁路文学》和《佛山文艺》的,前几本杂志,你的小说跟他们风格相差太远,《佛山文艺》的编辑你跟他们的关系好像也是很好的……
万纤还未等我说完就笑了,说,四方你真圆滑,好吧,不帮就不帮吧,还是我自己来把这个事情搞惦。现在呀,什么事情都得靠自己最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我说,万纤看你说到哪里去了!
不说这事了,说点别的吧。你真不知道马达出事了?
我说我天天像蜗牛一样躲在家里当然不知道——怎么,刚才你说你不知道是装的?
万纤说这个当然,这事说起来,跟我还是有点关系的——以后我的日子可就难过喽,都是马达这个不长进的狗东西害的!
我打断了万纤的话,说,万纤你等等再说,我先换衣服。我刚才老是觉得不自在,原来是还穿着一本正经的衣服,连脚上的皮鞋还没有换成舒服的布拖鞋。我一个人在家里呆久了,不是不穿衣服就是穿很宽松的休闲服。以前,欧阳雪就经常说我做人太挑剔,出门是一套衣服,在家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衣服,连内衣裤也要家里家外有区别。
我回到房间换衣服。房门没关,虚掩着。
万纤出现在我的身后,悄无声息。我不知道她已经进来了,连内裤也脱了。万纤从背后抱着我。我像触了电一样全身肌肉一下子突然收紧。我不笨,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也知道将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万纤的身体贴在我的背后。我没有动。我的内心一片空白。生殖器绷直如满弦之箭。
我转过身来,吻万纤,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幻觉,以为时光倒流,我吻着的是欧阳雪。万纤的衣服也全部脱光了,一半是我脱的,另一半是她自己脱的。吻了老半天,相互摸了老半天,前戏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是差不多了,我俩相拥着慢慢向着床的方向移去,比较默契,双方都是老手,双方都全情投入。万纤突然把我推开,说,等一下。我像梦游的人一下被惊醒了一样呆在当地,我突然知道了,我眼前的裸体的人是万纤不是欧阳雪。我下意识上了床,把自己藏进厚厚的被子里面,我看到万纤走到窗边,把窗帘拉上。我说,你拉窗帘干什么,又没有人看得见。我住在高高的半空中,从窗户往外望,俯视是一片低矮的屋顶,平视是整块蓝蓝的天,仰视是一片片的白云。万纤说,我怕上帝会看见。说完她还自以为很幽默地看着我笑。她的话实在是多了点儿,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里,她继续说,你跟欧阳雪这样的时候也不拉窗帘吗?
该死的万纤,为啥要提欧阳雪呢?我想,真是无中生有。
万纤终于倒在我的怀中了,一个冰凉的身体。
我却是热情已退。
当欧阳雪变回万纤后,我的热情已经全部退去。万纤吻我,从脸开始,到胸部……当她要吻我的嘴唇时我躲开不让她吻。我仍然是无能为力。
我把自己搞糊涂了。不听话的身体呀真不争气。不过,在我对自己极恼火的同时心底下却又有了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或者,事情本该如此。不过,我没有放弃努力。身体表皮零距离的亲密接触,已经让我无比满足。这横空飞来的艳福。事情的发生得太突然,我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我只是跟着感觉走。两个人都脱得光光的睡在一个被窝里,能轻易就放弃吗?不能呀。我偷偷在心里唱歌,像中学时代时在一个不应该冲动的场合里偏偏冲动了后我会在内心唱歌以放松不让自己出丑时一样,我唱歌,企图令自己变得轻松,重振雄风。
还是不行,最多去到一半,就已经停滞不前。或者是惊鸿一现。我操他妈的。
万纤的失望可想而知。她看着我,眼里写满了同情和不解。她说,你刚才没有喝酒呀。
喝点酒可能更好些。
我有点恨自己,事情本不应该这样的。自从欧阳雪出国后,我每天都渴望着做爱,每天都无法做爱。自从开始跑步后,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好,年轻时的冲动变得越来越持久,越来越不受理性思维的控制,每天清晨从梦中醒来后我都发现自己充血、勃起……我没有办法解决自己对性的要求,是的,我承认在这段长长的时间里,我是性饥渴,自己的双手解决不了我的的性饥渴,每一次自己把自己解决,都伴随着无法原谅自己的恼怒。因为自己把自己解决,伴随着淋漓尽致的痛快之后是长时间的烦躁压抑。三十出头,我已经能客观地面对自己内心最为隐蔽的想法,所以经过多次以自虐为代价的自慰后我明白到,性满足不仅包括发泄,还包括两人之间零距离的肌肤相亲。古人把这个称之为体贴入微。
可是,现在我的身体却不听我的使唤。现在,万纤把我对肌肤的渴望解决了,却撩起我无尽的无法得到满足的兽欲。当真幽默。我把自己和万纤都幽了一默。
万纤说,四方你到底怎么啦?
我也不知道。
以前是不是也这样?
不是,从来都没有试过这样的,我跟欧阳雪在一起的时候很好,双方都很满足。
你没有跟其他女人做过?
没有,自从跟欧阳雪在一起后一次都没有。
可是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万纤不信任地看着我,她一定是认为我真的是不行了。
我也不知道,总之刚才我的脑海里不停地出现欧阳雪的样子……
万纤笑了起来。她说,说起来好像有些玄乎,这种好像叫做婚姻外阳痿。
我大笑。我居然还有心情笑。我笑的时候,万纤的手搭在我那里,一下一下地努力着。可是,她的手像一个虚拟的物件一样我对此毫无反应。但我仍然对她满怀感激,因为她的动作给了我一种舒服的感受。没有反应但却有感觉,这是一种近似于母爱一样的感受。
万纤把所有的被子推开。冷。我说冷。万纤说,让我看看你。我说,你把我的眼镜拿过来,让我也看看你。到了这种时候,我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我只好借用一句周星驰的话来表扬我自己:I服了ME。万纤让我平躺着。我平躺着,双手抱头。万纤的手,轻轻掠过我的脸,脖子,胸部……这个时候,我的内疚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平静,甚至有点好奇,我想知道万纤的表现。现在回想起来,这天的表现多么像情色电影《爱情不是全部》里的一组镜头呀,充满了变数和戏剧性,甚至还带着点黑色幽默。我的胸部有稀稀拉拉几根黑毛,一直向着阴部生长,由上往下,越长越旺盛。万纤说,四方,你其实挺性感的。我说谢谢你的表扬啦,不过今天真是不好意思。万纤的身体,比欧阳雪白一点,但没有欧阳雪结实,欧阳雪的身体的手感好些。妈的,我真是有点不知道羞耻了,越写越原生状态。
万纤说,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我说,你要是说出去我就不活了。
万纤看着我的样子似笑非笑,她大概认为我一直都是阳瘘症患者,她在同情我。管他这么多呢,我心里倒没什么压力,不就是少操一次吗?少操一次又不会死。
终于,万纤趴在我怀里笑。她的身体抖动着。我却不觉得好笑,也没有虚伪或者说是故作大方地笑,我搂着她,说,睡吧,睡会吧,我都累坏了。
万纤说,说会话吧,一会再睡。于是,万纤把马达的事情告诉了我。
万纤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认识了马达、江维。那个时候,江维名气比较大,过的是风光的日子,不像现在这样,过这种死气沉沉的内部刊物主编的生活。那时,万纤还写小说,经常跟马达以文会友。那个时候,在佛山的东北人不多。其中一位是马达,另一位是万纤他们《每日晨报》的副社长老杜——那个时候他还是办公室主任。老杜是行伍出身,转业到地方后进了报社,管行政。万纤介绍马达认识了老杜,从此两个东北人就成了好朋友。
老杜管行政有一手,但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在这种文化单位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是到头了,也无心再往更高的目标发展,于是就把工作之余的精力用在享受生活上了。这老杜偏偏又是个老实人,兴趣和爱好并不多,大不了找几个老乡到马达的茶庄里打打麻将,喝喝功夫茶,找不到人的时候就找马达下几盘象棋。对谁,马达都敢马虎,唯有对这个老乡相当讲究,不管多忙,没有时间也要尽量满足他的老求,不说自从西湖茶庄开张以来,报社的茶叶就全部由西湖茶庄进货这一层,单论亲不亲,故乡人,就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