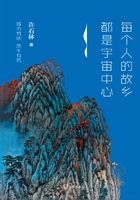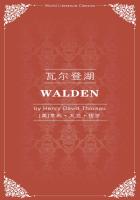童梦弟搬来我家隔壁住的时候,手里托着一盆仙人掌。
我家隔壁,是两间老式平房。门前铺着细细的条砖,砖缝里长草,也冒出一株两株的小黄花。原主人买了新房,搬走了,两间平房,便作了出租用。
初秋的天,薄凉。雨飘得细细密密。砖缝里的小黄花,在雨里瑟瑟。童梦弟却穿着一条超短裙,裸露着修长的双腿。她跟着房主,一路走,一路笑,浑身洋溢着与初秋的雨,颇不协调的欢喜。那份欢喜,如同云罅中的光亮,晶莹剔透。让人的心,忍不住雀跃。
她住下后不久,就来拜访我,送我一盆仙人掌。“我妈说过,邻居好,赛金宝。”她笑,笑得灿若春花。唇红齿白,青春逼人。“姐姐,这个很好长的,你不用怎么理它,它也能长得很好。”她指着仙人掌对我说。她告诉我,她的老家,家家都长这个。哪里碰伤了,用它的汁搽搽就好了。
这便相识了。院门外遇见,她总是脆声声地跟我打招呼,一口一个姐地叫我。脸上,始终如一的,是花开般的笑容。
她做的工作,似乎很杂。我在街上遇见过几次,一次她在路口发传单,怀里搂着一捧彩印的广告。一次她在商场门口,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她又唱又跳的,为商场促销搞宣传。还有一次,我在路边的地摊上碰到她,她在吆喝着卖一些廉价的棉袜子。青春的脸上,挂一抹花开般的笑容。即使在满大街的芜杂之中,那笑容,也没有丢失掉一点点。
童梦弟说:“我想攒多多的钱呢,我要攒钱寄给家里。我还要攒钱买房子,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过一辈子。”这是童梦弟的理想生活,很寻常,亦很动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很熟了。我约她来我家里喝茶,新沏的茉莉花茶。她手里捧一团毛线过来,手指在棒针上,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不停地编织。那是外贸加工的线衣,织一件,可换十五元的手工费。
听她说起她的老家:贵州。深山老沟里。开门看到的全是石疙瘩。能见到土的地方,都被他们开垦出来,种上土豆,种上苞谷。她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三个妹妹。父母盼男孩,给她取名梦弟。她的妹妹分别叫盼弟、招弟、来弟。“名字很俗气,是吧?”她低了头问我,吃吃笑。“不过,我很喜欢,因为,这是我妈给取的。”她复又说。
她的姐姐在12岁上,得病没了。她成了家里最大的孩子,书只念到小学三年级,就回了家。她要带妹妹,要帮父母干活,尽管,她那么喜欢念书。
在她13岁那年,母亲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全身浮肿。家里没钱送母亲去大医院,两个月后,母亲走了。“要是我那时能挣钱,我妈就不会死了。”她说到这里,有些自责,脸上的笑容黯淡下来,好长时间没再言语。唯有十指,在棒针上,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舞得人眼花缭乱。
15岁,她跟了村里人出来打工。做过保姆,在饭店端过盘子,做过化妆品推销员。最穷困潦倒时,她捡过人家丢弃的食物吃,睡过桥洞。她辗转过不少城市,这让她骄傲。“简直就是免费旅游呀。”她笑了,有些得意地晃了晃头。更让她骄傲的是,她挣的钱,不但养活了她的家人,而且还让她的妹妹们都有书读。现在,她最大的妹妹盼弟,已读大二了。“她成绩很好的,也能自己挣钱给自己花了。”日子苦尽甘来,童梦弟显得很知足。
童梦弟唯一的遗憾,是书读得少了。她梦想有一天,能读大学。她买了不少的书,自学。还买了钢笔字帖,练字。有次,她拿了她练的字来给我看,我看到上面写着一首拙朴的小诗,题为《仙人掌不哭泣》:“仙人掌不哭泣/因为泪水对它来说/十分十分珍贵/它要用它浇灌心灵/还要用它滋养身体/好使它卑微的生命/也能开出美丽的花朵。”我好奇地问她:“谁的诗?”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告诉我,是她写的。我惊叹,我说童梦弟,你都可以成为诗人了。她听了很开心,一再向我道谢,仿佛我给了她什么恩赐似的。
这之后,每隔一两天,童梦弟会拿了她的新作来,给我看。那些诗,虽稚嫩,却充满灵气,清新得如同乡村野地里的小野菊。她羞涩地说,她正在学着投稿,等她挣到第一笔稿费,一定请我吃饭。
有一段日子,我很少见到童梦弟。隔壁的门,整日整夜地关着。要不是晾衣绳上,晾着一件她的黑裙子,要不是窗台上,摆放着她长的两盆仙人掌,我会疑心,我的隔壁,根本不曾有人来住过。
再见到童梦弟,秋已深了。平房前,砖缝里的小草和小黄花们,都萎了。她来敲我的门,穿一件绛红色线衣,素妆,笑容恬淡,有点像邻家女孩。她问我有没有葱。她说:“我想学做扬州炒饭呢。”她站在黄昏下,黄昏的金粉,铺她一身。
我问她这些日子去了哪里。她只管抿了嘴笑,后来才告诉我,她和一个人,回了她的老家一趟。
原来,她爱了。之前,她在另一个城,已有一份稳妥的工作。某天,她遇到他,她放弃了好好的工作,从别的城,一路追奔到我们这里来。只因为,他家住在这里。
我给了她一把葱。不一会儿,她端一碗扬州炒饭来,请我尝。我尝一口,赞:“味道真不错,像正宗的扬州炒饭了。”她眼睛亮亮地看着我,欢喜地问:“真的?”
她喜欢的那个人,是最爱吃扬州炒饭的。“他祖上是扬州的呢,他曾祖父,还在扬州做过官呢。”她说起他来,眉眼里,全是笑。
几天后,我看到一个男人,开始出入她的小屋。男人模样一般,举止倒也温厚。他帮童梦弟晒被子,在晾衣绳上,一遍一遍扑打上面的尘。童梦弟则去菜场,买回一堆菜,一头钻进厨房里,忙得油烟四溅。他们隔着一些尘和油烟说话,让人望得见最凡俗的幸福。
转眼,冬了。第一场冬雪降临,总是叫人惊喜的。不过是在眨眼之间,树白了,屋子白了,路白了,整个世界,都白了。人仿佛,也是一个雪白的人了。我找出相机,去叫童梦弟出来一起拍雪景。门敲了许久,童梦弟才来开门,身上裹一件毛毯,凌乱着一头长发。
我一眼瞥见,她的眼窝底,有深深的泪痕。正诧异着准备寻问,她的脸上,早已换上笑容,花开一般的。她说:“姐,你等我一下啊。”转身冲进房内,再出来,她已换了装,上身套一件红色外套,脚上蹬一双红色雪地靴,脸上施了薄粉,长长的头发,挽在脑后。人像一朵红梅了。
我是在一些天后才得知,那时,童梦弟已怀上男人的孩子,而男人,却不能接受她了。男人的父母一直不同意男人与她交往,尽管她做出种种努力。她给他父母织线衣,一件一件,从上衣,织到毛裤。她去他家,小保姆似的,里里外外忙着打扫。隔三岔五的,她会买了他父母爱吃的糕点,送过去。她甚至托父亲,做了贵州特产——熏肉,打包寄过来,让他父母品尝。他们还是不能接纳她,嫌她是外地的,嫌她家穷,嫌她没文凭。男人在父母的安排下,去相亲,很快与一本地女孩开始交往。她选择了放手,关在屋子里,独自疗伤。自始自终,她都没有告诉男人,怀上孩子的事。
腊月底,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一股甜蜜,家家户户都着手准备过新年了。童梦弟来跟我告别,她把窗台上的两盆仙人掌,捧过来给了我。她说她要去别的地方,不会再到这里来了。她说有机会,她很想去读书,走在漂亮的校园里。她说她会活得好好的,找到一个真正喜欢她的人,一起过一辈子。她说这些时,脸上始终挂着花开般的笑容。
我问她:“恨他吗?”她笑着摇摇头,说:“不。就当是我不小心,碰伤了皮,用仙人掌的汁,搽搽就好了。”
新年过后,我隔壁那两间老式平房里,很快搬来新的租客,是一对做生姜生意的年轻夫妇。清晨,他们一起推了拖车,去卖生姜。晚上,他们一起拉着拖车回家,一起做饭,隔着一些尘和油烟,大着嗓门说笑。他们总使我想起童梦弟,她的理想生活,就是这样的。
暮春的一天,童梦弟送我的几盆仙人掌,在不知不觉中,开了花。花粉粉的,重瓣,像微笑着的人的脸。
§§第二辑 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