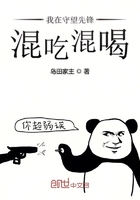我按照酒店的黄页播打了私人医生的电话,大夫来看过,开了些常规的感冒药。
冰箱里空空如也,吧台上都是些冰冷而纯正的烈酒。我嘟了嘟唇,“宁惟汐,你实在矫情得太夸张了!有必要住在这样奢华的酒店里么?还把自己弄得跟不食人间烟火似的!生病了吧?后悔了吧?连热水都没有,怎么吃药?”
他笑得十分无奈,依旧乏力,黑眸却盈熠辉晕,“你这个小丫头,说话永远这么尖刻!”
“我哪一点说错啦?你住在这,谁会知道你生活得好不好?想要把自己藏起来,还找一个这样的‘金屋’,你不是矫情是什么?”我撇了撇嘴,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Kettle(电水壶),灌水通电忙个不停,嘴上毫不留情地一通呛白。
他昔弱地眨了眨眼,目光一直在我面上痴缠,唇上笑意更深,“小笨蛋!‘金屋’是拿来藏‘娇’的!我这里除了你这个‘娇’,真的没什么好藏的啦!”
我飞他一眼,面上暗红轻渡,簇着眉微嗔:“你。。。我才不要藏在这儿,更不想做你的‘娇’。。。”
“为什么不想做我的‘娇’?”他修长的指探出病衾,捉住我冰冷的纤指,低低的叹息,“你以为我想住在这‘活死人墓’里么?我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永远的旅人是没有自己的家的。这房间是宁昭丰他老人家常年包下做‘商务会议室’的,我不过借宿而已。”
“宁昭丰?。。。”我依稀记得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他闲闲一笑,“没错!他是。。我的父亲!而且,住在这,是他的命令!”
“命令!”我摇了摇头,你们这些豪门公子总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父子关系也常常特别得令人大跌眼睛,不过有父亲总胜于无。。。
水,烧开了,沸腾地欢叫着,淹没了我的低叹。
“恶魔导师,吃药啦。”我轻轻托住他的头将枕头垫高。
“青青,”他的黑眸闪了闪,千万柔情纷至沓来。他唇角微扬,透明清浅地笑,眼底掠过一摸做错事的孩童般的心虚“是不是我不吃药,你就不再理我了?”
“嗯?”我歪了歪头,疑惑地睨住他。他为难地轻颦,“我。。。最怕打针吃药了!”
“你不是吧!”我一双本来已经很大的眼睛瞪如铜铃,看他盯着药片的样子果然是十分痛苦,不禁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这不过是几粒小小的药片,又没让你喝苦涩到家的中药,哪有那么可怕?不想吃药,干嘛要生病?你可是我的恶魔导师,为人师表,要以身作则!这么脆弱,怎么搞的嘛!?”
我一手水杯,面上装得出‘小女王’的威仪,“你不吃药,我马上就走!”
“不要!”他眉心纠结,紧张地打断我,赢弱得喘息,慌忙接过我手中的药片以伴以清水服下,小小的药片竟让他眉头大皱,水又灌得太急,他轻声的咳嗽,我柔抚着他的背,直到他慢慢平息下来。
“不要走,不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我。。。”他不依不饶地紧握着我的手,眸中柔丝纷纠碎散。
病中的他依然英俊得令我心悸,高贵优雅中更透出几分庸懒的纤柔,分外我见犹怜。
“我什么都听你的!青,别走!”见我怔仲不语,他纠住眉心十分孩子气推开毛毯,任性地环住了我。
他炽热的气息和柔溺的目光炙烤着我,我呼吸骤紧,全身如火燎,“好,我不走!你,先放开我呀!”
我挣了挣,他纵容自己孩子气的任性将我拥得更紧,仿佛是对我忤逆他的惩罚,他的唇就在我的耳边,他柔到入水即化的声音飘进我的耳廓:“不放!我再也不会放开你了!我放开了你,你会逃,带着我的心逃!”
“导师。。。”
“叫我惟汐!”他的语气中有种温柔的霸道和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