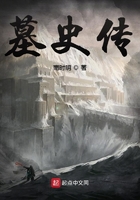萧淳这个手术做得时间很长,原本心外的手术就比其他手术要复杂难做,加上这个病人病情较重,一直到晚上六点段歆知下班,都没有见到萧淳的人。
站在医院门外,想起萧淳那个空荡荡的房子,她实在不想回去,身心俱疲的时候,她害怕再面对无边无际的孤寂。门口的公交站牌有通往学校的,踏上公交车的时候,她的心竟然有一丝的紧张。
握着手机的手心有细细的汗渗出,明知道,手机的主人早已不在,她却失了魂魄一样,忍不住按下熟悉的号码,然后,拨出去。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看似亲和有礼,实则冰冷无情的声音,有条不紊的传来,像零度的冰水混合物一路滚过肺腑,一直到她心脏深处去。
没有任何味道的,只有这彻头彻尾的冰冷绝望,间或还会被尖锐的冰块,划破心脏,然后痛的鲜血直流。侍者过来询问要点什么,她垂眸思考半晌,点了杯曼特宁。
侍者走开,她低头无意识的翻看手机,收件箱里存的,都是张临发给她的短信。一条一条,都刺痛她的心。
“我和你师母一起在杭州,忽然想起来,这是你喜欢的地方。它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所谓断桥目前为止,我只找到一个公交站牌跟它相关。这世上许多东西,只在梦中才会美好。歆知,青春如潮水,固然波涛汹涌动人心魄,却总是轻易的匆匆流逝,不要把自己固守在陈旧的梦里,你长大了,我身边这片天空不属于你,也承载不起。——张老师。”
总是如此,他给她的短信最后,一定会署上这个奇怪的称呼,好像要时时刻刻提醒她,他的身份,让她在想着他的时候,明明白白的知道,他们之间绝无可能。
他以前说,歆知,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在心里思付三四遍才敢出口,只怕哪句说错了,会伤害你。他确实一直都这样小心翼翼的保护她,可是,从一开始,他们不能在一起这件事实,就已经是她心里最致命的伤。
而今,哪怕让她永远别来见他都行,只要他还能活着……
“小姐?”侍者诧异担忧的低唤传来,段歆知才猛然回过神来,眼角有凉冰冰的水状物,正缓慢的爬过脸颊。抬手局促的胡乱擦一下,她急匆匆的拿过侍者托盘里的咖啡,掩饰的一连喝了几大口。
极致的苦涩,在口腔里蔓延,她忍不住紧紧蹙起眉,可是,心里的痛却奇怪的一点点好起来。
“我没事。”段歆知抱着咖啡杯,抬起头朝侍者一笑,侍者神色古怪的看她一眼,便转身走了。而那边咖啡馆的经理,早已发短信告知萧淳她来过这里,以及发生的这些现象。
一直在咖啡馆独坐到夜幕沉沉,她才起身回去。夜晚的公交车,乘客很少,她独自坐在后排,脑袋贴着玻璃,看着外面匆匆闪过的霓虹和法国梧桐,沉闷的压抑的绝望,似潮水一般不断涌来。
离开单纯洁净的校园,才刚接触这社会而已,便已复杂诡异到让她头痛,慌乱无措的境况里,张临也成了她心里无法承担的痛与负荷。所谓祸不单行,大抵是如此——人生和感情的挫折,双重而至。
推开门的时候,萧淳已经在客厅里,只开了昏黄的壁灯,他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听见她回来,也面无表情,连看都不看她,只冷声道:“过来。”
段歆知在离他两米多的地方站住,也懒得去开灯。就着壁灯昏暗的光,粗略的打量了一下,西装外套还没脱,连领带也打得很板正,看上去像是才回来,她抿了抿唇,没有说话。
“去哪儿了?”彼此对峙沉默半晌,他沉声询问,带着不可违逆的压迫。
段歆知眨眨眼,老老实实回答:“学校。”
萧淳冷笑一声,蓦然抬头凝视她,有些昏暗的灯光,他漆黑幽深的双眸,仿佛一双洞悉一切黑暗的探照灯,将她心里的难堪脆弱,照的无所遁形。段歆知的呼吸生生顿住,紧紧吸着气,小心翼翼的看他。
这样的他很可怕,她怕他一怒之下,真的会做出什么伤害张临妻儿的事情。所以,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哪怕是询问也好。
“饮鸩止渴就这么好玩?”他淡淡收回目光,她才松口气,他的一句话,却又准确无误的刺激到她的心,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敲击着膝盖,身体懒懒的靠着沙发,低沉的重复:“说啊,饮鸩止渴好玩么?”
饮鸩止渴,四个字,将她所有的爱恨痴嗔,准确无误的归结,狼狈不堪却无从逃避反驳。
她轻轻扬起头,把快要涌出来的眼泪憋回去。然后,低头淡漠的看着他,轻轻微笑,在晦暗的客厅里,穿着黑色紧身短袖,她就像调皮出逃的精灵,极致的纯洁与妖娆揉合。
“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品评。”咬牙吐出一句话,她便预备转身回房。
才走两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胳膊被一个大力紧紧扯住,他带着恼怒与残忍的气息,快速包围她整个人。下一刻,她便落在他坚硬的怀抱里。
钢铁般的双臂,因为太过用力,让她的胸口被勒得很疼。下意识的拼命挣扎抗拒,可是,他有意的禁锢,岂是势单力薄的她能挣脱的?
“唉……段歆知,”他无奈的叹气声在头顶响起,连名带姓的唤她,她一下子愣住,挣扎的力气也消弱许多,“如果需要一个怀抱痛哭,就不要强撑着,你这样子很难看。”
属于男xing特有的阳刚之气,他霸道而强势的紧紧抱着她,这个怀抱紧的几乎有些喘不过气。可是,却让她觉得莫名的心安,绷紧到极限的情绪,一下子就崩溃了。
就好像摔倒在地的孩子,正艰难努力的想爬起来,忽然看见家长走过来的情形,一下子没了力气,骨子里天生的撒娇因子被激发。辛苦隐忍了一下午的眼泪,以不可阻挡的气势,不断的涌出来,弄湿了他价格昂贵的西装。她很可爱的抓过他的领带,在鼻子上抿了一把。
他就静静的抱着她,任她哭泣,没有阻止的话语,也没有安抚的动作。仿佛,这个怀抱给她,也仅仅是个工具而已。
等到哭够了,他胸前的西装湿了一大片,他冷哼一声,缓缓解开西装的扣子。段歆知一边擦眼泪,一边忐忑局促的抬眼偷偷看他。
“叠整齐装起来,明天让钟点工送去干洗。”将西装扔在沙发上,他就转身进了书房,打开台灯准备看文件。
段歆知暗暗松口气,还好他没有再说什么,不然做了这种丢死人的事情,她真是要无地自容了。痛哭一场,心里好受了一点。拿着西装很细心认真的叠好,装在纸袋里,放到储存脏衣服的柜子里,她才不安的走到书房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