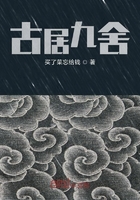我的故事要从很久以前讲起。如果可能,我还想追溯得更远,直到我童年的最初岁月,甚至继续追溯,直到我遥远的祖先。
作家们写小说时,往往乐于封自己为上帝,俯瞰和洞悉整个人类纪事,并像上帝本人那样,透彻而本质地概述一切。这一点,我无法做到。作家们也很少能做到。但我的故事于我,却比任何作家的故事对他们来说都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人的故事——不是虚构的人、可能的人、理想的人,或任何不存在的人,而是一个真实的人、独一无二的人、活生生的人。什么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今人不仅比以往所知更少,今人还大量屠杀这些自然珍贵而独特的造化。假如我们不是极为独特,假如我们中的每个人,都确实能被一颗炮弹从世上彻底清除,那么讲故事就毫无意义。然而每个人又不只是他自己。每个人还是唯一的,特殊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极为重要、值得注意的点。在这个点上,交会着世界的表象,而每次交会,都是仅有的一次,绝不复来。为此,每个人的故事都重要、永恒、神圣。为此,每个人,只要他仍以某种方式活着,只要他履行自然的意志,他就是奇特的,他就配得上任何关注。灵魂在每个人身上成形。造物主在每个人身上受难。救世主在每个人身上被钉上十字架。
今天,很少人知道人为何物。很多人有所感悟,并因此死得从容。正如我,写完我的故事后,也将从容死去。
我不会自封智者。我曾是探寻者,现在仍是探寻者。但我不再去星辰和书籍中探寻,而是开始学习倾听我血液中呼啸的教诲。我的故事并不让人愉快。它不像虚构的故事那般甜美和谐。它有荒谬和迷惘的味道,疯狂和梦境的味道。它的味道,就像那些不再想自我欺骗之人的生活的味道。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条通向自我的路,是在路上的尝试,是狭路上获得的启示。没有一个人能成为完全的自己,但每个人都力争成为自己,都尽其所能,成为昏庸的人,或明智的人。每个人都带着他诞生时的残渣,都背负着史前世界的黏液和蛋壳,直到生命的终点。有些生命永不成人。它是青蛙、蜥蜴、蚂蚁。有些生命上身是人,下身是鱼。但所有生命都是自然朝向人的造化。所有生命都有同样的起源,都来自母亲,来自同样的深渊。每个生命都奋争着,试图从深渊中奔向各自的目标。人们彼此理解,但每个人,都只能解释其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