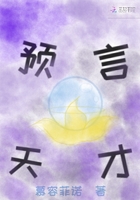靖天城东北方两百里开外有山,名曰天弃。天弃山自东北延伸向西南,与南边的山脉几乎连成一道曲线。连绵起伏的山势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遥遥地将靖天城环抱怀中。
天弃山与南边的天厌山原本应是一体,却是不知为何,在东南角开了一道口。这道口长约两百丈,最宽处不过一丈有余,两边皆是陡峭险峻的断崖。
若是人行于其间,抬头仰望,上方的天空被两侧陡峭的断崖遮挡,只在断崖顶上露出一道光线来。由此一来,这道口又被世人称作一线天。
天弃山与天厌山之间的一线天,乃是成国东部与南部诸城进出靖天城的唯一通道。当然,若是有人不嫌路远,也可绕过南边的天厌山,自靖天城西边进城。
四月的成国晚间算不得多暖和,经过一夜的酝酿,饱和的水汽在空中凝结,形成一片连着一片的雾气,在天弃山与天厌山中四处弥漫。
云雾弥漫间,给群山苍莽,林木叠翠的天弃山与天厌山尽皆蒙上了一层轻纱,远远瞧来,天空与群山似乎凝成了一体。
时辰尚早,四处一片静谧。似乎连原本早起的鸟儿都不忍打破这般静谧,尚且在窝中贪睡。
然而好景不长,一线天外的薄雾中,突的响起一阵“哒哒”的马蹄声。随着这“哒哒”的马蹄声响起的,还有一阵车轮前行的“嘎吱”声。
过得片刻,一匹黑马口鼻之间喷吐着白气缓缓地穿过薄雾,出现在一线天外的谷口。
这黑马马背上坐立一人,此人年纪五十上下,身着一袭灰白长袍,一张平平无奇的脸上纵横着几道伤疤,让原本便不怎的好看的面容,又陡地增添几分狰狞。
中年人虽是其貌不扬,可一双眼睛却是不时闪烁着精光,又给几分狰狞增添一丝凶厉,让人不敢与他直视。
中年人骑马走到谷口,瞧见谷中雾气弥漫,轻轻一扯缰绳,黑马陡停。中年人下得马来,朝后方的薄雾中过去。
后方紧跟过来的几人早已瞧见中年人的动作,下得马来,恭顺地立在马儿身侧。又瞧见中年人过来,齐齐招呼道:“苏统领。”
中年人轻轻颔首,说道:“此处地势险要,尔等小心戒备,切莫大意。”
待几人纷纷应是,中年人方才抬脚,朝后方走去。
后方的薄雾中,几匹马身后是一字排开的马车。这些马车车厢上尽皆挂着一面小旗,旗帜上写就一个“古”字。
中年人越过头前的几驾马车,在当中的一驾马车前停下,抱拳道:“夫人,已至一线峡。谷中雾气弥漫,属下觉着不适合赶路,特来禀报一声。”
片刻后,马车中响起一道女声来,“苏统领辛苦。既是如此,便让下边儿的人好生歇息一阵,待雾气散开后,再走不迟。”
听得此言,苏尘绝抱拳应是,转身又朝前方的薄雾中过去。
苏尘绝刚去不久,这马车后方过来两道身影。走在头前的少女身着一袭白色衣裙,只在袖口绣上一圈紫色花样,瞧来淡雅清新。落在后方的少女,上身着一灰白印花衣裳,下身着一藏青色衣裙,腰间束起一根红色腰带,俨然一副侍女打扮。
马车前方的家奴瞅见白裙少女过来,立马自马车前方下来,恭敬地低下头来,道一声“小姐”。
白裙少女微微一笑,开口道:“忠爷安好。这才赶了半个时辰的路,怎的又停下了?”
不待忠爷答话,马车中却是再度响起那道女声,“梦儿,进来说话。”
白裙少女闻言,小心翼翼爬上马车,掀开帘布钻了进去。片刻后,马车中响起少女撒娇的声音。
“母亲,我已经不小了,您怎的还叫我乳名呀?来之前不都说好了么,在外要叫我闺名。否则,若是被旁人听了去,定会嘲笑于我的。”
马车中,一美妇眉眼带笑,宠溺地伸指在少女鼻头轻轻一刮,说道:“你哪里不小了?即便你往后出嫁了,在母亲心中,也还是那个小女儿。”
少女面上爬起一抹晕红,说道:“我才不嫁呢,我要一辈子陪着母亲过日子。等母亲老了,我便守在母亲身边伺候。您想啊,哪个下人能比女儿更尽心么?有女儿在您身边伺候着,您往后且等着享福吧。”
美妇一个栗子轻轻敲在少女脑门上,引来一阵佯装的痛呼,“胡说,哪有女子家长大了不嫁人的?同你一般年纪的女子,如今儿女都成双了,偏生就你不急。”
瞧见少女噘嘴,美妇继续道:“相过那般多的男子,你都瞧不上眼。此番你既是一再央求,索性等你去了靖天城,再好生相看几人。为娘还真就不信了,偌大的靖天城,便没一个让你瞧得上眼的。”
少女嘴噘得老高,闷闷道:“哪里是女儿瞧不上眼,分明是那些个男子着实不怎的。要么歪瓜裂枣,要么精神萎靡,也不知那些画师得了多少好处,竟是这般弄虚作假。”
美妇闻言,愣得片刻,面上带起一抹疑惑,“你都见过了?”
少女点点头,说道:“倒也没亲眼瞧过,只是让织罗偷偷瞧过一眼,回来同我说了,我便知晓了呀。”
美妇一时哭笑不得,“罢了罢了,既是都瞧不上眼,只好去靖天城瞧瞧了。对了,这些时日累着了吧?”
少女点点头,脑袋一歪,倚在了美妇肩头,“唔,是挺累的。旁的还好,就是有三点不好。”
美妇愕然,“哪三点?”
少女又直起身来,掰着手指头开始数:“第一,这马车太过颠簸,如今女儿浑身骨头都快要散架了,脑袋也有些晕。因此,这是最不好的。第二,这时不时便风餐露宿的,无论是如厕,还是用饭,都不怎的方便。第三。。。”
少女说到这,回头瞧瞧马车前方的帘布,这才扭过头来,掀起裙摆往美妇鼻子凑过去,“母亲您闻,这都馊了。”
美妇微微一愣,笑着一把拍掉少女掀起裙摆的手,“你瞧瞧你,都这般大了,还如此肆意妄为。你若是再不改改这性子,往后去了婆家可是要吃亏的。”
少女讪讪一笑,小声道:“这不是没旁人么?若是有旁人在侧,女儿定会乖乖的,绝不做那失礼之事。”
美妇严肃道:“那也不行。若是成了习惯,往后想改已是来不及的。如今你已是不小,无论身处何地,均得有大家闺秀的样子才成。否则,没得让人笑话咱家门风不严。”
少女见母亲这般严肃,只好应声说道:“知道了,女儿往后定不会再这般恣意行事的,母亲您笑一笑嘛,这般模样怪吓人的。。。”
一线天外有三条官道,分别向东北、正东、东南方向延伸开去。三条官道殊途同归,在一线天外的谷口汇聚。
离着谷口两三里之处,东北方向的官道上有几道身影。仔细一瞧,却是三个人,一匹马。
走在头前的是一匹白马,白马脖颈上挂着一铃铛,随着白马漫不经心的步伐轻轻晃动,不时发出一阵清脆的铃声。
白马马背上坐立一中年男子,此时男子一手轻轻扯住缰绳,直视前方的脑袋却是随着白马前行的步伐,一下接一下地往下轻点。细细瞧来,却见这男子双眼紧闭,像是睡着了一般,端的是奇怪。
白马后方紧跟着一少年,这少年一袭蓝色长袍罩身,虽是未曾像马背上的男子一般紧闭双眼,可那一脸的疲色,显然也并未歇息好。
少年身后跟着一黄裙少女,这少女不时揉揉眼睛,又拍拍脸颊,略微精神了些,却又忍不住捂嘴打了个呵欠。
听得少女呵欠连天的声音,前方的少年许是受了感染,跟着伸手捂嘴,打起呵欠来。一个呵欠打完,少年扭头瞪了一眼少女,说道:“你能不打呵欠么?”
金雨寄瞥离洛一眼,揉揉眼角的水迹,说道:“还说呢,若不是你非要跑林子里烤野兔,又怎会招来那般多的畜生。”
离洛微感错愕,说道:“敢情,还是我的错了?”
金雨寄睡眼惺忪地点点头,道:“可不,我说就在路边寻一地儿歇息,你偏要往林子里跑,说什么安全起见,结果呢?”
离洛有些小尴尬,昨日晚间同往常一般错过了宿头,也就寻了一处山林过夜。用过晚饭后,三人有一句没一句地瞎扯一阵,便倒头就睡。
刚睡没多久,三人就遭到群狼袭击。忙活半天方才将群狼击杀。三人又睡,到得半夜,竟是又来了一头野猪,险些将金雨寄踩伤。
如此一来,这一晚终究是有些折腾,以至于三人醒来后,都有些精神不振。
离洛悻悻道:“往日也是这般过来的,可没遇上这些个畜生。再者说,在林中歇息,总好过在路边被人抹了脖子强吧。畜生来时尚且会招呼你一声,若是遇上歹人,你说对方会招呼你么?”
金雨寄有气无力地嗤笑一声,说道:“就你会瞎想。哪有那般多的歹人,即便是有,也不过是些许小毛贼,本姑娘三招两式也就解决了,哪里用得着这般折腾?”
离洛哂笑不已,“你莫非忘了?前几日某人尚且扮过老妪想要刺杀我,你怎的便知,不会再有那般歹人乔装改扮,再行刺杀之事?若是当真有,只怕到时候,某人来不及惊醒,就已然驾鹤西去。”
金雨寄微微一愣,说道:“这不是某人尚未成功么。你既是有这般修为,这世间又有谁能轻易靠近你?说到底,昨夜那般折腾,都是某人的错。偏生某人天生嘴硬,死不悔改,哼。。。”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是见某人修为不怎的,若是再不好生历练一番,怕是会成累赘。某人不要不识好歹,应当有感恩之心才是。不求某人五体投地,但端茶递水总是应该的吧?”离洛一边走,一边漫不经心说道。
金雨寄轻轻捂住双耳,口中直念叨:“我不听我不听。。。某人是真的烦,先前一声不吭,如今说道起来便没完没了。”
离洛勉强笑笑,不再开口。
。。。
太阳初升,柔和的光线自东方天际洒向世间。随着时间推移,气温渐升,天弃山与天厌山山脚下的薄雾逐渐散去。
薄雾散开,有光线自一线天峡谷上方透了下来,将谷中官道照得明亮起来。
苏尘绝细细瞧得一阵,并未发现有何异常,这才缓缓转身,踱步朝后方的马车过去。
立在方才的马车外,耳听得马车中传来一阵谈话声,苏尘绝等得片刻,不见说话声停歇,只好抱拳打断道:“夫人。”
马车中的谈话声顿止,片刻后,美妇的声音响起,“苏统领,可是薄雾散去了?”
苏尘绝沉声道:“是,薄雾已然散去,只待夫人下令,队伍便能开拔。”
美妇又道:“既是如此,苏统领便头前探路吧。”
苏尘绝抱拳应是,转身大步流星而去。
苏尘绝刚走,美妇的声音又在马车中响起,“梦儿快快回去,队伍立马便要开拔了。”
那少女说道:“能不回去么?女儿尚且想多陪陪母亲呢。”
美妇断然拒绝,“梦儿听话,此处实乃一险境。无事还好,若是突然有了变故,咱也不至于被一锅端掉。听话,赶紧回去吧。”
半晌后,少女才闷闷道:“好吧。母亲且放宽心,有苏统领在,谁来都不怕的。”
片刻后,少女自马车中下来,瞥得一眼名叫织罗的侍女,转身朝后方的马车走去。
美妇又等得半晌,方才开口道:“忠伯,鸣金开拔。”
马车前方的老车夫应声后,自身侧取下一铜锣,“咚咚咚”地连敲三下后,便见前方的马车缓缓动了起来。
苏尘绝作为护院统领,一马当先走在头前。他双眼放着精光,密切注视着周遭的一切动静。他走得并不快,只任由座下的马儿一步一步缓缓踏着步子。
苏尘绝乃是古家耗费颇多培养出来的高手,身负护佑家主安危之职。对于苏尘绝而言,家主在,他在。家主亡,他殉葬。
这一线峡他已随同夫人走过多次,回回都是安然无恙地通过。但即便是如此,他也从未放松过警惕。
走得片刻,前方已然是一线峡中最为狭窄之处,宽不过一丈,仅容一驾马车徐徐通过。
忽而,前方的空中响起一阵“呜呜”的风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快速地落下。
苏尘绝一抬眼,瞧见上方迅速下落的东西,瞳孔陡地放大,厉喝出声:“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