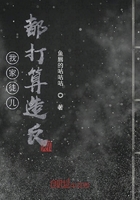砰!
咣当!
哎呦!
后面一片栽倒声,撞头声,兵器落地声,嗷嗷呼痛声。
冷夏终于坐到了凳子上,舒服的喟叹一声,望着房外挺尸的暗卫们,没有分毫愧疚的耸耸肩,她说的是实话,战北烈没有确切的消息传回之前,她的一切推断都只是靠猜,不过这猜测加上两人之间的信任和默契,便上升到了九成的可能。
看着终于爬起来的众人,她再次放出一个炸弹:“若我猜的没错,就在这几日,战北烈就要到了!”
“到了?到哪儿了?”
众人半信半疑的瞅着她,生怕彪悍的小王妃,再变着花样的忽悠他们。
呜——
就在这时,外面远远的传来一声汽笛声。
不待她回答,已经有熟悉的声音从外面大喊着跑进来:“王妃,爷来了!”
唇角缓缓的勾起,冷夏仰起脸看着天空中层云朵朵,红日高升,心间一瞬灿烂了起来,像是枯萎已久的枝条,生出簇簇鲜嫩的绿芽,想着那人就在不远处,想着马上就要相见,那笑开在唇角,越来越明艳。
他来了!
照冷夏所想,他定是伪装重伤之后,单人单骑一路往南,调集了南韩的海军从另一侧北上而来。
一方面以重伤麻痹东方润。
一方面以东祈渡的海军不动麻痹东楚的探子。
一方面奇招突袭,以雷霆凌厉之姿,出现在东楚的渡口!
然而猜测终归是猜测,只有此时,她才真的松了一口气,连续六天干涸的凤眸,终于流出了得知他重伤之后的第一滴泪,欣喜的,幸福的泪。
抹去面颊上的泪珠,冷夏笑望着冲进来的人:“狂风,雷鸣,闪电,好久不见。”
三人亦是激动的瞧着她,重重点头,不知道说啥好了。
啪!
一巴掌拍在脑门上,冷夏无语的瞅着他们,这这这……
这不是哭了吧?
瞧那三双小眼睛,湿润的。
当日,金鳞卫派出百人前往麓州知府江兆林的山中别院,被已经准备埋伏在那里的钟默等两百名暗卫突袭,最后负伤逃走,将消息带回总部的那三个金鳞卫,便是他们。
这一切,不过是他们演的一场戏。
麓州别院豢养私兵,是真的,不过只有两百人,伪造出来了各种上万人训练的动静,引诱金鳞卫上当;而江知府和大秦有所勾结,也是真的,他一家老少全部被绑在府里,任由两百暗卫在那边吃喝演戏,不是勾结是什么?
自然了,被动的。
忽然,冷夏的脑中闪过了什么,她霍然起身:“钟默,带人前往西郊衙门,将曹军医、邓富、邓贵、张荣四人带出,快!”
钟默领命而去。
太后怀疑过邓富,然而查不到任何的线索,可是东方润回来之后,必定会再查,还有曹军医,那夜东方润见过他,虽然喝醉了,但是未必第二日不会有模糊的记忆。
只怪第二天她收到噩耗,巨大的打击之下,整个人的心神完全被这件事占据。
冷夏叹气一声:“只望不要晚了才好。”
东楚,西郊渡口。
天地阔远,碧波汹涌。
漫漫长浪滔滔滚滚,起伏着向岸边逼来,波涛疯狂的拍打着礁石,激荡起雪白的浪花,像是拍打在了东楚百姓的心上,如惊雷炸响,如钟如鼓。
万人空巷,全城百姓闻声赶来,一波一波如楚海浪涛一般向着西郊渡口汇聚,秋风凛冽,带起海洋特有的腥气,清冷而犀利的刮在人的脸上,他们神色惊惶,心间忐忑,震惊的望着千百年来第一次出现在汴荣城下的敌国战船。
远远看去,黑压压的战船从天地间铺陈开来,一排排,一列列,密密麻麻似融入天际的花火,扩大蔓延至整片海域,无穷无尽的晕染开去……
无垠覆盖,几乎看不到边。
数以千计的战船上,大秦的将士身着黑色军服,一个个无声矗立,周身杀气腾腾,气息锋冽!
在他们的最前方,硕大的战船甲板上,一男子临风而立,黑袍翻飞若苍鹰,墨发狂舞如匹练!
他鹰眸俾睨,在阳光下散发着铁血肃杀的锋芒,带着目空一切的凌厉,俯瞰着远方仓皇登上战船的东楚大军,一身顶天立地的霸道气势,如神如魔,望而生畏!
碧海青天,疾风呼啸。
这宛如从天而降一般的黑色战船,在劲风中发出了猎猎声响,似一声声疯狂的咆哮:大秦来了!
以雷霆之姿,来了!
和大秦完全相反的一边,东楚的百姓已经完全的绝望。
他们遥遥望着那天神一样的男人,心中连对侵略者的敌意都升不起,剩下的,只有敬畏。
已经吓的屁滚尿流的东楚战士,终于慌乱的登上了战船,东楚的战船亦是远远的铺陈开,密密麻麻和大秦形成了对峙的状态,甲板上月白衣袍的男子,唇角含笑,发丝飞扬。
天下间并称于世的两个奇男子,终于在此时,遥空对决。
目光相撞,一个锋硬,一个温软。
狭长的眸子中,一抹落寞飞速掠过,东方润叹息:“我还以为……你死了。”
鹰眸一闪,战北烈并不答话。
他也不介意,负手仰望天际,口中继续说着:“我从未赢过你。”
东方润从未像此刻一般,心中升出无力的感觉,两人的交锋从七年前开始,大大小小连他也不知有多少次,看似输赢参半,然而到得最后,五国天下,战北烈占之四分,如今无声无息又雷霆万钧的出现在了东楚之前,这最后的一场大战,结果是什么,他比谁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