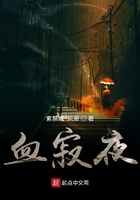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近代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以《人口原理》(1798初版)闻名于世,被称为现代人口理论的先驱者,他的《人口原理》200多年来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最富争议的著作之一。马尔萨斯因该书成名后,他又及时地转向当时英国热门学科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热衷于对当时社会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并与李嘉图等著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多有争论,这使他又跻身于英国当时著名经济学家之列。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英国社会经济状况有密切的关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英国和整个欧洲社会大变革的年代,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实现使英国社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资本积累和财富积聚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人口也在迅速增加。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又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迅速恶化,失业和贫困成为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也促使英国劳动群众反对失业和贫困的斗争日益高涨。维护和反对现存制度的思想斗争日益尖锐化,在英国出现了W。葛德文(1756—1836)等人主张社会改革的著作,而马尔萨斯则以其对立面的姿态登上了英国思想界的舞台。
身世和家庭
马尔萨斯1766年2月13日出生于英国一个小乡村的绅士家庭。其父丹尼尔·马尔萨斯是休谟的朋友,也是卢梭的虔诚的崇拜者,他早年在牛津的女王学院接受教育,但没有取得学位。他在欧洲四处旅行,又遍游英伦全岛,最后在伦敦近郊购置了一处雅宅,被称作燧石门农庄,马尔萨斯就出生于此地。马尔萨斯带来的希望唤起了丹尼尔的爱与雄心,因此决定让他在家中接受教育,由他本人和家庭教师共同教导他。
1784年冬马尔萨斯在家庭教师的引领下,成为剑桥基督学院的一名自费生。马尔萨斯在这里受到他的那些精神伙伴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和诱导。马尔萨斯在该学院的导师威廉·弗伦德以思想自由及坚持和平主义而享誉剑桥,而弗伦德的老师佩利于1775年离开剑桥,不过他的《道德法则与政治哲学》影响深远,这本书对马尔萨斯一定有很大影响。马尔萨斯学习成绩优异,爱好数学并在数学竞赛中获过奖励。1793年12月马尔萨斯成为该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在本科学习和后来学术研究中已经表现出温文尔雅、细心明辨和稳健的风格。马尔萨斯在1788年间已经取得牧师职务,1796年后他就在剑桥和艾尔伯里担任副牧师职务,1803年起任威尔斯比和林克斯的教区长。
马尔萨斯的第一篇文章《危机,一个宪法支持者对最近的有趣的大不列颠的状况的看法》写于1796年,未能发表,但其内容已经表明他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甚至人口问题已经很感兴趣:“在人口问题上,我不能同意阿奇迪肯·佩利的观点,他认为,人口是度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最佳方式。一国幸福与繁荣的增进,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口的增加。如果说人口总数是富裕程度的标志的话,它所代表的也仅是过去的富裕。”
人口论先驱者
1798年,马尔萨斯匿名发表了那本使他享誉世界的小册子:《人口原理: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评戈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这部书的观点是在与其父丹尼尔·马尔萨斯的讨论中逐步形成的。1793年,戈德文的《政治正义》问世。抱有理想主义的父亲对戈德文关于社会改革和进步的思想表示赞同,而儿子则持激烈反对的态度。据《马尔萨斯传》作者毕晓普·奥特说,在与父亲进行的这种富有生气的讨论的时候,马尔萨斯已经确立了他的事业的方向,即主要研究由于人口增长快于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给人类社会进步造成的障碍。在父亲的建议下,马尔萨斯终于将他的观点整理成书,公之于众。
《人口原理》初版是近10万字的8开本,5年后以4开本出了第二版,到第五版时已是25万字的三卷本。马尔萨斯在再版前言中说,初版的写作是出于一时冲动,仅利用了在乡间所能接触到的少量资料,不过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
凯恩斯这样评价《人口原理》第一版和其后各版:“这第一篇论文运用演绎的方法,富于哲理,文风大胆而精于修饰,语言华美,情绪饱满;而在其后的诸版中,政治哲学让位给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被社会学所做的证据归纳所掩盖,这位年轻人在执政政府后期写作时所具有的天赋和高涨热情却不见了。”这不难理解。《人口原理》第一版的主题是人类是否可完善这一类比较抽象的命题,而第二版以后,主题就变成了大多数劳苦大众贫困的根源这类高度敏感的主题了。马尔萨斯所持保守主义的立场注定了其著作的基调必然是悲观、沉闷和消极的。凯恩斯继续评论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作者完全清楚他所表达的思想的重要性。他相信他已找到了人类苦难的线索。《人口原理》的重要性不在于那些新奇的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一个简单的原理,并对这一原理做出极具冲击性的强调,这才是此书的重要性所在……这本书可以跻身于那些对思想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列……”马尔萨斯的朋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代表者李嘉图评价说:“关于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原理》,我在这里有机会表示赞扬,不胜荣幸。反对这部伟大著作的人的攻击只能证明它的力量。我相信它应有的声誉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传播遐迩,因为它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1799年,马尔萨斯为了搜集资料,访问了瑞典、挪威、芬兰和俄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1802年还访问了法国和瑞士。在此期间,马尔萨斯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并于1800年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对目前供应的过高价格的原因的调查》。他没有像李嘉图那样将这种供应价格过高的原因归因于货币数量,而是归因于随着谷物价格上涨而按比例提高教职人员的收入的企图,实际上表达了“有效需求”上涨的结果。
1803年《人口原理》再版,它是精美的4开本,篇幅多达600页。此后该书在作者生前又发行了四版,出版年份依次是1806年、1807年、1815年和1826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由于这部著作的确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
1805年,马尔萨斯担任位于海利贝里的新成立的东印度学院的现代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这是在英格兰建立的最早的政治经济学教席,直到1834年去世。1819年马尔萨斯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21年成为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初始会员。1834年他是伦敦统计学会发起人之一。1833年他被选为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和柏林皇家学会的院士。是“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
《人口原理》在后来的一系列著作中得到引申。1814年出版了关于《谷物法》的小册子《论谷物法的影响》,1815年发表了关于地租的著名论文《地租的性质与发展》,1820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尔萨斯此时从人口理论学家又成为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的主要论著,除了上述《人口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外,还有:《论纸币的贬值》(1811年),《价值的尺度》(1823年),《图克:论物价的高低》(1823年),《政治经济学》(1823年10月至1824年1月),《供给条件》(1825年),《商品的价值》(1827年)和《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等。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交往和友谊
与李嘉图的结识和交往,对马尔萨斯的晚年影响最大。马尔萨斯比李嘉图成名要早,马尔萨斯因1798年《人口原理》而声名鹊起,随后于1805年首任东印度大学海利贝里学院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时,李嘉图还正奔忙于伦敦交易所的股票经纪和投资,或下工夫学习各种知识以弥补早年缺乏正规教育而留下的遗憾,当时的他在英国政治经济学论坛上还是一个无名小辈。
李嘉图对马尔萨斯仰慕已久,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尤其推崇,多年以后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信(1816年6月2日)中还说:“我藏有您旧著的第一版(据研究应是1803年问世的第二版),以前读过,迄今已历多年……我对此书总的印象好极了。理论非常清楚,阐述得非常好,使我感到的兴趣仅次于对亚当·斯密的光辉著作。”
1811年6月,在马尔萨斯的提议下两人初次见面,6月16日,马尔萨斯初次致信李嘉图,他在信中说:“我在愉快地同您认识以后就冒昧地写信给您,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基本上在问题的同一边,所以我们可以进行私人的友好讨论,而不必在出版物上就我们的分歧进行长期论战。”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12年之久的亲密关系和友谊,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他们相互通信多达170多封。其此期间,李嘉图常在周末访问马尔萨斯的住所海利贝里,住在马尔萨斯那里,而马尔萨斯去伦敦时也一定同李嘉图见面,起码也要共进早餐。后来的岁月里,马尔萨斯也习惯于到李嘉图的家中住上几天。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书信的内容范围广泛,然而在一段时期某些问题是主要的。在1811—1812年较早的时期,其通信专门讨论通货和外汇;1815年春季密集的通信是关于地租、利润和谷物价格;1820年和1821年初夏的书信是关于经济停滞的原因和普遍过剩的可能性;1823年的最后一组书信,则是关于重新挑起的有关价值尺度的论证。
在两人的长期交往中,除了人口理论之外,他们在当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有根本的意见分歧,进行过长期尖锐激烈的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由于两人立场的不同甚至对立而愈发显得不同寻常而影响深远。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在研究和表述方法上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李嘉图擅长抽象思维和演绎,而马尔萨斯则偏重于具体描述和经验归纳,他不愿意与可验证的事实依据和直觉偏移太远。有意思的是,李嘉图拥有大地产,却是资本家利益的代表者,马尔萨斯是一介书生,终身从事教育和学术,没有地产,却被视为土地所有者的代言人。
看看他们是怎样看待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1817年1月24日,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信中说:“我觉得我们在常常讨论的一些问题上意见分歧的一项重大原因是:您总是想到一些特殊变动的眼前的和暂时的影响——而我是把这些眼前的和暂时的影响完全丢开,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些变动会产生的长期情况上面。也许您对这些暂时的影响估计过高,而我却过于喜欢低估它们。要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就应该仔细地区别和提及这些影响,承认各有其一定的作用。”
1月26日,马尔萨斯回信说:“我同意您所说的,我们意见分歧的一个原因就是您提到的那个。我确实倾向于往往只看事情的现象,认为只有这个方法可以使自己的著作对社会实际有用,并且我也认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陷入‘拉普塔’岛上的裁缝的错误,以及由于开始时有些微错误而得出的结论距离事实非常之远。此外,我确实认为社会的进展是由一些无规律的运动构成以及不考虑那些在八年或十年内会大大地刺激或者抑制生产和人口的原因,就是忽略国家贫富的原因——政治经济学方面一切研究的主要目的。”诚然,一个作者可以作出自己喜欢的任何假设,但是如果他所假设的东西实际上完全不真实,他就不可能根据自己的假设作出任何切合实际的推理。在您的关于利润的论文中,您假设劳动的实际工资不变;可是,既然实际工资随着商品价格的每一变动而变动(虽然名义上仍然保持原状),而且实际上和利润同样可以变动,您的推理应用于实际情况时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在周围所有的国家里,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国家里看到各个不同程度的繁荣时期有时也有困难时期,但从来没有看到过只有您一个人似乎看到的那种始终一律的发展。“可是,讲到我们意见分歧的一种还要更具体和更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这个。您似乎认为人类的欲望和爱好随时能适应供给;我则坚决认为几乎最困难的事就是激起新的爱好和欲望,尤其是从旧的材料中去激起;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赋予商品的价值,供给越是适合需求,价值就越高,它所能换得的劳动的日数或所能提供的控制力就越多。对外贸易的好处主要地在于它会增加这种价值,而任何一种商品的货币价格降低的损失,凡是不能用数量的相应的增多加以弥补的,都是起因于这样引起的价值总额的减少,或这些价值所能控制的劳动量的减少。我完全认为,实际上真正抑制生产和人口的,与其说是缺乏生产能力,不如说是缺乏刺激。”关于与李嘉图的争论的必要性和意义,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初版,1836年再版)绪论中有一段重要的说明。他说:“我希望能够避免使我的著述具有一种争论的气氛。但是,由于我的目的之一是讨论有分歧的意见,并根据广泛的经验来检查这些意见的真实性,因此要想完全避免争论,显然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一本负有盛誉的现代著作里,有一些根本原理,我深思熟虑之后,认为是错误的。假如这本书我没有特别加以研究,那就是我忽视了写作这部书的才能、著者的崇高权威和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利益。我所指的是李嘉图先生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他接着又说:“我对李嘉图先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才能怀着崇高的评价,对他的绝对忠实和爱真理的态度完全信任。因此我坦率地承认我有时震惊于他的渊博的学识,一方面却仍然不能信服于他的推理……”
长期尖锐激烈的争论并没有使他们疏远,更没有留下怨恨和对立,反而使他们的友谊更加牢固和真挚。诚如美国学者雅各布·霍兰德在《大卫·李嘉图百年评价》中所说:“(这)是精神修养完全不同的两人之间的友谊,”“他们的训练、他们的才能以及他们的同情心,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反的。在讨论时稀有的好脾气和耐心,对于经济分析的共同爱好,在交往方面的完全直率和无私,这些都促使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他还指出:“与马尔萨斯的友谊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通信,即使不是李嘉图在经济思想方面不断产生兴趣的主要原因,至少对他的兴趣所采取的特殊倾向和表现的形式是有影响的。”
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现在,亲爱的马尔萨斯,我完了。像其他争辩者一样,在许多辩论之后,我们仍然保持各自的观点。然而这些辩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你同意我的意见,我也不会比现在更爱你。”李嘉图故去后,马尔萨斯深情地说:“除了我的家人,我从没有像这样爱过他人,交换看法,我们毫不保留,之后我们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只为真理,别无他念,以至于我不得不设想,或早或晚,我们总会取得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