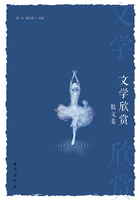《围城》里的董斜川,对苏小姐“一拉手后,正眼不瞧她”,这是因为“他承受老派名士对女人的态度:或者谑浪玩弄,这是对妓女的风流;或者眼观鼻,鼻观心,不敢平视,这是对朋友内眷的礼貌”。这段描写之所以常常使我们忍俊不禁,除了因为它活灵活现地表现了董斜川这位夫子的迂阔之外,还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态度只是出于道德观念的要求的产物,而人的本能的实际却并非如此,因而在其态度与人的本能的实际之间,便形成了某种戏剧性的反讽。
《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第三卷)里的卖油郎,一见花魁娘子后,心里便寻思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他果然说到做到,后来历尽难关,终于如愿以偿。尽管妓女制度早已遭到否定,但他的这种心理活动却仍能博得现代读者的赞赏,因为人们认为他懂得“爱情”,并能积极主动地去赢得“爱情”。或许正因为卖油郎这种心理活动的对象只是妓女,所以人们才能容忍甚至肯定它吧?
但是这种心理活动只要存在,便不会仅仅以妓女为对象,因为社会地位仅是人为的划分,人的本能原本是不管那一套的。于是,当与卖油郎同样的心理活动,针对另外一些对象(诸如别人的内眷)产生时,虽然颇使我们大吃一惊,但其实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第一卷)里的陈商见了三巧儿,肚里便想道:“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侯官县烈女歼仇》(《石点头》第十二卷)里的方六一见了申屠娘子,“偷眼觑看,果然天姿国色。暗想便拚用几万两银子,与他同睡一宿,就死也甘心。”《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一见潘金莲,到家便寻思道:“好一个雌儿,怎能勾得手?”(第二回)
他们在这么寻思的时候,都不是不知道对方是别人的内眷,但是他们不仅像卖油郎这么毫无顾忌地想了,而且几乎都立刻毫不犹豫地将愿望付诸行动了。陈商花钱买通了一个媒婆,经过半年多的惨淡经营,花了不下几千两银子,终于把三巧儿骗上了手;方六一设计让强盗诬扳申屠娘子的丈夫,自己在申屠娘子面前假充好人,终于达到害其夫而娶之的目的(尽管后来被申屠娘子识破机关,落了个全家被杀的结局);西门庆后来与潘金莲通奸,让潘金莲毒死了武大郎,则是众所周知的故事了。
在这些小说中,那些“色胆包天”的男人,当他们“见色起意”的时候,根本不顾什么伦理道德,也丝毫没有什么良心发现,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行动,听凭于自己本能的支配。尽管小说家反复替他们算计利害关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并且设计种种因果报应来吓唬他们,但他们对之却根本不予理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表现出了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精神。“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同上)
在那些男人的心理活动与卖油郎的心理活动之间,其实只有道德意义方面的区别,而其内在精神则是相通的。由于卖油郎心理活动的对象是妓女,所以人们认为是可以容忍的;由于其他男人心理活动的对象是别人的内眷,所以人们认为是不可原谅的。这种不同的评价标准,其实同样是出于道德观念的要求,而不是出于人的本能的要求。董斜川对女人的双重态度,便也正是这同一原因的产物。
但是上述这些小说却向我们表明,人们实际的心理活动,却往往只遵从本能的要求,而非道德观念的要求。因而董斜川对女人的双重态度,便也具有了某种反讽色彩;进而我们对于卖油郎与其他男人的行为的不同评价标准,便也带上了同样的反讽色彩。
我们无意于赞同那些男人的行为,也不是要抹杀他们的行为与卖油郎的行为之间的区别。我们只是想要说明,人的本能的实际,并不像我们的道德观念所要求的那样,也不像董斜川的双重态度所显示的那样,而是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肆无忌惮得多。
我们猜想小说家们是知道这一切的,因为所有以上那些男人的心理活动,其实都有着小说家本人隐秘心理的投影,尽管他们表面上的声音常常对其持非难态度。为了深入了解人性,我们有必要穿过道德观念的迷雾,看清人的本能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