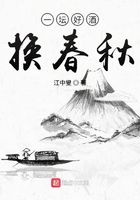景德元年秋,辽国萧太后与皇帝耶律隆绪亲率大军南下侵宋,辽大将萧挞凛破遂城,攻定州,俘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大宋朝野震动,官家赵恒畏敌,欲迁都南逃,被宰相寇准阻止,并力请御驾亲征。无奈之下,赵恒被迫率军北上,倚杨家杨延朗为大将。
十一月,宋辽相峙,辽将萧挞凛攻克祁州,与萧太后会师,后取德清,将澶州三面合围,宋将李继隆死守澶州城。
风已寒,城墙上点点火光跃动,随风而舞。明灭之间,照得值守兵丁人影交错。与秋风相和,宛如鬼蜮,颇有肃杀之感。
城墙走道上,两个巡城武官由远及近,至北城门上止,远望对面连绵数十里的辽军营帐。
其中一人身高七尺八寸,姿颜雄伟,两鬓微霜,身着的铠甲略有些残破,体态魁伟厚重,气质如渊,双目温润内敛,带有几分儒雅。
“贤弟,李将军言官家率军已离此不过百余里,待大军一到,陛下亲征,军士必定士气如虹,我等或可一举击破辽军营寨,趁势北上,燕云光复有望。”声音温和沉敛,带着几分振奋的喜意。
此人正是纵横江湖十数年,武学修为已入绝颠的陈余庆,因其义薄云天,常行侠除恶,武林中多有受其恩义者,又因刀法出神入化,曾以一敌三,斩杀为祸武林多年的邪道成名高手,如同天谴罚恶,故江湖人称“天谴刀”。而今却为心中大义,武举入朝,现职从七品武翼郎。
而陈余庆身边那武官,高七尺有余,亦是雄壮大汉,三十余岁年纪,颚下蓄有短须,脸廓鼻高,双目颇有疲倦之色。
见他轻轻颔首,说道:“确如哥哥所言,我等驻守经年,最是希望伺机北上,如今官家有此决心,甚是振奋人心......”此人名唤张环,官至正八品军巡使。
“咦?”语意未尽,却突然惊疑出声。随后指着对面辽军大营,说道:“哥哥请看那处。”
陈余庆举目望去,只见辽军一将,领着数十骑于阵前由东向西巡视。夜黑风高,距离又相隔甚远,看不太真切,遂运功行气,聚于双目承泣,睛明两穴。再看,竟将那领头辽将的相貌看得分明。
那将脸有虬髯,身壮体健,豹眼微突,隐见太阳穴鼓起,额头顶心微微凹陷,此乃修习烈性内气臻入上境之相。
又看其头顶银冠,上嵌宝石,腰悬宝刀,手提长戟,铠甲式样乃是辽军上将方有资格穿戴;再一看其身旁旗官所举大旗,上书一个“萧”字,旗帜以金线镶边,字旁秀有斗牛图腾。
陈余庆眉头微皱,说道:“此人内气修为不俗,观其衣甲势态,莫非就是萧挞凛?”
张环无甚高深武功,内力不深,虽手搭凉棚,极力眺望,却也不甚清晰,只是说道:“这几日巡城,似常见此标军马在彼处巡视,早晚均有。”
放下眉上之手,使劲眨了一下眼,略作舒缓,复又道:“原以为只是普通斥候,我武艺稀松,无甚修为,不如哥哥看得真切。但若真如哥哥所言,那萧挞凛身为统兵大将,怎会如此托大,远离营盘,亲身巡阵?”
陈余庆略一沉吟,说道:“照常理,不至如此。”
他背着手来回踱了几步,复又停下,转身对张环说道:“据闻萧挞凛生性骄傲,是辽国有数的高手之一,作战勇猛,鲜有败绩。其对我大宋向来轻视,并非不会有此轻率不智之举。”
手托下巴,低头沉吟了一会儿,又说道:“贤弟,这两日你且派斥候队潜伏打探,若此标军马依旧如此,速来报我。”
张环见陈余庆说的郑重,虽有不解之处,却不再多言,欣然领命。
自辽军上一次大举攻城已过数日,期间除了零星斥候间的厮杀,双方都无甚动作,宋军自然是在等皇帝亲征的大军到来;辽军行攻城之事,损失自然不小,亦需修整。
趁着这难得的间隙,澶州守将李继隆命人加紧修筑城墙,囤积火油、檑木、弩箭等守城器械,以备抵挡辽军下一次大规模进攻。
这日,张环挥退身前禀报的军士,出了自身营帐,快步走入陈余庆的营房,对抬头看着自己的陈余庆抱拳一礼,说道:“哥哥,方才斥候来报,两日前你我看见的那标军马,每日早晚均于阵前巡视,领头那将应是萧挞凛无误。”
“好!”陈余庆一拍大腿,有些兴奋的站起身,说道:“贤弟,此乃天赐良机!”
张环虽是武将,看似粗狂,却并非莽撞无谋之辈。闻言有些惊惶的瞪大眼睛,咽了咽口水,说道:“哥哥,你莫不是想......”
随即赶忙拉着陈余庆的手臂,眉头深皱,说道:“哥哥,官家大军将到,何须行此险招?那萧挞凛虽常巡阵,但离敌军大营不到十里,若有异动,辽军快马顷刻便到,若被围住,哥哥武功再高也有覆灭之危,此事万万不可!”
陈余庆似无半点担忧,拍了拍张环的肩膀,将之按到座椅坐下,示意稍安勿躁。又倒了一碗茶递给张环,笑道:“贤弟尽管放心,愚兄并非莽撞之人。
那萧挞凛向来视我大宋无人,又自恃武艺高强,好大喜功;我只需其巡阵时稍加引诱,必会追击,到时其远离营寨,辽军接应不及,正是击杀他的良机!
官家明日便到,若今夜能斩杀萧挞凛这辽军支柱,敌军士气必然低落,而我军却因官家亲征士气高涨。此消彼长之下,到时我大宋定能一战定乾坤,收复燕云,指日可待!”
张环闻言双目一亮,作势起身,尚未站直,却是一顿,复又坐下,摇头道:“不成,不成。那萧挞凛傲则傲矣,却非鲁莽之辈,未必会远追。
且辽营至此相隔不到二十里,快马接应不过一炷香罢了,其又有数十骑护卫,哥哥若要诱敌,为藏身形,至多带一伍斥候队,如此短的时间,便是哥哥也难在诸多护卫中将其斩杀。”
陈余庆摇头笑道:“贤弟此言差矣。按其脾性,我料只要不近澶州城墙二里之地,其必不会有所顾忌。而贤弟你最精通的......是何物?”
张环疑惑的看着陈余庆成竹在胸的笑容,皱着的眉头蓦然一松:“哥哥所言,可是八牛弩?”
陈余庆笑着点了点头,附在张环耳边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通。只见张环的嘴角越咧越高,双眼越来越亮,待陈余庆说完,猛的一拍几案,说道:“走,走,走!你我这就去见李将军!”
说着,便急急忙拉着陈余庆出了营房。此策要成,自然不可能跳开李继隆这澶州的军事主官。
李继隆乃是北宋初期的名将,亦是皇室外戚,宋太宗第三位皇后,明德皇后之兄。为大宋南征北战数十年,战功赫赫,如今已五十余岁。虽伤病缠身,天不假年,却依旧硬撑在前线指挥战斗。
按说习武之人向来体魄健壮,李继隆又非只练外功、硬功的江湖草莽,一身内力修为着实不俗,莫说五十,就是七十岁也当健步如飞,开弓舞槊视之等闲。
然而其多年征战,不仅满身外伤,就是极为严重的内伤也受过多次,甚至阎王殿门口都转过几回。大宋江山说是从这位老人的血里泡出来的亦无不可。
当张环拉着陈余庆求见李继隆,并迫不及待的将斩首之策道出后,以李继隆的能力,自然知道机不可失,当机立断,全力支持陈余庆和张环施行此计。
待吩咐下去之后,白发苍苍的李继隆勉力站起身,微微颤抖着双手,有些激动的对陈余庆行了一礼,说道:“子祝,汝之策若成,燕云十六州便犹如囊中之物。我朝从此便能有养马之地,不消数年,就是除了辽国这一心腹之患亦非难事。此于国朝有扶邦定鼎之功,老朽在此先行谢过。”
话虽如此,可惜在场诸人却忽略了赵宋官家是否有此进取雄心。毕竟,澶州被三面围城之初,这位帝国皇帝第一时间想的可是迁都逃跑。
陈余庆对李继隆素来敬重,岂肯受其一礼。也不见他怎么晃动,身形就出现在李继隆身侧,将他扶住,并搀到座椅处坐下。低声说道:“必不负老将军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