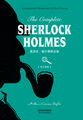安娜·瓦连安特失踪时二十三岁,在加利福尼亚圣拉斐尔的一家老年中心做勤杂工。她来自萨尔瓦多,家人至今还生活在那儿。她勤劳乐观、为人可靠。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六日,她的同事发现她没有到岗,就立刻向警方报告了失踪。
两周之后,她依然下落不明。警方不久便将嫌疑聚焦到三十九岁的格雷戈里奥·门德斯·德利昂身上。他出生于危地马拉,婚后有三个孩子,在马林县卫生区的回收中心当司机。根据回收中心其他人员的描述,他当时和安娜保持着性关系,安娜还怀了他的孩子。
回收中心的摄像机记录了出入中心的车辆,在十二月五日星期二下午四点三十分抓拍到了门德斯·德利昂的车,录像里安娜坐在副驾驶座上。这也让门德斯成了最后一个被目击与安娜在一起的人。不久之后,回收中心的一名挖土机操作员在得知安娜失踪数日,而门德斯·德利昂被认定为“可疑人士”后,主动联系警方坦承他应德利昂的请求——某晚在回收中心的偏远处挖了一个坑。
“案件在这个时候变得有意思起来了。”肯·霍姆斯说。
霍姆斯是马林县的验尸官。当时他已经在这个岗位工作了八年,在验尸所工作了将近三十年。先是当调查员,接着担任助理验尸官。截至二〇〇六年他已经处理了上百起他杀案件和数千起死亡案例。
门德斯·德利昂被带到警局审讯,没问几句,他就立刻自首了。德利昂说,十二月五日天黑后,他和安娜正坐在他的丰田轿车上,车停在圣拉斐尔市区的一家温蒂餐厅前。他们在车上起了争执,他拿出一把小折刀,往安娜的颈部刺去。安娜是个大块头,两百磅的身躯挤在一辆小车里难以抽身,加上门德斯·德利昂的不断袭击,几分钟之后,她就死了。
霍姆斯停了下来,摇了摇头,继续说道:“这类事件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形:一个问题很快变成了两个。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安娜的尸体。凶手知道他必须处理掉尸体,可是要怎么做?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他的车。车的内部,尤其是副驾驶座,沾满了安娜的鲜血。安娜的身躯过于庞大,以至于他必须切断她的双腿才能将她移出车体——这一决定让车内变得更加血腥。”
回收中心离得不远,于是门德斯·德利昂决定去那儿。几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现场,挖土机操作员也尚未离开。门德斯·德利昂说服他给自己在回收中心的后侧挖了一个坑。操作员并不知道所作为何,但他愿意帮德利昂一个忙。待他离开之后,门德斯·德利昂把安娜的双腿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身体的其余部分放在另一个塑料袋里。他巧妙地将两个袋子移到坑里,盖满挖出的土以掩盖一切。然后他开来一辆卡车,在埋尸处来回行驶,把泥土轧实,最后处理掉了轮胎印。
接下来他只需处理掉他的车。这个相对比较容易,他把车开到一个朋友的废车堆积场挤压报废。他和朋友说,他的车没通过尾气检查,所以与其付钱让废车场取车,不如把车挤压后,借一辆小货车把处理后的车体送给收废铁的人。
门德斯·德利昂自首时指认了安娜尸体埋葬的大概区域。当时四下一片漆黑,他并不知道具体的位置。那名挖土机操作员不知道具体位置,也记不清坑有多深。他觉得应该有五英尺深,但并不确定。
警方也在此时传唤了验尸所相关人员,听完详细的情况说明后,霍姆斯就开始了后续工作。
“我们知道要开始挖掘了。”他说道,“我们不得不开始考古式挖掘。如果你知道这里有一具尸体,一开始就得小心翼翼,也就是说要使用小漆刷、汤匙和园丁铲,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尸体埋得有多深。”
多年来,霍姆斯已经和FBI合作过无数起案件,也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只要案件涉及联邦资产或是联邦政府的雇员被杀,或是跨州犯罪,FBI特工就会出动。其他时候,如果当地的特工没有公务缠身,霍姆斯可以针对某个案件寻求帮助,他们也会配合。在这起案件上,霍姆斯接到一通电话说FBI的特殊应变小队——四名具有考古学挖掘专长的特工可以为他提供帮助。霍姆斯之前从来没有和这个特殊小队共事过,他们虽然不驻扎在当地,但是立即接受了这项任务。
特殊小队出现时拖着一辆十六到十八英尺长的厢型拖车。他们一打开拖车的后部,霍姆斯就看得目瞪口呆。
“那简直就是法医界的好市多超市——琳琅满目地放着所有你可以想到的工具,包括为我们每个人提供的蒂维克纤维服,用于标记位置的五颜六色的标志旗,还有弹出式帐篷,用于遮掩坑洞,防止听到风声的记者们乘坐新闻采访直升机在空中盘旋窥探。”
由于不知道确切位置,联邦调查局的小队划出一块六平方英尺的区域,然后用平板锹刮去满是页岩和岩石的泥土。当他们挖到足够深,发现泥土仍没有被破坏的迹象时,就会往下一块坐标方格继续挖掘。
挖掘持续了整整两天,直到他们发现了埋尸点,挖出了距地面五英尺深的袋子。第一天在现场的是霍姆斯的一名调查员达雷尔·哈里斯;第二天在现场的是另一名调查员帕姆·卡特。霍姆斯也几次路过挖掘现场,在两天的挖掘过程中,联邦探员们始终听从验尸所的安排。
“这和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不太一样。”霍姆斯说,“只要联邦调查局一到,就开始清道赶人。实际上他们不会这么做——绝对不会。他们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乐于帮我们做这些事情,因为平时他们没有太多机会接触这些。他们也知道这并不是他们的分内工作,他们只是乐于分享自己的资源和专长。有些人甚至午饭时会为我们订三明治、咖啡或饮料,从来不会让我们掏钱买单。”
开展挖掘工作的时候,警方找到了门德斯·德利昂报废挤压的车。霍姆斯让人把车送到了诺瓦托消防局的一个训练中心,让消防员打开。
“他们以前经手的东西从来没有被这样挤压过。”他说道,“所以把这次实践当作难得的机会。他们还不习惯参与调查凶杀案,这让他们兴奋了一把。”
“救生颚”是一部大型空气压缩分离机,它的液压油缸可以用气压一块一块地分解压碎的物体。在两个半小时里,消防员分离了车门、座椅和地毯,每一部分都沾有血迹。
霍姆斯通过国土安全部的指纹辨识确认了安娜的身份。她虽然没有驾照,但持有有效护照,所以国土安全部的数据库里有她的指纹信息。霍姆斯也让人分析了门德斯·德利昂车里的血迹,结果与安娜·瓦连安特的生物信息相匹配。
据此,门德斯·德利昂被指控谋杀了安娜和她腹中六周大的孩子。由于在加利福尼亚双尸命案可能被判死刑,该案件本身也极有可能罪至极刑。在诉讼期间,第二项谋杀指控没能成立,因为根据加州法律,六周大的孩子还不足以满足“胎儿”的定义。
霍姆斯出庭做证时,门德斯·德利昂突然推翻了他的供认,还将凶案归咎于一名未被确认的第三者。根据他的公设辩护人的辩词,门德斯·德利昂害怕自己在圣昆廷监狱成为攻击目标被杀害。该监狱在马林县,那里监禁着加利福尼亚所有男性死刑犯,和别的监狱一样受帮派控制,门德斯·德利昂自然也要受他们摆布。这些并未得到检控方的关注,然而通过认罪协商,门德斯·德利昂最终被判服刑十六年。
回顾这起案件,霍姆斯露出了困惑的微笑,说道:“这只是验尸所里普通的一天。”他深知这样的事情很难被称作“普通”,但是在这个行业里,“普通”的日子几乎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