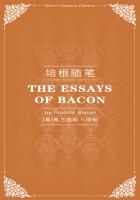客家是移民过程中形成的族群。移民的过程一方面是文化传播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文化融合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体现出文化的族群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客家入川一方面是将原乡文化移植过来,保持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又要融合当地的巴蜀文化,以适应迁居地的社会。正如庄英章先生指出,客家社会文化的特色在于他们和原住民保持密切关系,但是却又维持其原始族群认同,两种不同张力的互相拉锯形成了客家文化。而族群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意识到自己或被意识到其与周围不同,“我们不像他们,他们不像我们”,并具有一定的特征以与其他群体相区别。这些特征包括共同的地理来源、迁移情况、语言或方言、宗教信仰、共有的传统、价值和象征、文字、民间创作和音乐、饮食习惯、居住和职业模式等,对群体内外不同的感觉,因而族群强调的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的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族群认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的基础。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容易形成凝聚力强的群体。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语言、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构成族群认同的要素。
在族群认同中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一切教育目的是保持文化价值,教育是按照文化价值培养文化成员的最佳途径。
四川客家文化认同教育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成都东山客家人以是否说客家话、祖先神位的写法和家族来源作为客家文化认同的三大标志。依据周大鸣关于文化认同要素的理解,笔者以为,客家族群文化认同要素主要指客家方言、族群历史和文化。客家人是通过这三大文化标志的教育来加强自身的文化认同。因而客家文化认同教育具体表现在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 的客家母语教育、移民史教育(家族史教育、祖籍教育和创业教育)以及道德礼俗文化教育等方面,其目的是“修其教不易其俗”,保持族群的文化认同。客家文化作为移植型文化,四川客家文化在保持文化认同方面,客家教育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客家教育为客家文化的认同起了重要作用。四川客家移民注重文化认同教育,是客家“崇文重教”内容的突出表现。因而“崇文重教”保证了客家文化的传承,强化了客家族群的文化认同。
一、四川客家母语教育
四川客家人在远离故土不断地迁徙中,在其他土著民或族群的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为强化族群文化认同,四川客家恪守“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祖训,反映了客家人浓厚的族群意识和强烈的内聚心理,表现了四川客家加强母语教育的努力。
(一)四川人打乡谈
一般看来,在四川,“打乡谈”特指客家话。如《成都风物》杂志专设 “客家乡谈”的栏目,并认为“打乡谈”是至今仍在成都郊区以及内江、温江、绵阳大片地区流行的一种特殊方言。它起源于清代顺治、康熙年间,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中通用。现在这种方言不少语言、词汇、句型仍与广东客家话相通,所以有的地方史料又称“打乡谈”为“客家话”。
“打乡谈”是专指“客家话”吗?其实,“打乡谈”是移民社会普遍的文化现象。四川乡谈的形成与清前期的移民直接相关。即“乡市习俗,异区而殊,究厥要因,端在祖籍”。从清初“湖广填四川”看,四川的移民涉及湖北、湖南、广东、云南、贵州、江西、陕西、安徽、山东、广西、福建、山西、甘肃等10多个省,各省移民带来自己的乡谈土语。四川移民中的乡谈汇聚了各省的方言,几乎包括了北方话、广东话、江浙话、福建话、湖南话、江西话、客家话等汉语的七大方言。清朝前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初期,各省移民同籍而居、聚族而居现象十分突出,因而在相当一段时期,四川移民在说“普通话”(指四川话)的同时,仍保留着原籍的乡音,如安县“前清时,县属民皆由各省客民占籍,声音多从其本俗。同一意义之俗语,各处发音不同。有所谓广东腔者,有所谓陕西腔者,有所谓湖广宝庆腔者、永州腔者,音皆多浊”。乐至县“今中具五民,虽占籍二百年,操土音而循故俗,从宜异习,纠纷不能齐者,其势然也”。大竹“五省人之原籍不同,五省人之乡谈亦各自不同”。各省移民都讲自己的家乡话,即“打乡谈”。如宣汉县“凡本籍与本籍者遇,必述其原籍之土语,曰‘打乡谈’,一以验真伪,一以必亲切也,且父子兄弟相互传习,以为纪念”。大足“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各从其俗。本县语言,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操两种语言: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交谈,曰‘打乡谈’;与外人交接则用普通话(四川官话),远近无殊”。因此,“打乡谈”指四川移民讲原籍各自的方言土语,而不单指客家话。
乡谈不同称谓也各异。如对父亲的称谓,“籍属粤东则呼‘阿爸’,属江西则呼‘爷爷’,秦籍则呼‘哒哒’”。如在民国时期乐至县,“今日礼教大同,而方言故习,亦所常存。即如家庭名称,谓祖‘爹爹’,父直言‘父’,楚之黄州也;谓父‘爹爹’,母为‘孃孃’ ……楚之靖州也;……粤则父为‘爸爸’,母为‘懔懔’,诸如此类。”清末德阳县,“人少土著之家,地多杂处之民。声音不同,故称呼各异。楚人谓父曰‘爹’,秦人曰‘达’,粤人则谓之‘阿爸’,闽人则谓之‘爸爸’”。
方志中的这些材料说明,四川的乡谈土语几乎包括了各省的方言。五方杂处的四川移民社会,即使到清末民国初期,仍然是各省乡谈并存。清代王正谊《达县竹枝词》“吾处土音听不得,一乡风俗最难齐”,正是四川多种乡谈并存的生动写照。
四川方言格局有哪些类型呢?四川历史上有两次“湖广填四川”,第一次是明初入川的湖广人构成清初的土著,所操语音以湖北话为基础,成为四川方言的主体;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后新老湖广移民在长期的语言交流融合中构成了四川官话。在清代各省移民长时期的语言交流融合过程中,构成以四川官话(湖北方言)为主导,以客家话为其次,混杂其他方言的四川方言基本格局。即四川方言是四川省境内所有汉语方言的总称,共有三大汉语方言。一是四川官话;二是属于客家方言的“广东话”,一般称之为“土广东话”;三是属于湘方言的“永州话”,一般称之为“老湖广话”。即四川汉语方言分四川话、客家方言和湘方言。四川官话成了四川人的“普通话”。
据崔荣昌先生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四川仍存在乡谈主要有客家方言、湘方言等,这些方言岛分布在以下各区县。
1)四川客家方言(“土广东话”)
四川的客家人自称“广东人”,称自己的客家方言为“广东话”,即客家人“打乡谈”。据崔荣昌先生调查,四川客家方言的分布县达46个:1成都市(郊区东山一带,遍布38个乡镇)、2新都(石板滩镇、木兰乡、太兴乡、三河乡)、3金堂(云绣乡、官仓乡、黄家乡、三溪乡)、4双流(中和镇、新兴乡、太平镇)、5彭县(三界乡、蒙阳乡)、6新津(兴义乡)、7温江(金马河)、8简阳(桂花、石盘、老君井、五指、五龙、石堰等乡)、9资阳(小院、红莲)、10乐至、11安岳、12资中(铁佛镇、罗泉镇、龙结区、发轮区)、13威远(石坪)、14内江、15隆昌(胡家、石碾、石燕、界市、黄家等乡)、16仁寿、17井研、18彭山、19富顺、20南溪、21宜宾、22高县、23泸县、24叙永、25合江、26荣昌、27永川、28巴县、29江津、30南川、3l蓬安、32广安(花桥、天才)、33南部(楠木)、34仪陇(乐兴、风仪、大风、五棚、周河、旭日、马鞍)、35巴中、36通江、37广元、38德阳、39广汉、40绵竹、41什邡、42中江、43安县、44三台、45梓潼、46西昌。四川说客家话的人口约100万。
2)四川的湘方言
清初“湖广填四川”中的湖南人带来的湘语,以永州话为代表,被称为“永州腔”。四川湘方言的名目繁多,有“老湖广”、“辰州腔”、“安化腔”、“永州腔”、“靖州腔”、“长沙话”、“麻阳话”等。其中的“老湖广”还有“宝老倌话”、“邵腔”、“百腔”、“死湖广”等多种名称。四川湘方言分布在45个县:1江油、2安县、3绵阳、4绵竹、5三台、6德阳、7广汉、8中江、9金堂、10简阳、11仁寿、12乐至、13安岳、14资阳、15资中、16威远、17内江、18隆昌、19宜宾、20南溪、21纳溪、22合江、23古蔺、24雅安、25荣昌、26永川、27大足、28潼南、29遂宁、30蓬溪、31仪陇、32南部、33西充、34营山、35蓬安、36广安、37邻水、38达县、39开江、40开县、41梁平、42犍为、43天全、44什邡、45彭县。这些方言点集中在四川盆地中部,散布在沱江、涪江、长江和嘉陵江沿岸。典型的有达县安仁乡的长沙话,乐至县的靖州腔,仪陇的永州腔,中江、金堂、简阳和乐至四县相连的浅丘地带的老湖广话。在四川,湘方言的人口约90万。
3)四川的其他方言岛
在客家话、湘方言等乡谈之外,在四川还残存其他方言的痕迹。如西昌市区的河南话;仪陇县的磨盘乡至今还通行一种“安话”(即安徽话);彭县致和乡明台村、金堂县玉虹乡和大足天台乡茅店子的闽南话。
不过,以上乡谈中最有影响的还是四川的客家话。
四川各省乡谈并存的现象揭示出了四川境内汉语方言的复杂性,反映了移民社会复杂的心理和乡土情结。一方面当各省籍移民汇集四川之后,南北方言的统一和融合是大势所趋,各省移民为了交流的方便,必须学习和掌握四川官话。如“五方语言之异的名词,各随沿习,不能强同。故闽、粤之人必学官话”。四川各省移民的乡谈在多数地区消失,出现所谓的声音“由浊变清”的语言融合同化的过程。如民国时期,安县“近数十年交通便利,声音皆入于清,而各省之人腔调渐归一致,音皆多清而浊者少矣”。达县“其填入籍者,以湖广为最多。咸同以前语言尚异,后渐混而为土音矣,明月乡人永州腔今尚末改”。大足县“近三四十年,学校适龄儿童,出就师傅,乡谈遂失真传”。大竹县“其后习与俱化,原籍乡谈之存在者,百不得一”。移民社会后期,在文化的融合日益密切情况下,出于交流的需要,要独立保存一种方言是极其困难的。另一方面,由于乡谈独特的文化功能,各省移民出于固守族群文化的需要,对自己的乡谈土语怀有深厚的感情,因而千方百计想保留自己的乡谈。四川移民的乡谈并没有因交流融合而绝迹。四川移民在与外人交流用四川官话,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交谈则用原籍方言,是四川移民社会语言运用的一大亮点。
双语双言的存在使乡谈得以在强势的官话中生存下来。如大足“惟中鳌场之玉皇沟一带,其居民以原籍湖南之永州、会同两处为多,斑白之叟尚能乡音无改也”“湖广填四川”后,四川方言众多,给方言研究提供许多便利。正如四川方言专家崔荣昌教授感叹:“感谢巴山蜀水的父老乡亲,尤其是我阿妈。是他们的各种乡谈土语,使我从儿时起就同方言结下了不解之缘。‘广东腔’、‘湖广腔’、‘老湖广’至今言犹在耳”。
(二)四川客家“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
1.历史与现状
四川客家方言主要流行于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区。成都东山地区是四川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客家方言岛,至今最完整地保存了客家文化和客家方言(至今仍有不会说四川话的“死广东”)。而且,由于东山地区是距离成都大都市最近的客家方言岛,也是我国距现代都市最近的客家方言岛。成都东山区客家一直保存完好的方言向来引人关注。清末李伟生经东山区写有诗《过西河场》:“土音操闽粤,春事话蚕桑”,特别谈到东山区客家人操客家话;由于四川移民以湖广移民为主,湖广话成为强势语言,客家话处于弱势地位,客家方言岛处于四川官话的汪洋大海中,但300年来,四川客家方言没有被同化而完整保存下来,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四川客家文化之谜。
入川几百年后,四川移民后裔仍保留祖籍的乡谈是有趣的文化现象。事实上,“打乡谈”是移民社会情感维系和族群认同的需要。清代“湖广填四川”各移民先祖均有遗训曰:“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如广安州人敬祖,“远祖条约,不忘其本;原籍言语,必从其初,偶迁囿于方隅,习为他语者,族老必斥曰‘卖祖宗’。”四川各地移民都打自己的“乡谈”,都有一种母语情结,都不想忘“祖宗言”,因而“打乡谈”是移民社会初期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反映了移民“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文化心理。因而,必须指出,在四川,“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不是客家人特有的文化现象,它在四川移民中普遍存在。“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反映了清初四川移民的普遍语言心理,在四川还残存许多湘方言岛、闽方言岛等即为明证。当然,因为客家人一切惟礼是尚,有强烈的祖宗观念和保存固有的文化传统,因而“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在客家族群中更为突出,这倒是事实。
一种文化的延续并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保存下来,主要依靠自身文化隔离机制。四川客家话能在强势的湖广话中保存下来,客家人有意识地强化也是其中的原因,即“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是客家方言迄今能在四川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
东山客家对自己母语的执著态度曾两次令方言专家所震撼。第一次是董同龢1946年在成都十陵镇调查方言,董同龢注意到东山地区的客家人在茶馆里议事或赶场时做生意,都应用他们的“土广东话”。“他们的保守力是很大的,虽然同时都会说普通的四川话以为对外之用,可是一进自己的范围,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们非说自己的话不可。据说他们都有历代相传的祖训,就是‘不要忘掉祖宗的话’,小孩如在家里说句普通四川话,便会遭到大人的训斥。”
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黄雪贞对成都市郊龙潭乡的调查。“凡龙潭寺出生的客家人不论到多远的地方工作或生活,只要一回到家乡,就一定要说‘广东话’,否则将被责备为‘忘了祖宗’、‘四川骡子学马叫’。在农村,有些老人只会说客家话,不会讲官话。正因为如此,龙潭寺虽然位于成都市郊区,客家话仍然很稳定。”方言专家的调查说明客家人在家里严格要求讲客家话,东山客家有意强化说自己的客家母语。连新娶的非客家媳妇也不例外。民国时期,客家娶进的外地媳妇不会说客家话的,婆婆强制媳妇学,以为不说客家话是卖了祖宗。如江津陈怀礼先生回忆,新娶媳妇不是客家人的,还要由婆婆教客家话。李宗吾也回忆:“广东人来四川的,嫁女娶媳,必定要选择广东人,偶尔破例娶本地女子,入门也必须说广东话。家庭及亲戚往来,更要说广东话,否则说是‘卖祖宗’。从始祖入川到李宗吾一辈,已有八代,但还是和客家人结亲的。”至今成都洛带镇宝胜村刘家大院的长辈要求在刘家院子内必须说客家话,新进门的媳妇若不是客家人,也必须学会说客家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