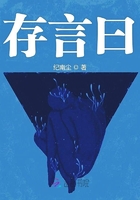四十八来望的羊妈妈死了
来望的羊妈妈已经很老了,行动迟缓,来望放牧它的时候,只能找一些嫩草嫩叶,入冬之后,就日渐消瘦,干草料已经嚼不动了,后来就起不来了,来望很着急,每天放学后都急急地跑回家看望他的羊妈妈。
一天上学的时候,来望红着眼睛告诉我,他的羊妈妈昨天死了。
“死了?”我有些惊讶地问。
“是的,昨天放学回来的时候已经死了,”来望哽咽着说,“我没有见到,我爸爸把它埋了。”
“埋了?”,我很奇怪,不过这是出于本能,我差点说出,怎么不吃了呢,在我的眼里它就是一只羊,埋了多可惜,但是我知道,对来望和他一家人来说,这只羊就是他们的亲人,是来望的妈妈。
“埋哪了?”我又问。
“埋果园里了。”来望说,顺手指了指那棵最大的苹果树。
“噢,”我应了一声。
“我们可以看看它吗?”来望说。
“好吧!”我答道。
我们一同来到果园里,一眼看到果树下新挖的痕迹。
“就这。”来望指着地上说道,“羊妈妈睡在这里,很冷的。”
都死了还冷什么,我心想,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来望用手拨了拨地上的泥土,然后又插上了一根树枝,然后他跪下来磕了三个响头,我惊愕地差点掉了下巴,我没有想到来望会对他的羊妈妈如此情深,当他起身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额头上粘着泥土,我伸手轻轻地抹去。
我们默默地走出果园,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偷偷地瞟了一眼来望,他还在抹着眼泪。
“来望,”我说,“你用不着那么难过,那不是你妈妈,你只是吃过它的奶,你妈妈埋在后山。”我知道来望的妈妈埋在后山,所以我才这么说。
“它就是我的羊妈妈,”来望固执的纠正道,“后山的妈妈我没见过。”
“就在我们以前玩过家家的地方不远处,我知道的。”我说,“我爷爷告诉过我,那座坟就是你妈妈的。”
“我知道。”
看着来望闷闷不乐的样子,我说:
“其实,你不用难过,你有两个妈妈。”话一出口,我才知道这话有多蠢。
“可是两个妈妈都死了。”来望更加难过了。
“你好歹还有,不像我,都是捡来的,捡谁的都不知道。”我只好搬出自己的黑历史来安慰来望。
“你不是捡的,那是你奶奶和爷爷骗你的。”来望否决道。
“我奶奶说在磨窑里捡到我时,就穿个红肚兜。”
“是吗?”来望有些惊奇。
“可我爷爷说他是在跑脚户的路上捡到的,还是光溜溜的,什么都没穿,像小老鼠一样。”
“啊?”来望更加吃惊,“那太可怜了。”
“谁说不是呢,我爷爷还说我吃过狗奶、驴奶、猪奶,甚至连老鼠奶都吃过。”
“那不可能,老鼠那么小,怎么吃?”来望摇摇头,“那是骗你的。”
“八成是捡的,你看我妈打我的样子,像是亲生的吗?”我一脚踢开脚下的土坷垃,“上次要不是我跑地快,估计腿都被打折了。”
“你妈妈打你倒是挺狠的。”来望小声说道,“那总比没有要好。”
“我现和没有有什么区别,还不是一个人照家。”
“那你妈妈总要回来的。”来望说,“还会见到,不像我再也见不到了。”
我看着来望又要哭的样子,赶忙接过话茬:
“回来继续挨打,鸡飞狗跳的,”我又捡起地上的一块土坷垃把它扔到远处,“说不准哪次跑慢了,腿就被火叉打坏了,她天天嚷着要敲坏我的腿。”
“也倒是,那你打算怎么办?”来望反倒同情起我来了。
“要跑得快,”我说,“我现在跑得特别快,要是咱学校有赛跑比赛,我准能拿第一。”
来望的眼光里有些迷惘,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许他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
“不信咱俩赛跑,你就知道我跑得有多快了,”我又对着他说,来望依然没有反应,“你看我跑到前面那棵树下。”我说着就飞奔起来。
然后我回头对来望招招手。
“怎么样?”我问,虽然距离不长,但是全速奔跑,胸部还是一起一伏的。
“我只看到你的两只脚在屁股后面绕。”来望说,“这的确快,这速度,你妈要打着你不容易。”
“是啊,跑起来,什么事都没有了。”我说着拉起来望的手往前跑,一开始来望还有些抗拒,随后就和我一道跑起来了。
但是,来望还是很难忘却他的羊妈妈,总是在上学的路上,冷不丁地问我一句:
“你说我的羊妈妈会冷吗?”
“不会,长毛的。”我会心不在焉地答一句。
“它是睡在地下的。”来望喃喃地说。
风很大,迎面吹来像刀刮在脸上,每说一句就会吸一大口寒气。
“别说了,把你自己顾好,你的耳朵都流黄水了。”来望的耳朵有冻伤的毛病,每到冬天都冻到流浓水。
“没有哪只驴耳朵还是羊耳朵冻得流黄水,你大可不必操心。”我接着说到。
来望的心情似乎宽慰了一些,缩缩脖子,和我一同加快了脚步。
但是,后来我几次看见他独自一人从果园里出来,我知道他准是又去看他的羊妈妈了,我真不明白,马铁匠为什么把那只羊埋在路边的果园,为何不埋得远点,这样来望也就不会来来往往地看见,触景生情。
后来,来望又慢慢地变得开朗起来,这要归功于打柴爷,他在山上打柴的时候,抓了两只还没出月的小狐狸,就带回来送给了来望,来望很高兴,每天对它们细心地照顾,由于还没有出月,所以小狐狸要喝奶,打柴爷刚好养了一只奶羊,给怀孕的珍珠补身体,来望就每天要一点羊奶和煮熟的稀饭拌在一起,两只小狐狸倒吃得很欢实,有几次我看见来望喂它们,嘴里呜呜着互相争食,抬起头的时候,嘴边糊着白色的羊奶稀饭,小肚子吃得鼓鼓的,十分可爱。
当然,来望也间接地去感谢打柴爷,常常在放学后驱赶牲畜,顺道也赶着打柴爷的牲畜到水沟里饮水,由于陕北干旱,牲畜每天的饮水只能到山脚下的水沟里,全村的人畜饮水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