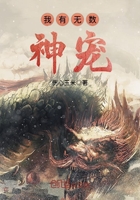二十花匠爷的小闹钟
自从见了花匠爷的小闹钟后,我一连几天都在想念着那个神奇的玩意,那一对啄食的花公鸡仿佛就在我眼前,有几次晚上我都梦到了那个小闹钟,那里面的花公鸡活了,从小闹钟里走了出来,我抱着小闹钟追赶着花公鸡,想让它们回到小闹钟里面去,我追呀追,怎么也追不到。白天当我玩耍的时候,我会忽然停下来,开始回想那小闹钟和里面不停啄食的花公鸡,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神奇,更能让我神往。而对爷爷的纸马,我似乎已没了多大兴趣,以至于什么时候少了一只我都全然不知,我想那一只一定是给太奶送去了,对此,我也只是偶尔会在吃饭的时候问起:
“爷爷,你什么时候骑那匹纸马?”
家人一阵大笑,然后奶奶说:
“你是盼着你爷死了,你能吃宴席吧!”
“不是,我想看爷爷怎么骑马。”我说,因为我想,那就是一匹纸马,连我都不敢去骑,爷爷怎么骑呀,骑马和死去有什么关系,我不明白,但是看他们大笑的模样,我不好再问什么,只好低头继续吃饭,但是心里还在想着,爷爷买那么一个纸玩意干嘛,还有花匠爷为什么要做那些纸品,不过,这些问题在我的眼里都没有那个小闹钟更让我痴迷。
几天后,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对小闹钟的思念,决定自己再去看看小闹钟,因为如果我给爷爷和奶奶说了我的想法,他们是决不会同意的,于是我去找来望,打算让他和我一同前往,来望正坐在前院的一棵大树下出神地望着远方,以至于我走近他都没有觉察到。
“来望,”我伸手在他眼前晃晃。
来望转过脸来,脸上挂满泪珠。
“怎么了,来望,谁打你了?”我蹲到他身旁,关心地问。
“没有,我的小松鼠不见了。”来望擦擦眼泪。
“什么时候?两只都不见了?”我一连串的发问。
“是的,都不见了,昨天我不在家,柱子哥放出来了,然后都不见了。”来望有些伤心地回答。
“它们是不是跑远了,我想。”
“不会的,肯定是被猫叼走了,”来望抬头看着我,“说不定就是被你的花花吃掉了。”
“你······”我有些生气,心想你怎么就说是花花呢,说不准还是别的猫呢。
“你看见花花叼走了?”我问。
“没有。”来望摇摇头。
“那就对了,没有看见就不能错怪,说不准小松鼠还活着呢,再等等吧。”我拉拉来望的胳膊又说道,“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
来望转过脸,眨巴着眼睛看着我。
“花匠爷家有一样特别神奇的东西······”
“什么东西?”我刚说了一句,来望就打断我,眼睛里透露出急切,仿佛小松鼠的事发生在很久以前。
“就是那个小闹钟······”
“我还以为是什么神奇的东西。”来望的眼神暗淡了下来。
“不是小闹钟,就是小闹钟,”我有些语无伦次,“就是小闹钟里有两只啄米的花公鸡,它们头顶着头,一上一下,太好玩了。”
来望听我这么一说又来了兴趣,我们当下合计去花匠爷家,说走就走,手拉着手走上了通往花匠爷家的小路,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赶赶枝头的鸟儿,抓抓路边的花蝴蝶,我们有着一样的兴趣,有着一样的话题,我们是彼此的欢乐,烦恼像一枚小石子,被远远地扔掉,而我们的笑声像涟漪一样在心头荡开,荡开在童年碧绿的远方。
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花匠爷家,家里依旧花匠爷一人,他还是坐在炕上做他的纸活。
“花匠爷,我给你送点李子。”我高声的对花匠爷说道,然后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了八颗紫红的李子,我的口袋太小,八颗已经塞满了两只口袋,而且塞得好像怀孕的老鼠,疙疙瘩瘩的像要蹦出来,这是我路过一棵不知谁家的李子树,顺道给花匠爷摘得,来望见我掏出李子,自己也弯腰掏自己的口袋,和我的口袋一样,还难产,好半天才掏干净,然后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花匠爷的炕边。
“好孩子,你们吃吧。”花匠爷有些感动地说。
“不了,专门给你送的,我们吃过了。”我高声说道。
花匠爷窸窸窣窣地下了炕,然后掏出钥匙打开炕对面放着的木箱,从里面掏出一个纸包,小心地打开,里面包着四个柿饼,给了我和来望每人两个。
“这是你姑上次回家带给我的,放在箱子里都忘了。”花匠爷说。
我们高兴地接过吃了起来。
“甜吗?”花匠爷看我们吃得津津有味,问道。
“甜,这个给你吧!”我把剩下的一个递给花匠爷。
“不吃了,爷吃过了。”花匠爷摆摆手,慈祥的看着我们。
我们边吃着柿饼边在花匠爷的窑里走来走去,而我的目光则一直注视着那个小闹钟,然后就爱不释手地把它抱在怀里把弄,来望随我看了一会儿小闹钟,端详了一会儿那啄食的公鸡,然后就被花匠爷的那些纸品吸引,开始细细的研究起来。
要回家了,来望几次提醒我,我才恋恋不舍地放下小闹钟,同花匠爷告别,没想到花匠爷说:
“闹钟给你吧,爷用不上,又不认识,以前是白天打鸣,这两天老是在晚上,搞得我都睡不好。”
“花匠爷,你不是听不到吗?”我有些诺诺的问,但我想花匠爷是不会听到我这句话的,我想可能是我上次鼓捣的结果。
“给你吧,爷看着太阳就行。”
“那万一没太阳呢?”我还是不确信花匠爷会把这么神奇的东西给我,或许用贵重更好些。
“没太阳就看天,天总在的。”花匠爷笑眯眯地说。
“是,天一直在。”我激动得眼睛都发亮了。
我把闹钟递到来望手里,在花匠爷面前连翻几个跟头,或许这就是我唯一能表达我心中感激之情的方式,因为家乡的百姓很少说谢谢,更没有人给我教表达谢意的方式和语言,不仅是我,而是所有那个年代的孩子的欠缺,但我们依然懂得最基本的礼仪和诚挚的待人之道,没有做作,没有虚情假意,有的只是最原始、最直接的感情。
回去的路上,来望小心地掏出剩下的一个柿饼问我:
“平子,这叫什么,花匠爷说我没记住。”
“柿饼,怎么,你没吃过吗?”我有些奇怪地问,“你不会连柿饼也没吃过。”
来望摇了摇头,诺诺道:
“没吃过,柱子哥也没吃过,我把这个带回去给爸爸和柱子哥尝尝,比糖还甜的柿饼。”
这时,我忽然觉得来望很可怜,这个从小就没有妈妈的伙伴,是那么的让人同情,就像一根针扎了我一下,让我这个在别人眼里的混世魔王的心也轻轻地抖动了起来。
“给你!”我掏出了我口袋里的那个。
“我不要,我有。”来望摇摇头道。
“一个怎么够,我吃过好几次了,过年的时候,二叔会买回来,爸爸也给我买过。”的确,县城教书的二叔年前回家带回了一网兜,有十几个,多数都让我吃了,爸爸也给我买过,还有核桃,这些东西,在当地都是稀缺品,虽然我不是经常吃到,但我还是能吃到,比起来望自己简直不知幸运了多少倍。
来望感激地看着我,我把柿饼塞进了他的口袋,然后就低头玩弄我的小闹钟,我伸直臂膀,一会儿把它举过头顶,像是要敬献给太阳,一会儿又把它移到面前,像是推送给远方,一会儿在左边,像是送给田野,一会儿右边,像是呈给远山,总之我的兴奋之情难于言表。
“平子,花匠爷的那些纸人纸马是干什么用的,不会也是花匠爷做来玩的吧?”来望有些不解地问我,看来他也同我一样,对那些纸品有着相同的困惑。。
“接气马,不是玩的,爷爷有一个,太奶也有一个,已经骑走了。”我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什么是接气马,那些纸马可以骑?”来望有些吃惊。
“不知道,反正他们说是骑得,我也纳闷,那怎么骑呀,还没我的小土车结实。”
“就是。”
我们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来望,我想打开看看。”我晃着手中的小闹钟对来望说道。
“怎么打开,打开就坏了。”来望迟疑地劝阻道。
“坏就坏吧,反正我想看看里面的花公鸡。”我说着就用指甲去扭闹钟背面那一字形的螺丝,可惜螺丝太紧,我的指甲很快劈叉了,我从路上随手捡来一个薄木片,可惜还是太粗,甚至是路边的一块瓷片,我都试过,我的心火急火燎的,有些迫不及待,仿佛那两只花公鸡很快就会飞走一样。
来望看我一心要破坏的模样,也就随我了,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了小刀,递给我,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一把接过来,嘴里还在埋怨来望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有了小刀,螺丝很快就被一一松掉,但是前后盖扣得很紧,闹钟虽然没有螺丝了,看上去依然完整,我只好使命摇晃,忽然,闹钟开了,除了抓在手里的后盖,其余的零件散落一地,玻璃面也打碎了。
“多可惜呀,那么好的闹钟!”来望一边帮我捡起地上的零件,一边叹道。
而我却没有那么多的惋惜,只是急急地寻找我的花公鸡,但是哪里有花公鸡,无非就是两只鸡头,鸡身都是画上去的,随着七零八落的零件,再拼上去,也没有什么稀奇了,头也不再点动,没有了生机,就是一堆冷冰冰的碎铁片,我不由得大失所望,心里这时才有一丝后悔,早知如此,就不拆了。
但是事已至此,我和来望只好将就着能玩的东西玩了一小会,便索然无味,于是我说:
“留下鸡头,把这些都埋了吧,别让人看见。”
来望点点头,或许他也觉得如此的作案现场,让人看见的确不舒服。
于是我俩就在路边挖了一个坑,把小闹钟的残肢断臂全部埋掉,回去的路上,我们的手里,各自握着一个鸡头。
这就是那个神奇的小闹钟,在我的手里还没过夜,就被我大卸八块,然后又被深处理地打扫了现场,我们可能埋过猫埋过狗,谁埋过小闹钟,那就是我,童年时代的混世魔王——黄毛。
埋葬了小闹钟,也并不影响我的心情,仿佛我终于释怀一样,那个萦绕了我很久的花公鸡我也终于见到了,虽然只有一个鸡头,我想我也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路过李子树下,照样饱吃一顿,又让衣袋继续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