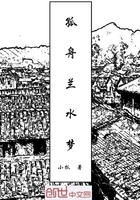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他的生活方式就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他对生活中敏感事物的追求就不同。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薛老喜就特别注重‘抱团儿’,并且他抱的是一种特殊的‘团儿’。
每逢过年下的时候,他都会特意的把康大功兄弟和大塔村村支书的兄弟们约到家里吃一顿饭,以便联络感情增强凝聚力。记忆中,每个春节的大年二十七儿或者二十八儿,薛老喜的家里都要举行这个饭局的。
饭桌上肯定是要喝酒的,不然不会每当那个饭局的时候,那个李姓的村支书总是在他家里喝的酩酊大醉,然后下午在苏家屯的大街小巷耍上一场‘酒疯’。那个时候,苏家屯的家家户户便倾家出动,围观由大塔村支部书记所主演的这场“闹剧”。
“闹剧”上,那李支书总手舞足蹈,骂骂咧咧,絮絮叨叨。面对着一街两行的社员,也面对着搀扶着他的康大功兄弟们。他有时畅怀,有时赤膊,有的时候大哭,有的时候大笑。嘴里总是大声的吆喝:“都滚一边儿去,你们真的不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你们暗地里做的啥事儿我会不知道?光想着把我撵下台儿你们干,知道不知道?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到这里,他总是“哈哈····”大笑。
“你们老中老能?我咋不知道嘞?‘窝里炸’了中,老中老能出出二家门,出出你们苏家屯的‘二道儿桥’试试?”说完又是“哈哈····”大笑。
“你老中老能,你就干,我现在就辞职,想着干着老美?你干干试试?不死也得脱三层皮····”,说到这里,他又哭了起来,鼻子鼾水一大把,好像是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
“啥事儿我能不知道?我不吭气儿就是高看你们了,咱敢把事都说得清清楚楚······?”
·······
他哭哭、闹闹、说说、笑笑。每当这时,不知道是谁把信儿送到了他的家里,他的几个孩子便如约而至,把他搀回家里去了。
那时候年龄小,也不知道他说的“你”和“你们”指的是谁,长大了才知道他说的“你”和“你们”指的就是康大功和他的兄弟们。
时间不长,又见那支书和康大功私跟着,有说有笑的,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那李支书可不是简单的人,他的功夫绝对在康大功之上。他平时说话有点“结舌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口吃”、“结巴”。听爸爸说的,他们小时候都是同学,李支书上学的时候背书背的可美可美,还会演唱节目,说快板书。他的“结舌子”是他到了社会上练就的一套过硬的本领。
那时,他都当上村干部了,在与人交流的时候,为了防止自己的语速太快,就像说快板书一样一下子把嘴里的话都倒出来,被对方抓住了什么破绽,他就想了一个这样的方法,每当去公社里开会,书记或者主任让它发言,或者与其他的支书交谈,他便放慢语速。但这种方法很容易让人看出来是在故意“耍心眼儿”。无奈的情况下,他每次去公社里,总是在嘴里噙着一个架子车车轮里的小钢珠儿,平时别人也看不出来,一旦说话了,或者交流什么了,那个小钢珠儿都起到作用了,如果不慢一点,小钢珠儿就会咽到肚子里去。为此,每当这时,他就把那个钢珠儿压在舌尖下,这样,舌头绻动的不灵敏了,他的语速就自然地放慢了。语速放慢了,他就利用前一句话和后一句话的充分间隔,组织安排自己下一句恰当的话怎么说,总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无懈可击。
时间长了,他便形成了“结舌子”的毛病,就是舌尖下不压那个钢珠儿的时候,这个毛病也改不过来了。
另外,李支书从心底里瞧不起康大功“唯我”的“窝里炸”作风,他总认为那是一种强硬的做派,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处世哲学。
那年,他手下的那个会计有点不听他的话了,要是在康大功,他就是一句话“滚鸭子过去”地把那人打发走。但李支书不那样做,那年公社管理纪律的副书记领着“账目清查小组”到大塔村例行查账的时候,李支书先是招待了小组的成员。谈话中,那副书记问他:“咱村的各项账目做的咋样?都是按照组织的要求没有违反纪律吧”?
李支书眼睛一亮,结结巴巴地说:“哎呀呀·······,做的可好了。首······先,咱用的那会计是个好·······人,是个大好人。无论如何的查·······查账,一定要保住我········我这个会计继续当下去,那人心正手勤·······”。他说了一大堆那会计的好话,然后又说:“给你们说········说明白吧,他只有去年的·······的时候,把公社返还回来的公········公粮款没有上账,就这一件事违了点·······点法,你们千千万万不········不要给党委汇报,他就这一点违法·······的事······”。
管理纪律的副书记是干啥吃的?就这几句话,他把公社返还公粮的账目调了过来,轻易的就把这件事情落实了。不几天,那个会计都叫派出所叫去关了几天,自然会计都当到头了。
事后,李支书又和那会计一块去找过公社的正书记说情,正书记给他俩日瓜了一顿,上了一堂政治课,还教育李支书,以后不能给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当保护神了。
后来我常想,那李支书可不是在简简单单地耍酒疯,他肯定在日常的生活中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了,遇到康大功的挑战了,遇到“英雄没有回天力”的烦人事情了······。他很聪明,就利用这个“耍酒疯”的机会,张牙舞爪的把他平时不敢说的话说出来,把他平时不敢做的动作事做出来,以便增加他的威慑力。
后来我又想,他的这个行为意义很深,他一方面是叫老百姓们看的,更重要是提醒康大功弟兄们的。
谁知道当时他真的醉了没醉呢?
时间长了,李支书的几个孩子总在他耍完酒疯的那个恰当的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把他接回家里。
薛老喜对这件事乐此不疲,他真正的希望村支书醉得越深越好,酒疯闹得越凶越好。那样,全村人都会知道他不但与康大功的关系不一般,而且与村支书的关系也是不一般的。他自己心里也清楚,他是会在这一种场景以后,坐收渔人之利的。
有一天,老师上课讲“狐假虎威”的故事,我是理解最深刻的人,我认为薛老喜是全世界最会“狐假虎威”的人。
那时候的农村喝不起原装的酒,像薛老喜这样的上层人物也是到“合作社”里卖零酒喝。在“合作社”买零酒,根本不用担心买住假酒,社会上也根本没有假酒的概念。
那年的年二十七儿中午,薛老喜和往年一样,把康大功兄弟和大塔村支书的兄弟们都喊到了家里请客吃饭,中午过去了,整个苏家屯的人们都全家出动,在大街上等着村支书醉酒后耍酒疯嘞。
这时,大家都看见村支书满面红光地从薛老喜家里健步走出来,一边的人要搀扶他时,他说:“搀我弄啥”?
大街上的人都感觉到有点奇怪,今年是支书的酒量增加了?还是薛老喜家没有酒了?为啥年年醉酒,今年不醉了呢?
薛老喜更是一脸的懵懂。
正在这时,支书的几个孩子走了过来,他们是商量着在这个时候来接醉酒的爸爸的,见到爸爸走在大街上,就一起上前去搀扶他。支书那只胳膊一下子挣脱了,对着孩子们,对着大街上的人们大声地说:“搀我弄啥?今年喝的酒是兑了一半多扣子沟下的河水········”。
一街两行的人都听见支书说这句话了,都在不解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到了晚上,我听见薛老喜在我家大门外喊我,我走了出去。见他就站在门外的黑暗处等我,他问:“老栓儿,是不是你仨给我买住假酒了”?
“我不知道呀”?我回答,
“是在扣子‘合作社’里买的吗”?
“就是”,我坚定的回答。
“回来的路上你们把酒撒了”?薛老喜问。
“没有呀,都是你家照东掂着的,他不叫俺俩跟他私跟,我还看见他在沟下把河里的水往瓶子里头灌了······”。
薛老喜听到这里不再往下听了,他扭头朝他家里走去。
一会儿,我便听见了薛老喜在他的家里吆喝和骂人声:“日你娘想起来的,你丢人不丢人,踢死你的功夫都有·····”。
又一会儿,便听见二骡子的求饶声:“爸,我不敢了,爸爸,我真的不敢了,不要再踢我了······”。
后来我便想到,那李支书为什么不趁着那个时间“发酒疯”了呢?
李支书一定是想象到了,康大功也会和薛老喜一起,用一瓶子凉水试验他是否是真的醉了。
这个世界上还真的应该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