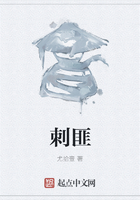“都趴下别动!”我在稀里糊涂中被翻过身,头被死死地摁在地上,嘴里啃了一口青草和烂泥。天还很黑,篝火已经熄灭了,我斜过脑袋,努力抬眼想看个明白,但只看到很多双肮脏的脚走来走去,周围一片嘈杂,夹杂着三毛他们的惊呼声,他们显然也经历了跟我一样的遭遇。
“这么多枪!”我听到有人欢呼。
“还有个娘儿们呢,哈哈。”有人淫笑。
我感到一只膝盖顶住我的脊柱重重地往下一跪,我疼得差点没背过气去,接着一双手在我身上上上下下摸了起来,我身上的所有东西,包括腰里别的手枪,装着衔尾蛇戒指和衣带钩的绒布口袋全被搜了出去,然后双手被扭到身后,用绳子绑了起来。
“站起来!”有人踢了我一脚,我翻过身,屈起双腿,有人拉着我的领口帮助我站了起来。我看看四周,见三毛、猴子、大力、杨宇凡和李瑾一个不少,都像我一样被捆住了双手。
抓住我们的是一群蓬头垢面的家伙,大约有十几个,虽然穿得破破烂烂的,但显然不是什么野人,他们正在大呼小叫地整理获得的战利品。
我转头看了看杨宇凡,只见他满脸懊悔,见我瞅他,便低下头哭丧着脸说:“对不起,我睡着了……”
“不准说话!”杨宇凡身后的一个“野人”冲过来打了他一巴掌,然后把他脖子上的一条Burberry围巾解下来自己围上。
“各位……壮士……”我试探着出言说道,“我们也是逃难来这里的,东西你们全拿走,就当交个朋友好不好?”
“少他妈废话!”一个大块头“野人”过来推了我一把,然后对着自己的同伴招手,“他们的嘴都塞上!”
几个小喽啰兴奋地高声答应,其中一个拿了一团黑乎乎的破布在我眼前晃了晃,然后一把塞进了我嘴里,我只觉得一阵恶臭,嘴里被堵了个严严实实。
“春哥,你看这是啥玩意儿?”刚才搜我身的那个野人突然走到这大块头跟前,手里拿着那只绒布口袋,从里面掏出戒指和衣带钩献宝似的递到大块头跟前。
“咦?”春哥拿过两样东西掂了掂,又看了看我们,这才把东西塞回口袋,“带回去给狼爷看看!”
狼爷?我大吃一惊,这家伙也大难不死从钱潮市跑出来了?只不过为什么阴魂不散,每一次都好死不死跟他撞上了?
“都带走!”春哥发了一声喊,小喽啰们都大声答应了,推推搡搡地把我们往山上赶。
于是我们又开始上路,只不过这一次是被迫的,我们就像是被巡山的妖怪抓住的唐僧师徒,被一路押解上山,却没有孙悟空会来搭救我们。一开始我以为这些人会把我们带进大山的更深处,但在山里走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我突然觉得眼前一亮,一条盘山公路出现在我们面前。
真是该死,我心里懊丧不已,离我们隐藏地这么近的地方竟然有一条公路!只要爬上一座高一点的山峰侦查一下就能发现!这帮人一定是看到我们生火的炊烟了,说不定前天大力他们打野猪的枪声也听见了,才能一路追踪过来。
“把头套给他们戴上!”春哥又发号施令道。
一只黑布袋从天而降套在了我头上。我忍不住叫出了声,扭着头想抵抗一下,但马上肚子上就挨了重重一拳,疼得我像烧熟的虾一样弓起,仿佛所有的肠子都绞到了一块。
“快走!”我背上又被推了一把,我只好继续摸着黑往前走。
所幸这段黑暗旅程并不长,只是感觉拐了无数个弯,其间我听到一片哗哗的水声,感觉到脚下的土地在坚硬的柏油路面、松软的沙土和厚厚的枯叶之间转换,过了大约不到一个小时之后,我感觉又踏上了硬实的地面。
“抬脚,前面是台阶!”抓着我后衣领的喽啰在我耳边大喊。
一段不矮的台阶过后,我感觉眼前光线更暗了,似乎是进了室内。
“进去!”我背后被重重推了一把,我向前打了个趔趄,一头撞到了墙上,接着又一个人被推了进来结结实实地撞到了我背上,紧接着又是一个……然后是“砰”的一声,似乎是门被重重地甩上了。
“呜呜呜……”我努力地想发出声音,想问问我的同伴们情况如何,但回应我的也是一片呜呜呜,我只听出了三毛的声音。很快我们都明白这样的努力只是徒劳无功,于是渐次安静下来。我们在黑暗中呆呆地站着,就像是一群待宰的猪羊,等待着命运的降临。
黑暗中的时间过得很慢,似乎很久之后,门外终于传来一阵脚步声,片刻之后门“吱呀”一声被拉开,一个男声高声问道:“这戒指和钩子是谁的?”
我梗起脖子呜呜了几声,马上就感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脖颈,把我拉了出去:“狼爷说要见你,跟我走!”
说是跟他走,但这人既不打开我的头套,也不解开绑着我的绳子,还是推着我一路往前走。几分钟之后,我忽然听到几个人对话的声音,紧接着眼前光线又亮起来,然后身后那人拉住我让我站定,说了一句:“狼爷,人带来了。”
“嗯……”我听到一个略显尖锐的声音应了一句,听声音却不不像是我们认识的那位狼爷。难道是同名?可是狼爷自从命根子断了以后,性情大变,声音跟着变化似乎也有可能……只是这个声音也挺熟悉,好像在哪里听过似的……
“山下情况怎么样?”我正乱猜着,就听见那狼爷继续说道。
“还是那样,东边过来人很多。”这是那位春哥的声音,“可进了山的也就这几个,应该是被咱吓住了。”
“嗯,不过迟早要进来的……”狼爷像是自言自语似的低声嘀咕,然后话锋一转又问,“这次抓了几只?”
“六只……两只大的,四只稍微小一点。”
完了,我心里大惊,这该是碰上食人族了,把人都论“只”算,我们六个人,可不是三毛和大力二人个子大一点嘛。
“今天先把两只大的洗剥干净,给大伙吃了,四只小的先养着。”狼爷又说。
“好。”春哥答应一声,又用命令的口吻道,“你叫几个人去河边弄,麻溜点,别弄脏了地。”
三毛大力!我心里惊骇莫名,忍不住呜呜叫了出来。
“嘿,不理你倒急了?怎么?赶着要投胎?”春哥嬉笑着说了一句。
“别扯了,把他头套摘了,我问问他这玩意儿的来历。”狼爷又说。
我眼前一亮,突然而至的强光刺得我眼前一阵发黑,我强自眯起眼睛,看到自己在一个宽敞的厅堂中间,面前摆了一张八仙桌,后面坐了两个人。
这俩人没有一个是狼爷,但其中一个相貌奇特,却是我的故人!
这人坐在桌子后面只露出一个畸形的小脑袋,不是侏儒毛头又是谁?大概是我蓬头垢面,胡子遮了一半脸,又掉了三分之一体重的原因,毛头却没一下就认出我来,此时正在桌子后面略带戏谑地看着我。
“呜呜呜……”我急切地想表明身份,好让毛头收回杀三毛大力的命令,但嘴里的破布塞得太紧,春哥掏了好几下也没掏出来。
“他妈的急什么!”春哥也烦了,怒吼道,“嘴巴张大!”
我张大嘴,感觉自己颌关节都快脱臼了,春哥粗暴地把布团用力一扯,我的门牙一阵剧痛,嘴里顿时泛起一阵血腥味,这一下一定是把我的牙齿带着扯松脱了。
“毛头!”我顾不上牙齿的事,破布一离嘴,便大喊道。
毛头一听这俩字,一下愣了,抬头仔细端详了我一会儿。
“毛头,快叫人回来,别杀三毛……”我喘了两口气之后又喊。
“源哥?”毛头这才认出我来,他狐疑地从椅子上跳下来,直接钻过桌子,来到我的面前,仰起头又看了看,这才确定,兴奋地说,“还真是你!你怎么来了?”
“快快,你别杀人,三毛在呢!”我没接他的话,只是语无伦次地大喊。
“什么杀人?”三毛疑惑地皱起了眉头,“三爷也来了?道爷呢?”
“狼爷……这是你朋友?”一旁五大三粗的春哥面露尴尬地问。
“什么朋友!”毛头暴跳如雷,“这是咱们的恩人!还不快松绑?!”
“哦哦……”春哥忙不迭地绕到我后面替我解开绳索。
“毛头,刚才你不是叫人去杀两只大的吗?那是三毛跟另一个朋友,你快叫人回来,晚了就来不及了!”我一边挣脱绳索,一边大喊。
“哦……”毛头和春哥二人同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然后哈哈大笑。
“那说的是两只兔子……”春哥笑得合不拢嘴,枯槁的络腮胡下面露出一口黄色的烂牙。
“刚好今天抓了六只兔子,”毛头拍了拍我的腰,“一会儿都杀了给哥几个开开荤……小春,快把源哥的朋友们都放了,带这儿来,今天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哎!”春哥应了一声,一路小跑着去了。
片刻之后,我的伙伴们都被带了进来,几个人都是满脸困惑,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转。三毛一看到毛头,很是愣了一下之后,才大声喊道:“毛头,狼爷就是你?”
“嗨……都是吓唬人的。”毛头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小春,你去张罗张罗,六只兔子全炖了,还有过年剩的腊肉也炒了,上次不是在城里搞了几瓶飞天茅台吗?也一起拿上来,把村里老人也叫上,咱们中午好好吃一顿,给哥几个压压惊!”
春哥麻利地应了一声去了。
“你小子出息了,怎么干起拦路抢劫的事来了?”三毛毫不客气地在八仙桌后面的太师椅上大马金刀地坐下。
“唉,”毛头叹了口气摊开手说,“我不劫人家,人家就得来劫我啊。来来来,坐,大家都坐……”
八仙桌旁还有几条长凳,我们依次坐下,李瑾、杨宇凡等人还是余惊未了,我和三毛跟毛头却是故人相见,很快亲热起来,各自讲述了自从浒丘分别后的经历。
原来毛头当晚拿到我那两万块钱,第二天就购买了一大堆食物和必需品,又集结了几个在浒丘打工的往日同乡,几天之后就回到了深山之中差不多被废弃的老村子里。后来感染者危机爆发,村民们都陆陆续续回来避灾。因为毛头示警得早,村民都以为他有未卜先知的异能,加上他前期准备充分,所以大家都奉了他当头儿。
这家伙人虽然畸形,行动力却比我们要强得多了!我暗自感叹,当时如果我们当机立断,在戒严之前就逃出钱潮市,可能就不会遭受后面的种种苦难了……当然,也很有可能在军阀混战中早早被巧取豪夺个干净,甚至丢了性命……福兮祸兮未可预料,我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转向毛头问:“那你们为什么要下山劫掠呢?”
“不是抢劫!”毛头大摇其头,“是吓人!本来这山里吧,虽然日子过得苦一点,但好歹能吃饱饭,前几年山里都没人待了,环境也好了,狍子、野兔、山鸡也多,烧几块坡地种种玉米土豆红薯,喂饱我们村里几十口人没什么问题。可后来进山找食的人越来越多,光我们浒丘县的人也就算了,最近一两个月,连你们大城市的人都陆续过来了,我们这儿实在是存不下这么多人,所以只好去吓吓他们,让他们知难而退,其实也就是装神弄鬼,也不会真把人怎么样……”
“还不是把我们东西都抢了。”猴子嘟哝了一句。
“呵呵……”毛头尴尬地挠挠后脑勺,“这也怪你们的家伙太好了,小春几个红了眼。”
“还把人都抢了呢!”李瑾追了一句。
“这是因为这两样东西……”毛头掏出那绒布口袋递给我,“上次在那棺材里找到的玉环,上面那咬自己尾巴的蛇,当时道爷讲的特邪性,我跟村里人当故事说了,小春今儿一见,就觉得有问题,所以把你们都带了上来……对了,道爷呢?怎么没见他啊?你们这一年多,都怎么过来的?”
我和三毛对视一眼,都黯然地摇摇头,我开始慢慢讲述我们分别之后发生的事,怎么买东西,怎么被困在了城里,怎么被骗出家门后来被冯伯收留……
“唉!”毛头听到道长被感染者咬断了脖子之后唏嘘不已,连连摇头,“真是乱世不如狗,道爷这人哪,学问做得好,体力和胆色难免就差点意思了。”接着又双手合十对天一拜,“道爷,您一路走好,这世道啊,也没什么可留恋的,早死早超生,早日投胎找个平安年代……”
这时一个流着两筒黄绿色鼻涕的十来岁半大小孩从门口跑进来,气喘吁吁地在毛头面前站定,啪的一个敬礼,然后猛地吸了一口,两挂鼻涕倏地被吸进鼻腔,只留下两条淡白色的浅痕:“报告狼爷,开饭了!”说完又是一个敬礼,摇摇晃晃地做了个向后转,又张牙舞爪地跑了。
“你这还是军事化管理?”我看着毛头戏谑地说。
“嘿嘿……”毛头难为情起来,讪笑两声,挥挥手转换话题说,“走走走,咱们吃饭去,让你们尝尝正宗的农家菜。”
说着便当先往外走,还没走到门口呢,突然又转过身仰着头对我和三毛说:“源哥、三爷,一会儿在小子们面前给我留点面子,我现在改了名……复姓独孤,单名狼!”
我说怎么又来一狼爷呢!
这个村子总共就二三十幢瓦房,被两座高耸的山峰夹在中间,一条小溪从一侧流过,房子因为被遗弃了很久,外墙上覆盖了一层密密麻麻的爬山虎,就像是披上了一层森林迷彩。
吃饭的地方在村中央,大概是以前的祠堂,四开的门面,飞檐斗拱,厅堂里面已经放了三张饭桌,上面摆了碗筷、几碟凉菜和两瓶飞天茅台,当中是一张八仙桌,另两桌却是竹板两头靠在条凳上草草搭就。毛头把我和三毛领到八仙桌上分主宾坐了,猴子等人自有村里的年轻人迎上来热情地引到两边就座。
我们这一桌上还有四位老人,加上毛头和春哥,毛头一一为我们介绍,说四位老人自从村里集体搬迁就没出去过,一直待在村里,算是元老。
“小春你们见过,”毛头指着下守陪坐的春哥说,“大名叫董艳春。”
我一下呆住了,这个五大三粗,胡子拉碴,像极了《哈利.波特》电影中巨人和人类的混血儿——霍格沃茨学校的看门人海格的汉子,实在无法跟董艳春这个名字联系起来。
“呵呵。”董艳春憨憨地一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家里人说取个女孩的名字好养活……跟叫阿猫阿狗的意思差不多……”
我们被这个耿直的汉子逗得哄堂大笑,剩下的被他抓住的些许不快也马上烟消云散。
“开席开席!”毛头像领导似的在头顶上挥手大喊。
于是各桌都纷纷开酒,菜也流水似的上来。毛头说得没错,都是典型的山里农家菜——山鸡炖笋干,蒸腊肉,白切猪头肉,排骨炖蕨菜干,棒骨炖萝卜……菜都用不锈钢盆装了,高高堆起。
“来!我们先敬老人一杯!”吃了几筷子菜以后,毛头猛一挥手说,“古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咱们牛轭沟啊,这一年全靠四位老人,现在也只有他们还认识山里的野菜,认识那些山货了,来,让我们祝老人们长命百岁!”
众人都闹哄哄地站起来喊好,高举着酒杯面向老人喝了,老人们也是面露红光,笑着端起酒喝了。
“接下来我们要敬几位贵客!”毛头等大家重新斟满酒,转向我和三毛说,“这二位可是咱们村的大恩人,当初要不是他们给的两万块钱,我也置办不起那么多米粮,也买不来那几杆土枪,更别说几次让大家死里逃生的那些药。来,大家端起酒杯,敬几位恩人!”
这下三桌哗啦啦又站起一大片,连几个老人也都颤巍巍地站起身敬酒,我们赶紧推辞,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把酒喝了。
“好!”毛头又大喊,“大家今天一定要要好好招待几位客人,让他们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村民们跟着大喊。
喝完这一杯大家便坐下开始乒乒乓乓地吃,我们主桌还好,几个人吃相还算斯文,其他的两桌就跟打架似的,肉塞到嘴里几乎不嚼就往下咽,每个人的腮帮子都鼓得像松鼠似的,几大盆菜很快就见了底。女人们虽然不上桌,但都在窗户外面看着,一见菜盆空了,便马上进来撤出去,重新装满端上来。
农家菜虽然都是炖和蒸,但味道十足,对于一年没吃过正经饭菜的我们来说,简直就是珍馐美馔,我用了很大的自制力,才避免自己像其他两桌那样狼吞虎咽。
“这是什么东西?”我夹起一块跟兔肉炖在一起的东西,一开始以为是土豆,但尝到嘴里却发现比土豆更面,味道也很特别。
“是葛根,”毛头坐在主位上,他的椅子经过专门的加工,四脚拉长,就像以前餐厅里的宝宝椅,“这玩意儿可救了我们的命了,以前没人要,漫山遍野的长了个遍,这个冬天玉米土豆都吃完了,幸好老人还记得这东西。”
“哦……”我一下明白过来为什么老是会对这片山林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就是这种覆盖在林子上空的葛藤,道长曾经说过葛根可以吃,花能制药,葛藤还能织布做衣服。
这样吃了大半个钟头,几个老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说自己吃饱了先走了。等老人一出去,屋里马上大乱,董艳春率先发难,给我们这几个外来客挨个敬了一遍酒,然后村民们纷纷跟上,除了李瑾之外,其余人一个也没放过,把我们团团围住,排着队敬酒。
接下来的聚餐过程我已经完全断了片,只记得自己在一片久违的喧闹中来者不拒,乱糟糟的,吐了好几次,等我再一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了。
身边的三毛鼾声如雷,我勉力抬起重如铅块的脑袋,只觉得里面的脑仁像是被挖出来扔到墙上似的一阵阵地疼。窗外天刚蒙蒙亮,隐隐有整齐的号子声传来,像是很多人正在一起抬什么重物。我掀被下床,发现自己身上赤条条的只剩一条短裤,床边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叠着两套衣物,显然是为我和三毛准备的,我都抖开看了看,捡了自己的尺码穿了,衣服不新,但都干净舒爽,带着一股淡淡的洗衣粉清香。
我穿好衣服,推门而出。门外是一条石子路,青黑的石子被磨得油光发亮,石缝间长满厚厚的青苔。对面是一口小小的池塘,几个妇女正在池边浣洗衣物,见我出来,都朝我笑了笑,我看了一眼,见她们洗的正是我们几人的衣服。
门外那整齐的号子声越来越响,我循声而去,渐渐走出村口,石子路沿着小溪一路蜿蜒向前,几分钟之后,小溪前面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水面渐宽,形成一个小型的堰塞湖。在湖水的对面,我看到一架长龙似的木头水车一头插在水面,一头架在岸上,几个精壮的汉子正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奋力踩着水车。水车下面还有几人围观,正是李瑾、大力和杨宇凡。
“源哥!”杨宇凡隔着老远就向我招手,我从架在水面上的几个石墩子上跳跃而过,到了对岸才发现水车不止一架,而是依着山势逐级而上,像是接龙一般,一架连着一架,直达山顶。一圈一圈的梯田如涟漪般顺着山势荡漾开来,几头老牛在山间耕作,从山下看,就像是挂在天上一般。
“昨天咱们睡觉的地方就在这下面。”杨宇凡指着湖水的尽头,那边水声大噪,我过去一看,只见山坳在这里猛地往下一挫,形成了一个二三十米的悬崖,悬崖下面可不就是我们昨晚宿营的地方吗?
难怪这么容易就被董艳春他们发现了,原来我们自以为隐秘的地方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我心里暗忖,不过也幸好如此,才碰上了毛头,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像个桃花源,地方偏僻,自给自足,很有机会在这乱世中独善其身。
“这是在干吗呢?”我仰头看着奋力踩水车的三个汉子,他们都光着上身,一层层热气在他们虽消瘦但线条分明的脊背上慢慢蒸腾,随着他们“嘿、嘿、嘿……”整齐的喝呼,清冽的湖水不断被汲上岸边,然后由另一架水车继续往上运转。
“今天种稻子。”大力咧着嘴,手搭凉棚眯着眼往上看,“这得有几十层吧?”
“六十五层!”水车上一个年轻小伙子笑着抢答,“听老人说,是以前‘农业学大寨’的时候传下来的,去年时间不凑巧,错过了春播,只来得及种了点旱菜,冬天狼爷让我们把破的地方重新修整了,这回赶了个早,一定要把稻子种上。”
“就是,吃了大半年玉米番薯,这嘴里都淡出鸟了,要是有碗大米饭吃,啧啧……”另一个小伙子搭腔道。
“你拉倒吧,”最后一个年轻人摇头道,“老人们说了,就算收了大米也不可能顿顿白米饭,都得跟玉米番薯萝卜掺着吃,哎哟!”话还没说完就成了一声惊呼。
原来三人只顾说话忘了喊号子,节奏顿时散乱起来,三个人抬起腿,像只树蛙一样在横木上吊了一会儿,等水车稳定,才继续“嘿嘿嘿嘿”地踩了起来。
“那个……毛……啊,狼爷呢?”我想起昨天匆忙而至,紧接着又醉了半天一夜,脑子里还有很多疑问没打听清楚,再说毛头虽然客气,但到底肯不肯收留我们,也是一个未知数。
“嘿嘿嘿嘿……在上面……嘿嘿……跟老人……嘿……在一起分稻种呢……”
我点头致谢,又问大力等人要不要一起上山看看,李瑾说要给村里人出诊看病,自己率先回村去了。我跟大力、杨宇凡一起从盘旋在梯田的田埂间踟蹰而上,在山顶的凉亭里见到了正站在中间的石桌上张牙舞爪大声呼喝的毛头:
“我不管你是张家李家的,十层以上就是种玉米土豆和番薯,没得商量!再说,往后这收成全是集体的,大家一块儿种一块儿吃,哪有什么你的我的?今年的稻种就这么一点,高地里派水不容易,万一今年雨水不足,不都得干死?这稻种啊,肯定是要种在下面的地里!”
毛头看到我们,只是点了点头,又转过头去跟排着队的一群人争论。我发现队伍中绝大部分都是妇女,极少壮年男性。
“这地里长久没有水,肥力上不来,今年要是不种稻子,往后好好的水田可就只能当旱地使了!再说以后也不是一直集体啊,谁知道会不会又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了?我家男人这又是巡逻,又是放哨,今天又在下面车水,出的力又不比谁家少,凭什么不给我稻种?”站在他对面的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叉着腰唾沫横飞。
“少他妈扯淡吧,就你们家那孬种?上次让他去基地放哨,还没见到僵尸呢,就吓尿了裤子,你还有脸说!该不是你男人让你弄得太多,卵蛋都弄没了?都别在这瞎嚷嚷了,快去下面插秧,否则我扣你工分!来来来,下一个!”毛头大肆开着荤笑话,引得周围一阵哄笑,搞得那妇人也是满脸通红,咒骂了两声,悻悻地去了。
我们等到日上三竿,毛头才分完稻种,闲杂人等都依次离去之后,他从石桌上一跃而下,连连朝我们招手称招呼不周。
“怎么着?你这儿还搞集体合作社,赚工分呢?”我打趣道。
毛头不好意思讪笑几声:“不这么搞不行,现在种子啊,机器啊,人力啊都有限,不这么搞,哪天就要为抢水抢种子打出人命来了!”
“还没吃早饭吧?走走走,咱们回村吃去!我特意让他们包了豆腐包子!”毛头转过话题又说。
“这个……狼爷……”我掂量了一下称呼才开口说道。
毛头转过身四处张望了一下,略带尴尬地说:“没人的时候,还是喊我毛头吧,怎么就觉得怪怪的……”
“那好吧,毛头,”我单刀直入道,“我们几个想在这里待下来,你看……”
“那太好了啊!”毛头雀跃道,“我还怕咱们这庙小,留不住你们这几尊大佛呢!”
“你也看到吧……”毛头指指四周埋头耕种的人,继续道,“我们村啊,男丁是严重不足,又是上有老下有小,而且以往都是在外面打工的,没什么本事,不像你们,我听说那大姐是个医生,还有个建筑工?还有三爷,那身手,那枪法,我可是见识过的,我们这儿只有几杆土枪,能打枪的人是少之又少,您二位来,正好来当我们的教官。”
我见毛头是由衷的开心,心里也松了一口气,接着问道:“咱们上次去过的那个军事基地……就是有飞机的那个,就在这附近吧?现在情况怎么样?”
“嗨,我正要跟你们说这事呢!”
下山的小路难行,毛头却走得飞快,在田埂间上下纵跃,充分发挥出了他作为山地民族的种族特性,我们紧赶慢赶才不至于落后太多。
“基地就在那座山后面,”毛头在梯田的边缘站住等我,指着牛轭沟村背靠的那座高山说,“上了那座岭,后面就是咱们上次爬过的悬崖。”
“基地呢?现在怎么样?”我艰难地迈下一阶湿滑的田埂,急切想知道答案,“那些僵尸还在吗?”
“都被轰平了!”毛头噘起嘴摇摇头,“我回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那边看了看,基地已经被完全炸烂了,那个放飞机的圆房子,还有另外那些楼房,一个都不剩,现在就剩下些黑乎乎的大坑。至于僵尸嘛……”毛头缩着脖子看了看四周,仿佛只要提起这两个字,感染者就会从空中显形对着他的脖子来上一口似的,“肯定是有的,因为外面的铁丝网围墙又被加固了,包括咱们开车撞出来的那几个洞,都补上了!你想那放棺材的地下这么深,炸弹也炸不到啊,那底下还有那么多僵尸呢。”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想起那些浑身漆黑,随着石窟里的水钟不断被冲来冲去的感染者,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所以我派了几个人常年在悬崖上蹲守,”毛头继续说道,“只要一有情况,他们就会砍树。”
“砍树?”我奇怪地问。
“对!”毛头得意扬扬地点头,“就是消息树,《小兵张嘎》里学的,一有情况就把树放倒。本来我想用狼烟来着,可一来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二来,这狼粪也不大好找……”
“你说的树在什么地方?”我手搭凉棚往那片山上张望。
“就在那边……咦?”
毛头转身一指高山,自己却一下愣住了,随即惊叫道:“不好!出事了!”
他再也不顾我们,自己蹬着两条短腿飞快地从田埂上跳下,几下就把我们甩出去老远,等我好不容易连滚带爬地下到山脚,毛头已经在大喊着让一群精赤着上身的青壮在湖边集合,应该就是刚才在车水的那群人。
村子里也有一大群人狂奔而出,三毛和猴子也在其中,领头一人还没过湖就喊:“狼爷……消息树!”
毛头皱着眉头挥了挥手示意自己知道了,然后大声命令道:“一列纵队,跑步……走!”
那二十来个汉子马上齐齐转了个身,喊着号子从石头墩子上跑了过去,只不过这次的号子从“嘿嘿嘿嘿”改成了“一二一二”。
“快去拿家伙!”毛头刚过湖就喊,“都上这儿来干什么?”
众人又都跑回了村子,在昨天吃饭的祠堂后面的堂楼上拿出了武器,几支95式步枪、军刺和无极刀都还给了我们,而他们自己的武器是五花八门,大多是粗制的土枪,用的是火药和钢珠,甚至还有两杆古老、硕大的抬枪。但即便如此,枪械也是严重不足,大部分人使的还是砍刀和长矛。这些人行动起来却是有模有样,一点也不吵吵嚷嚷,队列一直都井然有序,看得出平时受了不少的训练。
没想到毛头还是个军事天才!当我在路上提出这一点的时候,毛头却满不在乎地摆摆手说:“嗨,这都是小说里学的。”原来看小说还有这好处……
长途跋涉,毛头就失去了速度优势,跟我们几个外来客一起落在了队伍后面,路上我把最新的情况给刚睡醒的三毛和猴子做了简短的说明。
“怎么我们到哪儿,哪儿就闹感染者?这一天安生日子都不让过啊?”三毛挥着手里的刀无比懊丧地说道。
我们还真是灾星,该死的感染者就像是追着我们跑一样。我在心里暗暗赞同三毛,嘴里却什么也没说……一切都只是巧合,我们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凭什么会让感染者特别关注?我摸了摸裤子里装着戒指和衣钩的绒布口袋,抿紧了嘴唇,继续默不作声低头赶路。
毛头虽然说得轻巧,但爬上那座大山还是费了我们不少的时间,上了山之后,我们又沿着高耸的山脊走了半个多钟头,远远地就看见董艳春迎了上来。
“什么情况?”毛头焦急地呼喊,“是僵尸出来了?”
“别那么大声!”董艳春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快步走到我们跟前,才小声地说道,“不是僵尸!”
“不是僵尸?不是僵尸你砍个什么树啊?”毛头纳闷地问。
“你们自己过去看看吧……就是要小心,别被下面人看见了。”董艳春挥了挥手,猫着腰往前走去。
“人?什么人?”毛头皱着眉头狐疑地跟我们对视一眼,耸了耸肩跟着董艳春走了过去,我们也猫着腰跟上。前面不远处就是那座悬崖,原本如巨蟒般绵延的山脉在这里就像是被砍了一刀一般直削而下,丹霞地貌露出的赭红色山石就像巨蟒身上的血色伤口。
我们猫着腰轻手轻脚走到悬崖边的一块山石后面,然后小心地探出半个脑袋向下一看,只见悬崖下方还是熟悉的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原,左右两边是高耸的铁丝网,但在荒原的深处,却有几道炊烟袅袅升起,炊烟下面,依稀有人来回走动,而且人数看起来还不少。
“给你这个,看得清楚一点。”董艳春塞过来一架十六倍望远镜,我接过来一看,发现果真如毛头所说,那个我们发现飞机的蛋形建筑已经不在,只剩下一片破烂的废墟,而在废墟一边,密密麻麻支着一片花花绿绿的帐篷,几堆篝火正在熊熊燃烧,很多人在帐篷和篝火间穿梭,男女老少都有不少,俨然是一个难民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