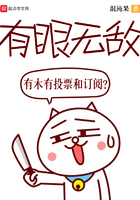爷爷在世时,绝对保持着在我们家的权威地位。我们家那时是四世同堂。我爷爷的母亲仍健在。爷爷和奶奶养育了九个儿女,自然是劳苦功高。爷爷体格健硕,又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不娇宠孩子们,印象中我的叔叔姑姑们都怕他。爷爷的话,在叔叔姑姑们中是有强大威慑力的。只有三叔有时候例外。这是因为在小时候发高烧,爷爷带他去打针,不小心给三叔打成了左腿小儿麻痹,成了一个残疾人。走路的时候要靠一根拐棍帮助,否则便站不稳。其他几个叔叔都相貌堂堂,有了在部队做了军官,有的做了老师,爷爷大概有时候也觉得心中有愧,便对三叔让了几分。
没想到这一让就让出了毛病。三叔虽然残疾了,但心劲很高。那时候刚刚搞改革开放,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叔虽然身体不行,但爷爷还是坚持把他供到初中毕业,先是在生产队担任会计,后来土地一承包,他便失了业,但脑子挺活络,领会上级的政策也快,便想当那中国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父亲所在单位给我留下了几百元的抚恤金。爷爷把这笔钱存入银行,存折就压在奶奶嫁过来时的箱底下。预备以后我长大了娶媳妇用。三叔不知怎么发现了这个秘密,便想打这笔钱的注意。一次,他趁爷爷奶奶都下地干活的功夫,把存折拿出来到银行办了抵押贷款。三叔当时是这么想的:等以后赚到了钱,再把存折拿回来就是了。
三叔拿着钱去做生意。先是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大堆衣服拿到镇上去卖,结果也没能赚得到钱。不久又改行养鸡。那时候正流行这专业户那专业户。他把他的养鸡厂设在原来生产队的破房子内,外边是一个装饲料的大缸,是专门放饲料的,买了几千只小鸡,一时间,平静的小山村热闹了不少。养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闹了一场鸡瘟,鸡死去了不少。还有一次,他出去办事,忘了把大缸口子封上,结果,回来的时候,发现一部分小鸡不见了,一看饲料缸,一大半都死在里边了。
三叔于是又改行了。和别人合伙做木材生意。去了一趟东北,没想到钱没赚着,倒差一点没回来。回到家里的时候,口袋里只余下了几元钱。我奶奶给他做好一碗面条,两个馒头,被他风卷残云解决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很少出门。
爷爷有一次到镇上去赶集,正好碰到了在银行工作的一个熟人。爷爷便问父亲那笔存款的情况,这一问爷爷才发现了事情的真相。气得连东西也顾不上买了,回到家里抓住三叔就是一顿狠揍。
那时,刚巧我二叔从部队转业回来,安排在市里工作,二叔便要三叔去市里学服装裁剪。三叔学会做服装裁剪后,开了一家店,生意渐渐地好了起来。再后来,残疾的三叔还在乡下找了一个媳妇,生了一个女儿。
爷爷去世前,三叔的女儿已经出生了。听说是女儿,爷爷很高兴,说:女儿孝顺,老三以后不用我操心了。
王小波的悲剧
远离家乡的小山村已经十多年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故乡的人和事逐渐在记忆中变得遥远了。但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至深。去年,我还在与家乡人的通话中打听他的近况。得知接近五十岁的他仍然是一条光棍。
他叫王小波。我记得当时他丑陋猥琐,一脸络腮胡。如果按照现在的审美观点,这应该是比较时尚的。
当时的村支书家造房子,因为是同一生产队,受支书老婆邀请,王小波和同一生产队几个青年一道去支书家里帮忙,支书家的三间大房子造好以后,出现了一件轰动全村的事,这件事便决定了王小波悲剧性的命运。假如,王小波知道他要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他绝对不会贸然行事。
支书家有一女儿,出于对其父亲支书权威的敬畏和支书女儿天生丽质的认可,支书女儿一直是被全村人公认的漂亮女子。据说,当时,镇里有不少国营工的父母都正在托人给支书女儿提亲,也许这时候,支书的女儿正沉浸在有机会嫁给城镇国营工、有机会变成城市人的喜悦里,所以她在给这些帮忙给自己家造房子的本村青年便多了一些按捺不住的喜气洋洋,坏就坏在别的青年都没有往别处多想,而王小波却想入非非了。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支书女儿是正在为自己献殷勤,也许是自己的勤快,是自己的络腮胡子迷住了支书女儿。
为此,在支书家的房子竣工的第二天,王小波特意把自己打扮一新来到支书家的新房子里,向支书老婆讲明了来意,我们不得不承认,王小波的这种提亲的方式有点超前,虽然在今天这已不算是什么事。但这在当时,王小波的思维绝对是空前绝后。绝对有点前不见古人的味道。支书老婆听着他的话一明白过来就觉得气血直往上冲。支书女儿是注定要嫁给城镇国营工的小家碧玉,但可从来没想过要嫁给王小波。在农村,支书女儿是处处高人一头,甚至有人说早有相面的算命瞎子为她算过一命,说她是命中注定的军官太太的命。一个长了一脸络腮胡子的家伙就这样一副德行,想娶她,这不是明摆着向被大家公认的大家闺秀的地位挑战? 支书老婆和支书女儿越想越气,支书女儿早已连气带羞,跑回屋里哭得泣不成声,自觉是受了奇耻大辱,支书老婆破口大骂,发一声喊,支书家的几个儿子包括支书的几个堂侄冲了上来,将不知好歹的王小波一顿饱打。
这一打,便把王小波全家打得几年抬不起头,打得王小波有神经病的说法不胫而走,打得王小波一辈子注定是一个不良青年,打得王小波一辈子打了光棍,打得以后谁家的女子见着王小波就像见着了大灰狼似的躲着走。
挨了这顿饱打的王小波消停了很长时间,然而事隔提亲事件后二年的一个冬天,王小波再次让人一顿狠揍。
这次挨打的原因说是他是耍流氓,心理变态。王小波在山上放牛,荒天野地的,他看着四下无人,便蹲在田地撩着屁股对着山间一条小路大便。为什么这样做,后来分析大概是不希望有人从小路走过来看到他的脸。他大概认为看到他的屁股不要紧,只要脸面不被人认出来。后来承认他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解释说就在他意识到有人而且是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孩子走过来时,他想躲藏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慌乱之中只好掉转了一个方向,这样,就把亮亮的屁股暴露在了女子的视线之中了——这成了他后来耍流氓的一个证据。女孩子的几个哥哥听说这件事后,又认为是对自己妹妹的侮辱,因为王小波有“求婚事件”的前科,他就这样稀里糊涂被狠打一顿,竟连申辩的想法都不曾有。
因了这件事,王小波找对象的事就彻底黄了。十里八乡没人提亲,名声臭了。就是远在几百里他家的远房亲戚在外地给他介绍一个媳妇,人家来了一趟,也不知怎么就听说了他以前的“风流韵事”而宣布告吹。
当兵前留给我记忆中王小波最后一次被打是被打得最严重的一次。这一次也给我的印象最深,它让那时才十多岁的我也甚至感到不寒而栗。原因是邻村—个17岁的高中女同学从山上放牛回来,这个长相斯文的女同学从山上放牛回来,和王小波家的牛走在了起。她家母牛和王小波家的公牛也走在了起。走在一起本没有什么事,但那段时间正是春天,是公牛和母牛的发情期。便发生了那一切。那女生早已羞得满脸通红了,找一根棍子想把牛分开,但又怎么能分得开呢,而王小波却因为看到了一场难得的好戏而手舞足蹈。据那女子后来说王小波还看着她发出了不怀好意的笑。这一笑就笑出了一场血战。
这女孩回到家里向母亲哭诉之后,其父亲带领全家老少手拿皮带锄头等工具,气势汹汹进了王小波家。两家展开一团混战,男打男,女打女,但力量相比悬殊得多,王小波一家最后被打得落荒而逃。尤其是王小波的母亲,连头发都被撕下一大片。
王小波彻底臭了,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一提到这个人,便会争相把满脸的憎恶和辱骂送给王小波,在这方面,她们的立场有着惊人的一致,这只能表明,王小波触犯了众怒,虽然他到现在为止还一次没有触犯过法律,充其量那只能叫“性骚扰”。
王小波还害了他全家。他的弟弟本想当兵,回来之后找上一个对象。但后来村里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给他。他的大妹妹在方圆十里嫁不出去,只好嫁到外地去。
王小波也不是什么好处都没有。他为当时的本村青年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同村的青年充分吸取了这类教训,老老实实生活,平平稳稳娶妻生子,乐哉悠哉地生活着。记得我上初中时放暑假在家,一天晚上去村里的池塘洗澡,不料却被一群大姑娘小媳妇抢了先。月光下,这些大姑娘小媳妇看到有人走上来,以为有人偷看,就一齐声骂了起来。我吓得赶紧往回逃。因为当时年龄还小,生怕人家说自己是流氓,心里害怕得不行,回到家里就一五一十地讲给爷爷奶奶听。一再强调自己不是故意的,难过得都快哭出来了。还想让爷爷奶奶向那些洗澡的大姑娘小媳妇解释解释。爷爷奶奶当然不去。最后告诉我,没事,人家肯定以为会是王小波在偷看。
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那些女人是否知道了是我不小心看见了她们。后来一直没人提起偷看她们洗澡的事。或者,她们真的又把这笔帐记在了王小波头上?
只有天知道了。
如果真是那样,我就有点对不住王小波了。
我只知道,王小波依然在家乡打着光棍,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业已去世。他后来在煤窑上上班,被砸断了一条腿,农活是干不成了,靠煤窑上的一点补助生活。
其实,王小波当年的行为按照现在的说法充其量是“性骚扰”,而动不动就打人的行为才是违法行为。
后来,我想,王小波在向支书家提亲的时候,也许是一脸的真诚,据说那个后来嫁到城镇上的支书女儿,经常被当国营工的老公打骂,过得并不幸福。她嫁的并不是真心喜欢她的人。
我经常在做这样一个假设,假如当时支书女儿答应了这门亲事,又是什么样一个结果呢!王小波在我们家乡的个人历史和弟弟妹妹的历史,都肯定会重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