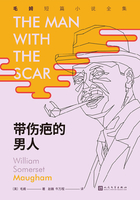“店伙计递来一碗白汤,我双手颤抖得接不住,汤水溅在桌子上,把手也烫了。本来我打定主意,如果到垭口赶不上,吃过饭就连夜继续赶路。现在知道他们就住在店里,我像从冰窖里爬出来似的,浑身发热,脸颊发烧,脑子里念头乱飞。
“我住的是大房子,通铺,整个屋子盘着一个大炕。客人不多,四五个人像平放的木桩一样躺在炕席上。屋里空气污浊,像烂泥塘里的水,汗酸、脚臭熏得人透不过气。越是睡不着,越是浑身不自在,身子底下不知有多少臭虫在倏倏爬,跳蚤在腿上乱蹦,蚊子嗡嗡地绕脸飞舞。
“我睡了一小会儿,也许只是打了一个盹,就起来在门口转悠。
“外边下了雨,天黑黪黪的。这雨能下大就好了,下大了明天他们就走不了了。我这么一想,雨真的下大了。不一会儿屋顶上响起刷刷的声音,屋檐上垂下闪亮的水帘。我抱起膀子靠在檐下,看着雨打在院里的泥地上,积起一个个水坑,然后顺着地势往大门外流。
“大房子对面是马棚。马棚左边是一个小院落。院子当中是井台。透过草泥垛成的院门,我从远处打量那排单间客房。一式的土瓦,木格子花窗,板打墙,灰白色的墙脚。看着那些关闭的房门,不知道她住在哪一间。
“天慢慢亮了。雨停了,天还阴着。车夫从马棚里走出来,提着桶到井边去打水。大房子里的客人也都纷纷起来踏着泥水到井台边去洗脸。
“我靠在屋檐下,盯着小院,我想让她一走出房门就能看见我。
“我虽然没见过林春长,可他一走出小院我就认出了他。一身藏青裤褂,大背头,一条怀表链子从纽扣垂到口袋里。那张脸比春生宽,身架也显得粗大,可一看长相就知道是林家人。
“我走到井边,把刚从井里打出的水往小木盆里舀。我一边洗脸,一边偷眼向小院看。他走到隔壁房间门口,敲着窗子喊,如,如!喊了半天才有人答应,可房门并没打开。
“吃早饭时他又去敲了一次,她的房门还是没开。天阴着,车夫没急着套车。林春长的房门一直开着。她不出来,我没法走近她的房间。
“有什么办法和她见面?怎么能让她知道我来了?我在院里转来转去,各种主意在我心里翻腾。
“我走出大门,在小街上走了一趟。垭口街像一条卧在两道丘陵中间的蚕,头枕东北,尾向西南,摆放着一片错落的房屋。杂色屋顶,白色土墙,山坡上夹杂着零零落落的窑洞。旅店背靠土崖,崖上长着苍黑的荆棘,崖下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小树林。
“我沿着荒草中的小路走到旅店背后,溜着墙根一间间往前数。那排房子的后窗离地很高,像堡垒上的枪眼一样悬在屋檐下。我从小树林里搬了两块石头垫着脚,勉强够着狭长的窗台。
“房门关着,屋里很暗。我趴在窗棂上,拿手遮着额头,过了好大一阵才看清屋里的情形。窗子下面是床,床上有人躺着。我壮起胆子在窗棂上敲了两下,然后对着屋里轻声喊:小如——小如……
“床上的人坐起来。当她扭头朝后窗看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的脸。她激灵一下跳起来,沿床走到后窗下。隔着窗棂,我们俩看着彼此露出的半张脸。几天没见,她显得又黑又瘦,眼窝深陷,两颊露出阴影。
“快出来!我在大门外等你。”
在恋爱的关键时刻,女孩总比男孩更机灵,更沉着。当父亲心急火燎地在旅店大门外徘徊时,母亲不慌不忙端着脸盆走到井台上,站在那儿慢条斯理地刷牙、洗脸,拿毛巾在脸上仔细擦拭。然后慢慢梳理那一头齐耳剪发,把盆里脏水泼掉,毛巾、牙膏、牙刷收好。
“林春长站在门口抽烟,她走到他跟前说,啥时候套车?他说,恐怕得过了晌午,路干一点才能走。
“她把洗漱东西送回房间,再一次走到他跟前。我到街上去吃点东西。他把手伸进口袋去掏钱,她说,我这儿有。
“她走进一个小饭店,我也跟进去。她要了一碗醪糟,我也要了一碗。我坐在她对面,看着她低声说,咱们走吧。我察看过垭口的地势,跟店里伙计打听好了路。从镇子出去,向东北是往西安去的大路,到三岔河往西,奔宝原……
“她看我一眼,等我往下说。
“我开始对她说我的计划。这计划在我心里盘算了一夜,为了万无一失,我把所有细节都想过了,还到镇子两头去看过了地形。
“咱们不奔东北,也不回陈官营。咱们过河往西,一直走到清浦,在那儿躲一天,然后折转来往东北。……让他们找不着……
“她默默看着我,那眼神让我心里发憷,说话也开始打结。
“马昌,我不会跟你私奔,我要光明正大地走。
“我不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跟大哥到西安,在报上登个声明和孙家解除婚约,让他回家有个交代。你也必须先登报离婚。
“可是……可是……
“你不离婚,我不退婚,我能跟你走吗?我算谁?你算谁?
“可是……到了西安,你大哥……
“你不用担心,谁也别想阻拦我。她把‘我’字向上挑了一下,声音提得很高。你到西安来吧。咱们在那儿会合。”
从宝原来到西安,父亲住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他从练习簿上撕下半页纸,按照约定,写了一张便条,贴在候车室外的留言墙上。墙上贴满了形形色色的字条,留着各式各样的文字。虽然他竭力想找个好位置,可贴上去之后,还是被花花绿绿的字纸淹没了。他不知道她能不能发现它。
“天皇皇 地皇皇 我家有个夜哭郎 行路君子念三遍 一觉睡到老天光……”在这些文字下面,他又写了几个英文字母,“D IGT LY MY YH”,本来他和她约定只写IGT三个字,表示“我已到达”,可在写的时候,他忍不住在信的开头加上了一个D,在后面多写了几个字母,他相信她能看懂这行字的意思。
在街上转了一会儿,到饭馆去吃了点东西,再转回来时,他看到墙上的字条已经被添上了五个字母“D IK MY”。他惊喜万分。她不但看到了留言,还留下了温柔的回信。“IK”是约定的回复,表示“我知道了”,其余几个字母显然是对他的信的回复。她在信的开头同样加了D,这让他心里充满温暖。他仿佛看见她站在候车室的墙壁前仰起头抑住内心激动读他写给她的信,“亲爱的,我已到达。爱你,想你,你的马。”看到这些句子她肯定被深深地感动了,抑不住以同样激动的心情对他说,“亲爱的,我知道了,想你。”一股甜丝丝的感觉使他忍不住笑出了声。他在心里默默自语,小如,你真好!小如,我爱你!他既高兴又遗憾。“如果不急着去吃饭,说不定能在这儿碰上她。”虽然他们约定了什么时候见面由她决定,可他还是很想见到她。
他当即写了第二张字条,“三叔 我住在北大街兴安旅社 大明。”
“我在下面添了D MY KY五个字母,虽然这有点大胆,可我还是忍不住把它写上了。”
小伙子一路走一路吹口哨,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笑意。走进房门,他仰面朝天往床上一躺,两腿交叠,一手垫头,一手举起香烟。用眼角瞧着鞋尖,长吸一口,撮起嘴唇,冲房顶吐出一串白圈,然后又鼓起两腮吹出一条直线。他吐得非常成功,五个烟圈被一条直线贯穿,在空中缭绕了很久才慢慢飘散开来。“亲爱的,想你,吻你。”反复咀嚼这五个字母传递的意思,他被浓浓的温情陶醉,不由得在自己腿上狠拍了一掌。
地址已经给她,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心爱的人突然推开房门出现在面前。这是一次甜蜜的等待,没有痛苦,只有幸福的思念。
“金钟烟厂办事处在北大街西边的胡同里,老家来的人大多在那儿落脚。那地方人多眼杂,我只能趁天黑才敢到胡同口去转一转。很想看见她,又不敢走近院子。
“她没到旅馆来。她在留言墙上贴了一张纸条:石瑞:我不日东归,见字速与二伯联系。秦。字条下面写着T、A两个字母,虽然这封信前面没加D,可我还是很高兴,她通知我明天(T)下午(A)见面。”
“登过报了?——这是她看见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只要她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心里就会紧张,说话也不利索。
“稿子……交给他们了,钱也付过了。……
“没说几号登?
“还没说。
“她又用那样的眼神瞥我一眼,得让他们马上登。林春长在等盘纸,货一到,我就得跟他走。
“你呢?你的……
“我要先看到你的声明。”
虽然太祖父为父亲算的卦是鸡年流年不利,然而按照《周易》的基本卦理,吉凶相生,否极泰来,不利藏在吉利之中,不幸预示着转机。在父亲出生后的第二个鸡年,他的经历差不多总是好事跟着坏事,坏事带来好运。在父亲保存的旧书里,有一本万年历。虽然翻卷了页边,经历了那么多劫难,可它一直被保存得很完好。这本万年历是民国二十六年的版本,应该是太祖父留下的。在乙酉年这一页里,能看到八月初五被圈在一个红墨水画出的框子里。虽然岁月使墨水变得灰暗,可那红色的印记还是清楚地围裹着这个日子。对照公元,它是1945年9月6日。白露刚过,秋分未到,天气应该还有点夏末秋初的暑热。看起来是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万年历上这样的日子数不尽数。当我问起这个日子时,父亲脸上已经看不出什么激情,他微带笑意,平静而安详。然而从他的神态我能看出,圈在书页上的这一天,是圈在父亲心中的重要标记。它深埋在父亲的记忆里。如今能有人和他一起打开这尘封故事,分享岁月的窖存,他脸上分明有一种安慰和惬意。
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两套年月符号。履历表上的一套,装在档案里,记载着他在人世间扮演过的角色;每个人心中储存着另一套日历,虽不轻易对人言说,却深藏着他的幸福与隐痛,标记住一生最难忘的时刻。我一直希望能够找到1945年9月6日这一天的《震旦报》,重读一遍父亲、母亲的声明。为此我查找了很多图书馆。后来听母亲说,我大舅林春长看到这天报纸后,让金钟烟厂办事处的伙计到街上去买,把西安城所有报摊、报童手里的《震旦报》全买光了,不要说现在,即使当年,要找到这天的《震旦报》也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