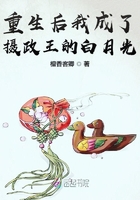父亲的目光在我脸上打转,我慢吞吞地系扣子,垂下眼帘不看他。他的衣服我穿起来有点旷。他转到我面前,伸手把我的衣领提展。
“瞧,这褂子他穿着也不嫌大。”
他看着我的额头,我看着他的下巴。
“你妈妈——她好吗?”
我唔了一声。
“你怎么这时候到这儿来了?现在还不到放假时候啊?”
“学校开运动会。放几天假。”
父亲盯着我的眼睛。
“到这儿来,跟你妈妈说了吗?”
我又唔了一声。
娘打好鸡蛋端过来。父亲坐在旁边。我知道他想听我说点什么,可我什么也不想说。
娘把我的手拉过去,放在她手里摩挲。不知是因为长大了,还是和她生疏了,她这亲昵动作让我很不自在。我把手抽回去,理着鬓边湿发。她像父亲一样用疑惑的目光打量我。我低头喝汤,一直没抬眼。
坐票车来的?
扒了一辆货车。
咋找到这儿的?
我到肖王集问了舅妈。
娘再一次伸出手,抚着我的头。
娃儿,是不是跟你妈怄气了?
我没吭声。
本来我有很多话,见了娘我想把心里的怨气全都倒出来,可当她抚着我的头问我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想说了。
父亲提上一小袋黄豆,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去。回来的时候,手里提一瓶油,一条猪肉。这条猪肉虽然只有窄窄的一绺,却柔软、鲜亮,油光光地照亮了小屋。看见这样鲜亮的肉,我的心情一下子好起来。
吃了肉焖的大米饭,我脸上的表情轻松多了,人也不再那样矜持。
父亲坐在小屋门外抽烟。娘凑到我身边,看着我的眼睛。她再一次拉起我的手,我乖乖地让她攥着。
出来没跟你妈说吧?
我笑了一下。
傻孩儿!你妈会急疯的!
我又笑了一下。
吃了一顿好饭,人的心情居然会变得这样平和,对母亲的怨恨一下子就烟消云散,只剩下一点惴惴不安。
晚上煮鱼吃。父亲把瘸二爷请来,把他的小桌搬过来,到供销点去打了酒。当他把一杯酒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知道在他眼里我已经长大,心里涌起一种庄严感。
我从没见过娘和客人坐在同一张桌上吃饭,更没见过娘喝酒。她那快活的样子让我感动。她坐在我旁边,看着我的脸,把酒杯向高处猛举一下,夸张地喊了一声,喝!好像没沾酒她已经醉了。
父亲把酒壶递给我,让我给瘸二爷敬酒。第一次担当这样角色,我有点紧张。没怎么出手,酒已经漫出来,流洒在桌子上。娘哈哈笑着说,傻孩儿!真是个傻孩儿!还有你爹!给他也敬嘛!父亲插嘴说,还有你娘。
能和大人同桌喝酒,我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在父亲的撺掇下,我喝了几杯。喉咙热过一阵之后,酒的魔力开始在我身上发散,眼前的一切变得热烈起来。灯光发虚,板凳在我身下摇晃。嘴巴不受支配似的想说话。打手势时把胳膊抡得很高。有一股豪情在胸中盘旋,不知想哭还是想笑。
喝过酒,记忆也变得不那么确定。记不清瘸二爷什么时候走了,大老黑卧在我脚边,摇着尾巴蹭我的裤腿。我只是喂了它两块鱼,它就变得这么温顺、亲热。
父亲面对鱼塘坐在小凳上,烟头的火光在他手里明灭。晚风习习,紫云英的香气沁人心脾,让我的头脑变得清醒。新出生的鱼苗像淘气的孩子,趁着夜暗浮出水面,塘面上一片唼喋声。我拍一下手掌,它们立刻逃进水底,转眼又倏倏游出来。
“我一直看着你,一直在揣摸。你娘给你做好吃的,她哄着你,想知道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可你真的长大了。你的眼睛不再那样透明,笑的时候也不像从前那样开朗。你站在塘埂上看着鱼塘,那副表情让人琢磨不透。
“孩儿,你出来几天了?你妈不定会急成啥样儿呢!从你进屋那会儿起,我就知道你肯定和妈妈闹别扭了……
“……
“她是不是把你管得太严啊?”
酒意拉近了我和父亲的距离,夜晚的鱼塘让他和我的交谈变得亲切。
“星期天我和叶子在河边玩,碰上一个女同学。我们在河滩里玩了一会儿。我妈知道了。她逼我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和她来往。她还找人家谈话……
“这么点事儿,你就离家出走?”
娘插上说,你和那女孩——有没有啥事儿?
本来我想用强硬的态度否认,可话说出来却很软。
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和我前后桌。
她叫啥名儿?
张丽娅。
她和你一块儿到河滩里去干啥?
我着急地说,不是说过了吗?我带着叶子在那儿玩,和她碰上了。
娘笑了,父亲也跟着笑。如果不是天黑,他们一定会看到我已经涨得满脸通红。我得承认娘和父亲很精明,他们知道我没把全部实情说出来。可我只能这么说。都是叶子这丫头惹的祸。我把她带在身边本来是为了不让妈妈起疑心,可没料到一个四岁的小丫头竟那么多嘴。一回家就说,我们到河边去玩了。哥哥和一个姐姐坐在苇子丛里。更糟糕的是,母亲不但知道我和张丽娅在河边约会,她还看到了她写给我的信。是个窄窄的纸条,我看过以后没舍得扔掉,把它夹在数学课本里。没想到母亲偷翻我的书包。我和她大吵一架,把门一摔就走了。
“孩儿,你马上该考高中了吧?这时候可不能分心哪!”
父亲的话和母亲的话一模一样,好像商量过似的。
娘不以为然,她甚至还有点高兴。孩儿长大了,女孩子喜欢他,有啥错?
爸,我不回去了。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话一说出来,娘和父亲都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娘说,那是你亲妈,她管你是为你好。不能为一点小事就说这样话。
“我用稻草给你打了一个地铺。这地方没有稿荐。咱们家乡的稿荐多方便!
“你躺下就睡着了。勾着头,蜷着腿,胳膊压在被子上。看你这副睡相,我很想伸手去摸摸你。恍惚间,我想不起你是怎么长大的?在你长大的过程中我在干什么?我关心过你?照顾过你?留意过你吗?‘眼看四十岁的人了,你怎么还像个孩子?’你娘常用这话取笑我。我不知道她说得对不对,我从没想过这三四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好像直到现在我还是刚从兴隆铺逃婚出来,在流亡路上盲目奔走的那个愣小子。我干过很多傻事,蠢事,可我没反省过自己。当你说要离开妈妈跟着我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还没想过怎样做一个父亲。爷爷活着的时候,我没想过怎样做孙子;恋爱了,结婚了,我也没想过怎样做丈夫。
我自顾自地走着,不知道伤害过谁,不知道对谁有什么歉疚。即使在采石场打石头,蹲在肖王集大队部门外的墙根边等派义务工,在响塘湾看鱼塘,我也没后悔过。可你的话触动了我,戳痛了我心里的暗伤。我坐在地铺边看着你,心里对自己说,马文昌啊马文昌,你这个自负的家伙,活到三十九岁,在人世间你有什么用?你的儿子十六岁了,他躺在这儿很长的一条了,他已经开始恋爱。可你连一天也没抚养过他,一天也没教育过他。要不是这个夜晚,你甚至没和他认真谈过一次话。春如她真不容易,真够坚强!我除了带给她伤害,什么事也没为她做过。还有刘英,卓娅,我的女儿马上十岁了,我为她们做过什么?
“我凑到你娘跟前,小声和她商量。
“你娘说,孩子也不是物件,说送人就送人,说要回就要回。眼看麦子熟了,出来两年,我也想家了,你那点破事儿,听说现在已经没人追究了。不如咱们趁这时候和长安一起回家吧。
“风吹动草帘上的叶梗,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你沉睡在我床前的地上,占满了小屋里这块空地。我把你的胳膊放进被子,没过一会儿它又伸出来。
“其实我心里早已拿定主意。即使她不这样说,我也会带你回去。我不能再让你离开你妈妈。
“你娘把手探进稻缸去摸了摸。明天把它背到碾米机那儿去打了吧。”
其实我并不是真想离开母亲。离开她的第二天我睡在异乡汽车站的地上,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想她。我也开始想张丽娅。我很沮丧,很懊恼,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儿。起初不过是赌一口气,出来之后就没法回去,只好越走越远。
当父亲把稻谷打成米,装在袋子里;把铺盖卷起,连同锅碗瓢勺一起塞进浅筐;娘背起小包袱,把一罐咸菜交到我手上,我的心情安定多了。有他们陪我一起回家,我不用再担心怎样跟母亲说。
娘悄悄问我,那女孩长得咋样?
就那样。
比丁香好吗?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说。丁香和张丽娅根本不一回事。
娘笑了,丁香比你大两岁,她属猴。这女孩多大?
我不知道张丽娅多大,也不知道丁香多大。
娘的话勾起了我对肖王集的想念。如果不离开肖王集,每天和丁香一起上学放学,我当然不会认识张丽娅。即使认识她,我也不会和她这么好。父亲、母亲和娘,他们不知道进入县中的最初日子我是多么孤独、苦闷、烦恼。一切都那么陌生,周围全是不认识的面孔和冷漠的目光。乡下的功课和城里是那么不同,为了跟上课程,母亲让我留了一级。我的名字第三次被修改,这次改得比任何一次都彻底。我既不是马长安,也不是肖长安。在班里的点名册上,我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每次点名我都会犹豫一阵子,不知道“曾安”这个名字是谁。回到家里我同样感到自己是个陌生人。和叶子妹妹比,母亲对我的关心、爱抚有几分做作。
她的表情、话语、举动处处和娘不一样,我的习惯也不合她的要求。连刷牙、系扣子的姿势她都看不惯。那时候,张丽娅脸上的微笑让我感到温暖;她温情的眼神让我觉得亲切;体育课分组的时候,我一个人站在队外,她叫着我的名字,把我叫到她的小组里。她是班里第一个叫我名字的人。她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无论人群多嘈杂,我都能分辨出她的声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越来越在意她。上课时我感觉到她在看我的背影,下了课,她总在我眼前转悠。做课间操,我会有意无意凑近她,看她伸臂、踢腿,感受她的气息,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快乐。无论走路,跑操,伏在桌上做作业,还是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她的脸庞,她的眉毛、眼睛、嘴巴、酒涡,举动和声音,都让我想念。
当我坐上回家的班车,挤在娘身边的时候,我对张丽娅的想念比对母亲更强烈。我可以给母亲写保证书,可以骗她说我不再和张丽娅来往,可回家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见到她,只有见到她我的心才会安宁。
娘安排我们在车站吃饭,就近找了一家小旅馆。把行李、杂物存放下,洗了脸,换了衣服。娘把大米倒出一小袋,让父亲提着。
母亲看到父亲时,他已经不像一路上担着行囊匆匆赶车时那样狼狈。他穿着一身旧干部服,虽然衣边、袖口都已经磨破,却浆洗得很干净,也很板正。
对父亲和娘的到来,母亲好像并没感到意外。她平静地看着他们。我把手里的东西递给她,朗声说,这是俺娘腌的箭杆白,可好吃了。她着意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我摊开手,咧嘴笑着,让她看我既没伤着、碰着,也没饿着、冻着。如果她知道在响塘湾每天娘给我做好吃的,我的嘴和脸都变得油亮了,她肯定会吃醋。
父亲把米袋放在地上。她转头看着它。
给你捎了一点大米。
她没说客气话,只是感叹了一声。
叶子走过来,眨巴眼睛看我。我俯下身,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学校刚开过晚饭,晚自习的钟声还没响。趁母亲忙着招呼父亲和娘,我拿上书包往外走。
母亲用严厉的目光看着我。那么要紧?脸也不洗,衣服也不换?
耽搁了两天功课,不定有多少作业呢!
也不饿?
我们在车站吃过饭了。
“你一走,你妈妈的脸马上黑下来。儿子一回家就匆匆忙忙往外走,她脸上挂不住失落。一个刚强的人,在儿子面前无能为力,憋着满肚子火气,还要用平静的口气和我们说话,以春如的性格,我知道她心里的滋味。
“你娘站在屋里打量这个房间。这是两间平瓦房。一看就知道迎门那张小床是你的。上面放着你的衣服和书。
“你娘的眼睛在你床上转悠,她的目光让你妈妈不自在。
“瞧这乱七八糟的样子!一回来就乱扔东西,一天不知道要给他收拾多少遍。
“还不是跟他爹一样,从小伺候惯了,什么心也不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