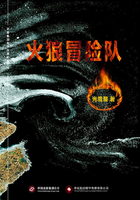娘突然哭起来,哽哽咽咽说不出话来。娘一哭,我也哭,眼泪顺着我的脸往下淌,我伸出手在下巴上不停地擦。
母亲把我拉到跟前,一手抚着我的肩膀,一手替我擦泪。我哭得更厉害,娘也哭得更厉害。
哭过一阵之后,娘把我招到床前,用布帕把我的脸擦干净,拉着我的手。
“长安,你看你妈——她对你爸的感情比娘还深,她惦你惦了这么多年。要不是亲你、惦你,她为啥这时候来接你?她是怕你在乡下受罪,怕你耽搁了学业。”
我又哭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不怕饿。跟着娘我什么都不怕。上学不上学无所谓。我哭着说,我不,娘,我不怕……
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站到了我身后。他抚着我的头说,长安,听你娘的话,啊。你是个中学生了,应该明白道理了。跟你妈到城里去,不光是不挨饿,往后前途也会好些。难道你愿意一辈子待在乡下?
我把头梗了一下,从他的手下摆脱出来。我愿意!我就愿意在乡下!我不会像有的人那样……把娘抛下不管。
娘大喝了一声,长安!
长安,把你的户口转到县城,你就能吃上商品粮……
我不稀罕商品粮!我没吃商品粮也长这么大。
母亲把我拉到怀里,抚着我的头,摸着我的脸。我把头贴在她胸前哭。我喘着气说,我走了,娘你会不会饿死呀?
娘不会饿死。你爸也不会饿死。娘要看着我的长安长大成材,以后做大事。
母亲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粮票,一卷儿钱,放在床头小桌上。
走出村,我一边哭一边回头看。父亲站在村口看着我们。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父亲也会这样让我牵肠挂肚。我曾经在心里怨恨他,觉得他不应该插进我和娘的生活,分走了一份娘的关爱,给我的快乐童年抹上阴影。可在离开肖王集的时候,我明白了,其实我不只舍不得娘,也放不下父亲。
星期日你回来看娘,城里到肖王集也就三十多里路。
母亲这样说,我反而更伤心。万一我回来见不到娘、见不到父亲了呢?
我跟在母亲身后,独自沿着路边走。我用脚踢着干枯的草丛,一只手不断在脸上抹泪。
“你爸回来了。他一声不吭地站在我床前。孩子一走,两个人好像更亲近了。
“我把衣服穿好,穿上鞋,站在床前聚聚精神。
“他看着我的脸说,咋样?你能起来吗?
“我用手拢拢头发,把裤腿提展。无论如何得想法出去找吃的,咱们饿死了,长安回来就见不到他爹、他娘了。
“我走到小屋门口,身子探进门里。五叔,你能起来吗?
“吃了点东西,身上有点劲儿了。
“你起来,烧点水喝喝。把这点粮票和钱拿上,到古庄店镇上去买顿饭吃。别心疼钱,也别吃太饱,太饱了会出事儿。
“你和文昌咋办?
“我这就带他出去找吃的,你别替我们发愁。
“看着五叔往外走,我回过头说,文昌,你记住了,这两天别人都在偷割地里的豌豆秧,咱不去。那是队里的庄稼,集体财产。村边的榆树皮咱也不能去剥,那是队里的树;地里的田鼠,人家挖,咱不挖,挖坏了庄稼说不清楚。你当了多年干部,应该知道,集体财产别人动得,咱们万万不能动。
“这个浑货低着头,脚在地上跐。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喜欢听,可这都是为你好。人要懂得在哪山唱哪山的歌,演啥角儿唱啥角儿的戏……
“好了,好了!你说咋办?听你的,还不行?
“你拿上小铲子,跟我走。
“文昌拿着铲子,我挽上篮子。
“大雁粪你吃过吗?
“在朝鲜战场,我吃过马粪。
“我笑了一下。还真小看了你。昨晚我想好了,南坡那片滩地,年年都有大雁在那儿过夜。灾荒年的时候,我娘带我去拣过雁粪,有时候能拣半篮子。拿回来在锅里焙干,吃着像菜饼子,比马粪好吃多了。
“听我这一说,这个浑货来了精神,虽说腿不利索,可比我走得还快。
“南坡那片芭茅丛里,大雁粪都是昨晚留下的,没费多大工夫就拣了小半篮。没有锅,摊在瓦盆里,几把火焙干,就着开水吃。这个浑货吃得满脸通红。
“咋样?好吃吧?
“比马粪强,比糠饼子强。
“别吃多了。给五叔留点。
“天都快黑了,五叔怎么还不回来呀?古庄店也不过八里路。
“饿坏的人,八里路是容易走的吗?”
“太阳落下去了。这一天过去了。这一天好像很长,经遇了很多很多事。长安一走,屋里冷冷清清,今晚咋过呀?
“我站在堂屋门口说,文昌,我看你不如搬到堂屋来住吧。
“这个浑货有点忸怩,我睡相不好,还爱打呼噜……
“你拿什么糖啊,叫你过来就过来呗,我能吃了你不成?把你的被子拿过来,摊在我旁边。
“我站在廊檐下往外看,天都黑了,五叔怎么还不回来?
“文昌挟着被子和我一起站在堂屋门口。会不会出什么事啊?八里路,走得再慢,这时候也该到家了。
“我坐在床边解扣子脱衣服,这个浑货磨磨蹭蹭不好意思。我笑着说,把衬褂脱了吧,白天黑夜穿,不结实了,省着点吧。我在他额上点了一指头。咱俩成亲十六年,今天头一次圆房,白天给你弄了那么多好吃的,看你晚上还有啥说?
“这浑货垂着头不敢做声。我哧一声笑了。不管办成事儿办不成事儿,咱俩总算睡在一张床上了,从今往后,你再不讲理也不能说咱俩不是夫妻!
“话虽这样说,那晚上我可没心思和他办事儿。天黑,屋里没点灯。窗外冷冷清清。五叔没回来,我心里揪成一个疙瘩,整夜听着院里动静,天不明就起来了。我先到五叔屋里去看。屋里空空荡荡不见人影。
“这事儿不对劲儿,我到镇上看看去。
“我和你一起去。
“你的腿不好使,在家省点气力吧。
“我一定得和你一起去。万一有什么事儿……
“烧点开水,把给五叔留的雁粪吃了。
“古庄店这八里路还真难走,歇了一歇才到。进了镇子,老远看见供销社食堂门口排着很长队,我心里越发不安。
“我从人群里挤过去,走到卖票员桌前。
“李妞,看见我家五叔了吗?昨天晌午我让他来买饭吃。
“那个穿蓝长袍腰里扎黑缠带的老头儿?
“对。就是他。
“他下午来,哪能买上饭吃?咱们食堂一天只有二十五斤粮食的指标,不到半晌就卖完了。
“那他到哪儿去了?
“他回家了呀。
“买饭的人嘟嘟囔囔叫嚷,人们怕我插队,瞪着眼冲我喊叫。李妞低下头去忙她的事。
“从人群里挤出来,文昌跟我走到路边。看我脸色不好,他扶我坐在供销社门口的台阶上。芝兰,别着急,你先坐下歇会儿,咱们想想再说。
“我真糊涂啊!我咋能叫他下午来买饭吃呢?
“那不是下午,那会儿还不到晌午。你怎么会知道食堂的饭限量卖?
“我看五叔是没指望了。空着肚子往回走,八里路,他走得回去吗?
“你别着急。歇一会儿,咱们沿路往回找。
“到这会儿,这浑货显得蛮有见识。他说,你把粮票给我,我先去买点吃的,要不,咱俩哪有力气去找五叔?
“食堂门口排那么长队,你能买到吃的吗?
“这儿职工食堂的司务长是县委下来的,我去找他想想办法。
“要是买到了馍,你可要揣到怀里,别让街上的饿汉给抢走了。
“这算让我又欠这浑货一份人情。要不是他,说不定我也跟你五爷一样,口袋里装着粮票,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五爷的尸体是在离古庄店三里地的路沟里找到的。脸朝下,侧着身子,好像并没有多少痛苦。大概他走累了,想坐下歇歇,坐下之后就歪倒了,没有再起来。那时村庄里的猫啊狗啊之类动物,不是进了人的肚子就是没了气力,老五爷在野地里躺了一夜,尸身完好无损,没有受到任何侵犯。父亲解开他右腋下的扣子,翻开袍子大襟,在贴身口袋里摸到了娘给他的粮票和钱。老五爷活了六十多岁,为马家劳碌了大半生,临死不但给我们省下二斤粮票八角小票子,还省下了棺木和丧葬的麻烦。娘和父亲没有力气把他抬回家,也找不到人安葬他。即使回到村里,也不会有人帮忙。活着的人谁肯为死去的人贴上自己最后那点气力?
“还是这个浑货,到古庄店借了把铁锨,就着路边,挖个浅坑把他埋了。
“回家之后,他铁青着脸,一整天没说话。我知道他和老五叔感情很深。小时候,五叔经常背他去赶会,带他去捉蚰子、逮鹌鹑。可现在,一个人说没就没了。人活在世上,有啥意思啊?”
“虽说他已经搬到堂屋来住了,可他还是喜欢一个人待在边屋。他伏在窗前桌子上,手里掰弄一张报纸。那是古庄店供销社司务长给他包馒头拿回来的。他千方百计弄报纸,就为的卷树叶当烟抽。肚子可以饿着,嘴里的烟不能断。
“看他转颜失色的样子,我走过去,伸头瞧瞧报纸,再瞧瞧他的脸。瞧你这张脸,涨红得像挨了谁的耳刮子。报纸上有啥东西惹你这么生气?
“他用手指弹着报纸,大声嚷,你看看!你来看看!
“我把他手里的报纸拿过去,凑着窗口的亮光。
“食堂饭菜花样多,人人争夸公社好。
“他伸出手指点戳着下边一行字,瞧这儿,肖王集公社食堂饭菜一个月不重样……
“我随手把报纸扔在桌上,你呀,报上随便说说,你当什么真?
“报纸能这么胡说八道吗?停伙个把月,人都饿死了,还说饭菜天天不重样!
“肖王集这些天饭菜就是不重样嘛!今天榆树皮,明天豌豆秧,后天说不定就吃老鼠肉了,人家也没瞎说呀!
“他们这是在欺骗中央!欺骗人民!
“文昌啊文昌,他们骗谁不骗谁,犯得着你管?从前你坐在机关里,不是也喜欢听这样的话吗?要是你现在还在台上,有啥办法能让他们不吹牛、不说瞎话?咱们的日子还得咱们自己想法儿过。有这个精神生气,不如到地里转转,说不定能拣个大雁回来,也能改善改善生活。生这样气,耽搁自己的事儿。值得吗?”
“我以为这样说说就完了,他身上那股邪劲儿再大,还能把报纸怎么样?谁知这浑货闹起人来还真叫你猜不透、防不住,我把脑袋想飞,也没想到他真敢给上级写信。
“要不是丁香她妈给我送信儿,我还蒙在鼓里啊。
“丁香她妈跟我说,你家那个浑货又惹事儿了!
“我当时不大相信。这些天他一直跟我在滩里转,没见他干什么呀?
“他给上面写信,说咱们公社欺骗上级。丁香她爹被叫到公社去,高书记把信摆在他面前,他都看过了,还能假呀?
“这个浑货!他什么时候写的呢?
“这事儿可闹大了,县里叫公社追查。幸亏王学斌还不知道。
“这都是你老爷的罪过呀,要是当初你老爷不让他读书,让他一个大字不识,老老实实在家种庄稼,他就不会拿那点儿文才惹祸,这辈子也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回到屋里,我什么话也没说就开始收拾东西。
“我把换洗衣服包好,床上的被子捆成一个行李卷。
“那浑货傻愣愣地跟在我身后问,你这是干啥?
“我把行李捆好,扁担递给他。走吧,咱们下湖北去。
“现在走?
“现在不走啥时候走?
“这时候咱们不能走。我给省委、中央写了信,上级会来了解下面这些情况的。
“我在他额上戳了一指头,你以为你是谁?你把天戳塌还能见着老天爷?我真服了你了!你啥时候写的?从哪儿弄的信封、信纸?咋寄走的?这么透钻的脑子,为啥不往正经处用?唵!你这疮疤还没好,就忘了疼?没想想,当初如果不是给上级写那份报告,你今天至于混到这一步吗?
“这浑货手提扁担,任我推搡,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你不想走,是不是?想等人家来请你?采石场的烂菜汤你还没喝够,是不是?你等着人家来请你马文昌去吃小灶,不掏钱,不拿粮票,对不对?你想学小邹,见了阎王也不低头?
“小邹?邹凡?他怎么了?
“春如没跟你说?
“她只说想把长安带城里去,没说别的。
“小邹已经没了!你想跟他学吗?跟你说了多少遍,叫你不要惹事,不要惹事,你怎么不长心眼儿呢?五叔死了,长安走了,你再有个好歹,叫我怎么过?你说!
“这个浑货站在那儿不吭声。
“我把扁担从他手里夺过来。行!有志气你站在这儿别动!看我一个人挑不挑得动这两个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