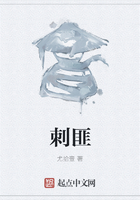从那时起,在娘跟前,谁也没再提起过爹。
“她从朝鲜回来那天我刚从医院转到招待所。我到街上去买了牙膏、牙刷往回走,看见她背着背包、提着提琴,从3518医院那边走过来。我从背后把她的琴盒掂过去。她吃了一惊,转脸看是我,笑着在我头上抹了一把,伤好了?
“不好还能住招待所?
“我提着她的东西往回走。她说,你这是去哪儿?我说,到街上找个旅馆去,别住招待所了。她说,那哪儿行?我是军人。
“你不是请假了吗?
“请假怎么了?请假就不是军人了?
“你不会换身便衣?
“她从鼻子里嗤了一声,马文昌,你还是支队教导员呢,我又不是逃兵,又不是犯了错误,干吗换便衣呀?
“我不想一见面就跟她闹别扭,可那会儿我心里很烦。
“你说咋办?招待所的房间是四个人伙住,外面冰天雪地,咱们坐哪儿说话?还坐在招待所走廊里?
“她扭头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昌,怎么了?……我看你今天有啥事儿吧……
“我倔强地转过身说,走吧,找个饭馆坐坐,总行吧?
“我们找到一家朝鲜饭馆,在楼上找一张靠窗桌子。天很好,街对面屋檐上的雪亮得刺眼。她看着我的脸说,咋?事儿办得不顺?
“我从口袋里掏出区政府寄来的离婚调解信。看看吧,她不知从哪儿给我弄出个儿子,真莫名其妙!
“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看信的样子很紧张。
“我心里生出一点愧意,觉得不该见面就说这事儿。我干笑了一下,解嘲说,我从来没跟她同过床,哪儿来的儿子?
“你不知道?
“我真的没跟她同过床啊。
“她写信什么都没跟你说?
“她的信都是六叔写的,几句套话。
“你爷爷去世她也没说?
“我的心猛地坠了一下,我爷爷……
“你爷爷五年前就不在了。你走后他就不在了。
“我盯着她的脸,你——怎么知道?
“她把手里的信放下,慢慢推给我,你就没问我是怎么离开家,怎么参军,怎么知道你的地址的?
“我张口结舌呆在那儿,傻看着她的脸。上次见面,在一块只待了两三个钟头,包着饺子说着话,只顾得给她说我的经历,还真没来及问她。
“我在你家住了一年。在你住过的密室里躲着。她卖了你家几亩地给我做路费,我才能出来找解放军。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她。
“那孩子,他是狗年出生,兰姐叫他小狗儿,我给他取名叫长安。马长安。
“我狠狠地盯着她,恨不得把她的胸膛看穿。这么说……
“你不问我为啥给他取名长安?
“我和她互相盯着看了一阵。这么说……
“她的头向下稍微动了动。看见他,你就知道他是谁的孩子了。
“我的手在桌下狠狠抠着膝盖,脚掌使劲蹬着楼板。”
“从饭馆到招待所,一路上我们谁也不说话,谁也不看谁。我把她的东西放下,就回自己房间了。
“我点着一支烟,仰面躺在床上,看着顶棚,脑子里像一锅滚开的糊粥。一个小家伙的影子从糊粥里冒起来,在头顶上漂浮。浮起来,沉下去;沉下去,浮出来。长安,狗娃?这是怎么回事儿啊?真操蛋!我的头晕起来,胸口闷起来。我忽然想起爷爷,他翘着胡子,咳嗽着,严厉、慈爱的眼神在我眼前闪。我想起了文盛,想起了老五叔。泪水涌出来,模糊了我的眼睛,哽咽的声音从喉咙深处发出来。
“我把棉军帽抹下来,攥在手里,在脸上蹭。
“午饭开过很久我才从床上起来。走到走廊里,看见她坐在火炉边,手里拿着捅火棍,眼睛看着火炉。和除夕那天一样,炉子上的铁壶嗞嗞响,蒸气在她脸前飘。我走过去,蹭着她的肩膀,站在她身后。她扭过脸看着我。我伸出一只手把她从凳子上拉起来,走吧,咱们上街吃饭。
“走出招待所,她说,咱们走走吧。
“我们俩把棉大衣领子竖起,帽耳巴放下,沿着一条冰冻的小河向郊外走。太阳正往下落,寒气浓起来。雪地不再耀眼,风显得更冷,河边林木灰蒙蒙的。那是北方的树,高俏,挺拔,枝杈向上,在风中摇曳。
“他们在土地庙没抓到你,大哥当时就逼我去重庆。我怀着孩子,能去吗?我知道这么做对兰姐太过分,可那是你的孩子,她不会不管。那时候我没处投靠。
“我把她的手拉过来,揣进大衣,攥在手里暖着。
“说真的,文昌,兰姐她不像你的女人,更像你的母亲。
“我吃惊地看着她。我忍不住伸出手指在她眉棱和脸颊上摩挲。我把大衣敞开,把她拥进怀里。我们俩面对面站住。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有点灰暗。
“兰姐她早已把自己看成是马家人,离婚后她怎么办?
“我从前没打算继承家产,现在也不需要,全给她好了。
“她俯在我肩上不说话。过了好大一会儿,声音低哑地说,这不是财产的事儿。她今年三十岁了,对吧?她还能找个合适的人吗?……
“我紧紧拥着她,嘴唇凑近她的耳轮,春如,叫你受委屈了。咱们找个旅馆,今晚就结婚。
“瞧你!又胡闹了!现在你是共产党员,志愿军支队教导员,要结婚,必须等报告批下来。
“咱们是自由恋爱,为了婚姻自由、为了解放,参加了革命。我在报告里写得很清楚。
“那你急什么?五年都等了,还在乎这几天?”
“第二天我让她陪我一起到邮政所去给兰姐寄钱。她问我,信是怎么写的?我说,我让她给孩子买点东西,替我给爷爷上坟。她冲我嗤了一声,你这人真不可救药!兰姐给你守家,为你做那么多事,你从来就没想过她?
“我愣住了。我真的从没想过她。
“就是你家的丫头、佣人,也该想到呀。她狠狠地瞪我一眼,走!给她买件皮坎肩寄回去。这儿的皮货多好啊!钱不够,我这儿有。
“逛了皮货店,买了皮坎肩,她又要逛百货商店。百货商店刚成立,跟从前的京货铺差不多。迎门是木柜台,柜台上摆放着布匹。往里走,是鞋帽、袜子、毛巾。她在钟表、眼镜柜前站下,手指着一块怀表说,能看看吗?售货员把表拿过来。她把它翻来倒去看,把表链子摊在手掌上打量。售货员的脸色不太好看,我用胳膊撞她。她像没看见我的眼色似的,把表盖弹开,看着表盘上的指针说,能把时间调准吗?售货员冷淡地说,要买就给你调准。
“她把它拿起来,放在耳边听了一阵,扣上表盖说,多少钱?
“我忍不住插嘴说,曾超,咱们该回去了。
“她抬起眼睛瞟我一下,掀起军大衣往外掏钱。
“我惊奇地看着她,你真打算买它?
“她又抬起眼睛瞟我一下,我只好闭上嘴,站在一边不说话。
“走出百货店,她一路没理我。走进招待所走廊,她站下说,手!
“我把手伸出来。她把表拍在我手上说,拿去!
“到这会儿我才明白,她是在给我买结婚礼物。我又感动又无奈,咂一下嘴,春如,买这玩艺儿干啥呀?
“她把表一把抓回去,板起脸说,行!不想要,别勉强!
“我连忙追上去,拉住她的手,不让她回房间。
“我是想,咱们都是革命军人,咱们的爱情应该……应该……
“她使劲把手往外挣,我使劲攥紧她,听我说呀,春如!曾超!
“我拉着她,又回到街上去吃了一顿饭。吃完饭,我也到百货商店给她买了一支金星金笔。她高兴起来,拉着我的手,到布匹柜上买了一床印花布床单,两个绣花枕套,两块亚麻布手绢。我得承认,在买东西上她很在行。东西都很漂亮,也不贵。她买东西时那兴高采烈的样子,让我看着很开心。
“往回走时,天已经黑下来,路上人很少。我用大衣裹着她。她拉着我的手,靠在我肩膀上,不断用额头蹭我的腮帮。
“记得下马台吗?伏牛山里那个小村?你把怀表留给了房东。打那时起我就一直想,如果将来没机会把它赎回来,我就给你买块新的。
“走到招待所门口,她突然顿一下脚,瞧!忘了买糖果!我在柜台前都看好了。那种沈阳产的水果糖,挺不错。
“我看咱们得早点给招待所长说,让他准备一间房。结了婚总不能还和别人一起住大房间吧?”
“我到政治处去。政治处主任是河南人,看见我总是很亲热。
“来催报告,是吧?着急了?我看见你对象了。洋气得很哪。那么好的对象,谁看着不着急?别着急,伙计,还有两份函调没来。材料一到,我马上通知你。
“我连忙说,不急,她请了十五天假,还有时间。”
组织上对父亲的结婚申请没拖太久,母亲的十五天婚假还差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被批准结婚,起码还能和父亲一起共度五天的蜜月。在1951年那样特殊时期,对两个革命军人,这已经是很奢侈的假期了。
在母亲假期的第十天下午,政治处主任来找父亲。那时他正和母亲一起逛街。这条街他们已经逛熟了,闭上眼就能说出哪个店挨着哪个店,哪儿的大饼好吃,哪儿的大骨头汤香。在街口,两人发生了争执,母亲说到朝鲜饭店去吃拌面,父亲说到老马家吃羊杂碎。母亲说,咱们确卡,谁赢听谁的。他们站在街边廊檐下确卡,剪、包、锤来决定输赢。母亲出剪,父亲也出剪,母亲出包,父亲也出包。最后母亲赢了。父亲没坚持住,他改了锤,就输了。当两人转过身准备去吃拌面的时候,招待所的小卞走过来,她说马教导,李主任在找你呢,让你一回来就到办公室去找他。
父亲高兴地说,肯定是报告批下来了,你自己回招待所吃饭吧。
母亲一个人回招待所。拌面和羊杂碎都没吃。她在招待所食堂买了两个馒头,用搪瓷缸打了一缸玉米面糊粥,为了表示庆祝,她还特意买了两份肉菜,放在走廊炉火边,等父亲回来。
“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李主任正打电话。他把电话打完,转过身打个手势让我坐下。我觉得他不像往常那样热情,既没开玩笑,也没寒暄,一副公事公办的神态,冷冰冰的样子让我很不自在。
“我把已经插进口袋的手拿出来,决定不给他掏烟抽。
“你对象原名叫林春如?
“我在报告里不是写了吗?
“她为啥改名字?
“他的态度让我不耐烦,人怎么一转脸就变成这样?
“我咂了一下嘴。报告里不是写了吗?她想和家庭划清界限。
“没别的原因?
“我看着他的脸,他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像块木头,眼睛直盯着我,像看一个犯人。
“还有什么原因?
“他拉开抽屉,把一份盖着红印章的材料递给我。你自己看看吧。
“我急匆匆地把几页纸翻了一遍,当时就傻在那儿了。
“老李脸上的表情松弛下来,口气也缓和了一些。
“这情况,你不知道?
“不知道。
“她没给你说过?
“没说过。
“你看——你们还能结婚吗?
“我的头脑在那瞬间失去了记忆。怎么回答,怎么走出办公室,全都模糊不清了。”
“我走到她面前坐下,什么也没说。她用勺子在搪瓷缸里搅,我把手放在膝盖上。
“她抬起头看着我,我脸上也像老李一样没表情。
“她把勺子放在搪瓷缸里,把热乎乎的玉米糊糊递给我。我端着瓷缸,隔着热气看着她。
“春如,在烽火店,你被民团抓走后是怎么出来的?
“我大哥把我接出来的呀。
“他没说什么?
“接出来他就把我送回老家了,还能说什么?
“他没说在报上给你登了‘自新声明’?
“自新声明?在报上给我登了自新声明?她转过头,眼睛像着了火,谁说的?李主任说的?
“材料我看过了。有组织盖章。
“你相信,是吧?他们相信?
“她盯着我的脸,我抓住她的肩膀。春如,你好好想想,是不是你大哥替你发表了那份声明?
“她好像什么都明白了。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会发表那样的声明呢?
“我攥紧她的手,想把她拉进怀里。她甩开我,站起来说,好了!我回部队去。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我得弄清楚了!
“曾超,你冷静点。
“你去冷静吧。我现在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