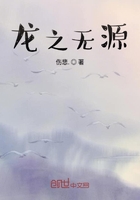鳌翔决定去堵铃木家的门。因为法律不能马上保护他,他又不能触犯法律,在吃过三份大肥肉的面条后,鳌翔做出了以下决定:态度和蔼,不急不躁,苦口婆心,不卑不亢,朝九晚九,赖着不走,不要回钱,决不罢休。
鳌翔按照铃木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他家。本以为是大宅子,眼前的却是栋旧楼房,铃木就住在这其中的一套公寓里。
站在门口,鳌翔把手指放在门铃上,突然犹豫了一下。他站在那,把想了一晚上的台词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又想象了一下铃木如果不还钱,自己将会遭到大老板怎样的斥责?
进而胡思乱想,自己的人生因为这个挫折从此一蹶不振,没工作、没房子、没汽车、没老婆,最后再加上一个没出息。
想到这里,鳌翔爆发了,他已经无暇再为铃木不在家或者敲错门或者忘了台词什么的而担心,现在要做的就是按响门铃,不管出来的是谁,即使谁也不出来,也要大喊:还钱!!
门开了,出来个老太太,慢条斯理,文质彬彬的。鳌翔的冲动和愤怒一下子止住了,想必她是铃木的夫人,便很有礼貌地说:"请问这里是铃木先生家吗?"
"是的,他不在家。请问你是......"
"我叫鳌翔,茶叶公司的。铃木先生欠我们公司一笔货款,我是来......" 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了,毕竟讨债是头一次。
老太太眼里的泪水像炸出来一样,顿时抽泣不止。然后捶胸顿足,干嚎又说不出话来,最后干脆蹲在了地上。
鳌翔被吓了一跳,接受尊老爱幼传统美德教育长大的他,面对一位老人因为自己的言语而嚎啕痛哭,讨债的心思立刻烟消云散,反而还觉得很内疚,很有罪恶感。
"您,先别哭了行吗?"鳌翔自己都快哭了。
老太太还是捶胸顿足,并且连连道歉。鳌翔见势,也不好再说什么,"既然铃木先生不在家,我下次再来找他吧。"
老太太边擦眼泪边鞠躬,进屋了。鳌翔坐在楼梯上,决定等铃木回来,自己也发誓要早上九点来晚上九点走的,无论如何也要和他本人说上话,做个了断。
铃木家里电视机的声音特别大,在楼道里都能听见。这么一来,屋里面人说话的声音就全被盖住了。鳌翔坐在楼梯上发呆,不过他已经很适应这种发呆的状态,这样会使时间变得飞快,不会让等待变得无聊。
混沌当中,鳌翔看见了自己小时候:第一批入队,戴着红领巾向老师敬礼;第一批入团,每天都把团徽擦得光亮;学习成绩优秀,所有的老师都喜欢他;在学校吹起长笛,所有的同学都羡慕他。
不费吹灰之力考上了重点大学,在周围的同学虚度光阴时,他被公司录取。他的世界是那么纯洁,没有羁绊,没有肮脏,一切好事似乎理所当然地降临在他头上。
唯一的不开心就来自妈妈的不认可和无休无止的奋斗目标,那种不能失败的危机感阴魂不散,以至于让他在获得一个成功之后看不清自己,一边发自内心地高兴,一边习惯性地机械地警示自己。
然而,一切强加的警示只能是虚伪,是躲避妈妈唠叨的假象,因为鳌翔从没有真正失败过,或者说从没有真正体会过触及心灵的失败,那么,他无论怎么警示自己,到头来也掩饰不了真正的自满和自傲。
现在,鳌翔终于懂了。人只能做到自己不去害别人,可不能要求别人不来害自己。害人之人固然可恨,可自己毕竟蒙受了损失。这损失可能是物品,可能是财产,可能是信誉,可能是前途,还有可能是生命。
法律、社会道德乃至上帝和佛祖,即使惩奸除恶,受害者蒙受的痛苦也无法归零。
于是他的妈妈告诉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受害,自己强大到坏人不敢害你,强大到坏人害不了你,这就需要有过人的本领,有如炬的眼光,有坚忍不拔的意志......
鳌翔的妈妈比任何人都害怕儿子受人欺负,她宁可自己当恶人,对儿子近似刻薄地要求,为的就是让他能够拥有自己保护自己的本领。
回忆受骗的全过程,哪怕到铃木的公司或者家里来看一眼,哪怕听周围人的劝告提出付订金的条件,有那么多的哪怕,只要稍加注意就不会弄得如此惨局。
说涉世太浅也好,太过善良也好,其实是贪婪与自大害了他。鳌翔第一次从心底看清了自己,那个其实手无寸铁、身披皇帝的新装,还在腥风血雨的社会里赤膊上阵的自己。和自称音乐家十几年后得知自己是音痴不一样,这次更加刻骨铭心,真正地唤起了他的一点觉醒。
日落西山,路灯也亮了。回家的人们经过楼梯,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鳌翔。第一天的蹲守没有成果。
...
第二天,第三天,连续一个星期也不见老铃木的踪影。他太太也不出门,真不知道这家子每天吃什么喝什么。
一个星期一的上午,鳌翔准时来到铃木家,坐在楼梯上继续蹲守。刚刚准备掏出饭团吃早饭,看见电梯里噼里啪啦出来好几个人。一个小老太太在前面带队,人群里还有警-察。
小老太太敲开铃木家的门,她的夫人出来,又蹲在地上哭。人们进去了,把铃木从里面搀出来。
"铃木先生,您已经拖欠了四年的房租,现在勒令你马上离开。"小老太太是这栋楼的房东。
"这里有法院签署的文件,你可以核实一下,然后马上收拾东西,限你今天黄昏之前搬走,否则我们就要强制执行了。"警-察很客气地用敬语宣布了以上内容。
鳌翔在一边看着,等警-察说完话,一把推开前边的人,一个箭步窜到铃木面前,大声地近似吼叫地说:"请把货款付清了再走。"
铃木本来很平静地听警-察宣读逐客令,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可被突然窜出来的鳌翔吓得一激灵。定了定神,用那被白内障几乎封死了的眼睛仔细凝视着鳌翔的脸。
一瞬间,老铃木恢复了平静,微笑着,那微笑和在帝国饭店和咖啡时的笑毫无差别。
"对不起啦。"铃木轻蔑地说完,转身回屋了。
"小伙子,你死了心吧,你被骗了。"房东把鳌翔拽到一边,"这个老家伙是个职业骗子,职业到身无分文就能在帝国饭店骗吃骗喝,有很多像你一样上当的人。那个老太太是他的情妇,以前有债主讨债,老太太就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替他还,可是他骗了那么多人,怎么还得完呢?"
"还不上怎么办?难道就任由他逍遥法外吗?"
"欠债是不能判刑的。傻孩子,你就认栽吧,他这辈子恐怕是还不上你的钱了。"房东叹口气,"即使打官司,就算你赢了,他也没钱给你。我也是跑了一年法院,今天才能把他轰走,我也没指望他能交出拖欠的房租。"
"让他变卖家产呐?"鳌翔觉得头很涨,快要炸了,他几乎能感觉到血液猛烈地冲击着眼球里的血管,乃至交织成条条血丝,而血丝越来越多,让他的眼睛看起来通红。
"你进屋看看就知道了。"房东拍拍鳌翔的肩膀,摇摇头,走了。
鳌翔破门而入,他呆住了。地上堆满了破报纸和方便面盒子,还有无数烟头。榻榻米上被烧黑了一大块,没有桌椅,没有一件家具。只有一台破电视机,声音开得巨大,屏幕晃来晃去的,里边人的脸色都发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