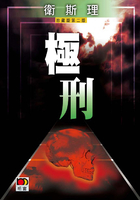但这一切只是顺带提一提而已。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还非常年轻。一次幸运的机会使它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各色人等都想要结识我。
我最初带着羞涩而热切的心情被介绍进入伦敦的文学界,现在回忆起来,都不无忧伤。我以前常去伦敦,现在已很久没去了,如果这座城市而今的奇特之处真像小说里描写的一样,那它现在也已经改变了很多。聚集点不一样了。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代替了汉普斯特德、诺丁山门,以及高街、肯辛顿。在过去,四十岁以下是个分界线,而现在,超过二十五岁就显得可笑了。我觉得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有点儿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而担心受到别人的嘲弄也使我们不至于过分狂妄自大。我不相信那时在上流社会放荡不羁的文人当中会强调节操的文化,但我不记得有似乎存在于今日的粗俗的滥交。我们并不认为用得体的沉默来掩盖自己异常的行为是虚伪的。我们说话并不总是直截了当。女性也还没有完全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住在维多利亚站附近,我还记得自己坐长途大巴去拜访那些热情好客的文人家庭。我因为羞怯而在街头徘徊很久,最终才鼓起勇气按响门铃;接着,我忐忑不安地被带进一间满屋子人挤得密不透风的房间。我被逐一介绍给那些名人认识,而他们对我的书所说的溢美之辞却使我感到无比不安。我感觉他们期待我说些有才气的话,但直到聚会结束我都没能想出点什么。我依次递上一杯杯茶和切得糟糕的黄油面包,从而设法掩盖我的窘迫。我希望没人注意我,这样我就能够自在地观察那些名人,听他们说一些有才气的事情。
我记得那些冷漠的大块头女人,长着大鼻子和贪婪的眼睛,仿佛身上穿着的不是衣服,而是盔甲;我也记得那些长得鼠眉鼠眼的小个子老姑娘,声音轻柔,而且目光机灵。她们坚持戴着手套吃黄油吐司,这一点一直深深吸引着我,还有,每当他们以为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就漫不经心地把手上的黄油抹在椅子上,我看到了总觉得无比钦佩。这一定对家具很不好,但我猜女主人在去她的朋友家里造访时,也会在对方的家具上进行报复。她们中有一些衣着时尚,她们说自己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你只不过因为写了一部小说就变得邋邋遢遢;如果你身材匀称,就应该尽量好好利用,在小小的脚上穿着漂亮的鞋子,永远不会阻止一位编辑录用你的“东西”。但也有人认为这样有些轻佻,他们穿着“人造织物”,戴着粗陋的珠宝饰物。男性很少有怪异的穿着。他们设法让自己尽可能看起来不像作家。他们希望被看成阅历丰富的人,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会被当成城市公司的管理人员。他们看起来总是有些疲倦。我以前从未了解过作家,我觉得他们十分奇怪,但我认为他们对我来说并不真实。
我记得当时我觉得他们的对话精彩极了,我也常常震惊于他们刻薄的幽默,有时候一位作家老兄刚刚转过身去,就立刻被批得体无完肤。艺术家相比于其他行业多了这个优势,他们除了朋友的外貌和性格之外,还同样可以讽刺他们的作品。他们精于此道,相比之下,我实在是自愧不如。那时,谈话技巧仍然被视为一门艺术来培养;一句干净利落的妙语比锅子底下荆棘烧得噼啪作响更被人看重;而那些格言警句,还不是愚笨的人用来假装聪慧的工具,它们给文雅的人的闲聊带来了乐趣。伤心的是,这些才华闪现的瞬间我已一点点也不记得了。但我认为,最愉悦的交谈发生在谈论交易细节的时候——这是我们所从事的艺术的另一面。每当讨论完了一本新书的优劣,我们很自然地就想知道它卖出了多少本、作者得到了多少预支稿费、他一共可能得到多少钱。然后我们会说说这个出版商,再谈谈那个,比较这一家出版商的慷慨和那一家的吝啬;我们会争论哪一个选择更好,是去一家提供丰厚稿酬的出版商,还是去另一家能够把书的价值“推到”最大化的出版商。有些出版商善于做广告,有些却做得很糟糕。有些出版商时尚,有些守旧。然后我们会谈论代理商,以及他们为我们弄到的报价;我们谈论编辑,谈他们欢迎的稿件类型,每千字多少稿费,是按时付清还是拖拖拉拉。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无比浪漫。这让我有一种亲密感,仿佛自己是某个神秘兄弟会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