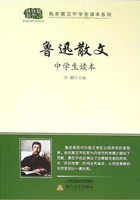杨禅师看了看慢慢浮上天空的弯月,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步法说是有六十四步,其实只有六十三步,最后一步只有一句口诀,并无招式。”
“什么口诀?”
“四个字,让——人——一——步。”杨禅师一字一顿,每说一个字,就递出一根手指。他极为少见的语风如刀,斩钉截铁。
“啥?让人一步?”智深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这算什么‘步’,不过看着杨禅师的表情,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智深慢慢思索着,杨禅师不说话,只看着他。
智深忽然想起年幼时曾学过的一套枪法,名叫仁者枪。这套枪法还和林冲的父亲林老教头传给智深。仁者枪有几个练法套路,前面的套路名字都是诸如“仁者爱人”、“杀身成仁”、“仁民爱物”、“以德行仁”、“仁言利博”之类的言语,唯独最后一个套路话风一变,变成了“假仁假义”。当时林老教头的大意是,上了战场,技击就是你死我活,‘假仁假义’就是提醒枪手不要想着套路,不要顾忌使用一些诸如洒沙子之类不太光彩的手段。
智深眼前一亮,说道:“这‘让人一步’难道是说,进招必须留有余地,以免出现意外,不及变招吗?是了,这五郎八卦棍极为刚烈,出手往往不留余地,多有玉石俱焚的招数。所以最后才有这句口诀,是时时提醒的意思。”
杨禅师听了放声大笑:“就是这个意思!想不到我临死前竟然有你这个传人,真是幸甚。”
智深大惊:“师兄何出此言?”
杨禅师坐在地下,语气很是轻松,轻松到了有些欢快的地步。他对智深说道:“我即将圆寂,你也坐,我有话与你讲。”
原来高僧临终前,皆有所感,能提前预知死期。杨禅师已知自己即将辞世,要交待后事。
智深坐下,垂泪道:“师兄前往极乐世界,换一个躯壳修行,本是好事,可洒家终究是不舍。
杨禅师道:“想必你已猜出来了,我与杨家将渊源不小。你可知我到底是何人?”
智深道:“不知,看师兄年纪,可是杨五郎延德公的孙辈?”
“不是,你且听我慢慢道来。昔日天波杨府杨老令公和佘太君除去七个儿子外,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叫杨延琪,一个叫杨延瑛,人称八姐九妹。她二人平时不离佘太君左右,是老太君的掌上明珠。”
“那时在位的真宗皇帝赵恒,是个好色之徒。他不顾江山安危,不管黎民疾苦,整天住在深宫,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有一年清明时节,真宗在奸臣刘文晋的陪同下,带了一簇人马出了皇城,专门物色美貌女子。路上遇到两个年青女子,骑着高头大马,一个穿红,一个穿绿,身态优美,面如海棠。”
“真宗回朝后,命刘文晋查访那两个女子的下落,结果查出是八姐九妹,便急命刘文晋去天波杨府去提亲。那刘贼没想到提亲未成,却让八姐九妹打了个痛快,滚了回来。真宗听了刘文晋的一派胡言,又见他被打成那个样子,勃然大怒,传旨命佘太君上殿。”
“佘太君来到金殿,道:“我杨家马上马下,南征北战,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愿效犬马之劳,没有做娘娘千岁的那个福份。’
“真宗听了大怒,拍案问道:‘难道为保大宋江山,你女儿就不出嫁了吗?’”
“这一问,使佘太君气上加气,说:“女大当嫁,这是正理。我杨家之女自然也要出嫁,只是现在还小。”
“真宗皇帝急问:‘那要等到多大?’”
“佘太君知道宋真宗昏庸无道,不愿意将女儿送入虎口,于是狠狠心、咬咬牙,说:“八十!”结果八姐九妹,守在母亲佘太君身旁,一直未嫁。
“佘老太君死后,杨家人除天波杨府主脉外,还有五台山杨五郎一人,辽国杨四郎一脉。八姐九妹向佛,便来到五台山颐养天年,蒙杨五郎传授五郎八卦棍。有一日,她们捡到两个被人遗弃的双胞胎婴儿,便一起抚养成人,又传授武艺。我是其中的哥哥,还有一个弟弟。”
鲁智深恍然大悟,道:“原来师父是杨家人收养。”
“正是。我弟弟自幼体弱,受九妹溺爱,从小就是唯我独尊的性子,后来慢慢走上邪路。八姐九妹便没传这五郎八卦棍与他,只传与了我,其余人却因资质所限,没能学成。前些日子,我自知大限将致,便传与了你,如今你便是五郎八卦棍的唯一传人。我这一生随性而为,并无遗憾,只有一愿,望你助我。”
“但请师兄吩咐。”智深道。
“这也是八姐九妹遗命,只是我未能完成:五郎八卦棍本是杨家武艺,杨家历经波折,已经失传,她二人希望能将这套武艺重传给杨家。我听人说天波杨府后辈有个叫杨志的,如今在种经略相公帐下听用,你可去将这套武艺传与他。辽国杨家一脉改姓为木,你若是寻访到他们,也可教导。”
“不管天涯海角,火海刀山,智深发誓一定让这套武艺重归杨家。”
“如此就好,这次我与你前程永别,正果将临也!我圆寂后,你把尸体火化,骨灰洒在菜地便是。这个草屋乃供奉八姐九妹的佛堂,你若是还在五台山上,时常烧香。”智深答应了。
见鲁智深还是垂泪,杨禅师叹一口气,对他说道:“痴汉!人生于世,如行冰雪之中。往来的人,或擦肩而过,或同行千里。然而雪落冰消之后,终无痕迹,亲爱仇怨皆为泡影。如今我无病无痛而去,你该为我高兴才是。”
鲁智深听得似懂非懂,忍住泪水。
杨禅师叠起两只脚,左脚搭在右脚,念道:“六根束缚多年,四大牵缠已久。堪嗟石火光中,翻了几个筋斗。咦!阎浮世界诸众生,泥沙堆里频哮吼。”便去了。
智深强忍悲痛,依着杨禅师遗言,把遗体火化,骨灰洒到四周,又去山上禀报首座与长老,搬来此处居住。
待过了头七,鲁智深辞别智真长老下山,往延安府来。
杨禅师许是临死之前糊涂,只说杨家后辈在种经略相公账下,却没有交待清楚。鲁智深心伤之余,也没顾得上问。当时种经略相公是叔侄两个,叔叔名叫种谔,在延安府做经略相公,人称老种;侄儿叫种师道,在渭州做经略相公,人称小种。这二人祖上乃宋初大儒种放,后来累世从军,镇守西北,前仆后继,可谓满门忠烈,人称种家将。
鲁智深虽不知道是哪个种经略,但想着两处都去,总有一处会有着落。因延安府离五台山近,加上前番曾听史进说王进也去了延安府,因此鲁智深便先奔延安府而来。
有人道,那杨家男丁不正是杨志么,鲁智深直接找他便是。这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时资讯不畅,虽然鲁智深认得林冲,林冲认得高世德,高世德认得杨志,但这四人,鲁智深却不认识杨志,加上鲁智深在五台山,林冲在沧州,高世德在汴京,杨志在苏州,四人各处天南海北,更是难上加难。
闲话不扯,且说鲁智深这一日行到了汾阳府平遥县外,只听到前路有金戈交鸣之声,间或有人惨叫,空中隐隐有血腥之气传来。
智深自言自语道:“应是有强人在劫掠路人,这么远还有血腥气,只怕已害了不少人命,洒家却得出手管一管。”
智深疾行前去,转过一个小树林,便见有一伙强人围了两个圈,一个人多的圈里是一个中年汉子,手里提着一根棒,身后护了一个约莫十来岁年幼女子,与强人厮打,眼见就要被打倒;另一个圈人虽然少,却围的极密,隐约听到有布帛撕裂声与强人淫笑声;地上横七竖八,摆了几十具尸体,有强人打扮,也有庄客打扮,但庄客打扮的远比强人打扮的多。
见有人来,一个独眼的强人迎上来道:“绵山好汉在此办事,不相干的和尚绕路!”
智深怒道:“阿弥陀佛你这鸟厮全家,真是凭白污了好汉这两个字。”说罢,他扔了包袱,横了禅杖便打。那些强人发一声,齐齐冲了过来,只剩下一个人光着屁股趴一女子身上行淫邪之事。
智深不看则已,看了勃然大怒,怒气直冲牛斗。他大喝一声,直如金刚降世,手下使出全力,有如虎入羊群一般。他挥舞着禅杖,往一个强人冲来。那强人被他气势吓住,急忙避让。但为时已晚,智深变换了禅杖的握点,一推一扭。只一下,那人便当场被禅杖的杖尖刺穿了喉咙。智深抽出禅杖,脏血如喷泉一般喷了出来。
智深一脚把那人踢开,接着压低身子,切开了另一人的大腿,然后舞着禅杖越过他,回首一击,将他后脑打的粉碎。那人痛苦哼了一声,转眼间双眼黯淡下来,重重摔倒。
见智深一个照面便杀了两人,那伙强人都胆战心惊。智深痛下重手,连毙了四五人。那伙强人眼见不敌,发一声喊,四散逃去。智深分身乏术,只得捡一个方向追了,又杀了几个强盗,直到都不见了,这才折返回来。
且说那中间汉子见强人散去,心下一缓,昏倒在地。智深回来时,他还未醒转。智深急忙上来看,发现他没受伤,只是累脱力了。
再看那个年幼女子,梳着靓丽的三丫髻,用一条垂着珍珠的红罗头须勒着,插着三只短钗,身穿穿着嫩黄短衣、白绫细腰襦裙。这身装扮甚是规整,只是眼下全都凌乱了,还沾着泥土。
智深掏出水囊,让年幼女子喂那汉子喝水。年幼女子见智深浑身是血,吓的发抖,战战兢兢接了。智深再去看被强人奸淫的那个女子,却是不活了,周围还有几个女子,都是丫环打扮,全是死去多时,皆衣衫凌乱,下身带血。
智深看了四周,再无活人,便回到汉子和年幼女子身边静坐,默诵佛号。缓了一会,那汉子醒来,坐在地上拱手道:“多谢大师出手相助,不敢请教大师法号。”
智深双手合什道:“洒家姓鲁,法号智深,现在五台山文殊院出家。方才那些贼子被我打死一些,剩下的都赶散了。你们是什么人?”
那汉子一五一十说了,他姓叶名清,在离此地七十余里的介休县一户叫仇申的人家做总管,会使枪棒。这年幼女子姓仇名琼英,是仇申的女儿。因仇申妻子宋氏父亲过世,他们一家人去平遥县奔丧,行经此地,突然冒出那伙强人。叶清拼死,只护得琼英周全。若不是遇见智深,二人也都要送命。
叶清起来,检视一遍,发现了仇申尸体,却不见宋氏,想是被强人掳走,只怕也不能活长久。
智深道:“那伙强人自称是山上强盗,附近可有什么土匪山寨?”
叶清摇头道:“这条路以往女主人回家省亲时走过几次,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土匪山寨。”
智深环视一圈,问叶清道:“事已至此,你有什么打算?”
“我先在此地埋葬家主尸首,然后去官府呈报官司,捕捉强人;我家主人只剩小主女琼英一人,我自当带回去养育;再周知仇氏亲族,议立本宗一人,承继主人家业,以免断了主人香火。一切事罢,再行报仇。”
智深见叶清计划的井井有条,不再多话,只长叹一声,抱拳告辞。
正要起行,仇琼英上前磕头道:“我愿随同大师一同上路,求大师教授武艺,以待日后为父母报仇。”
智深却是为难,他倒是颇为欣赏女子这番志气,但带着她上路,终究有所不便。
叶清劝道:“这位大师是出家人,如何能教导你。你若真有心学武,等回家后我四处延请名师教你便是。”
琼英只是拉住智深衣角不放,双目含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