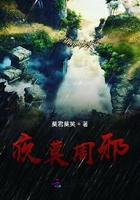门却自己开了。罗小鸽迷惑地站在门外,双手费力地抱着一厢可乐。三个人有几秒钟的冷场。
罗小鸽放下可乐问道:“怎么了,马袖你哥哥怎么了?”
说着她剧烈地咳嗽起来,一直咳弯了腰。
马袖帮她把可乐搬进来,说:
“小鸽姐你生病了吗?”
罗小鸽用手捂着胸口说:“有些感冒,还咳嗽。”
她瞪了马领一眼,马领明白她的意思。罗小鸽身体稍有微恙就会抱怨马领都是做爱太多了,都是做爱太多了。马领有气无力地坐回到沙发上,看她们收拾地上的碎片,他把脚不时举一下,让开罗小鸽手中的扫帚,问她,晚饭怎么吃?
3. 拿掉
三个人坐在街角的餐厅里吃饭。夏天坐在有空调的房子里看外面,就是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好像可以对世界冷眼旁观了。落地玻璃窗外,一个性别不明的要饭小孩龇牙咧嘴地一直冲着马领做鬼脸。起初马领没去理会,可这个小流氓越来越变本加厉,吐舌头,皱眉头,突然用力把一口痰吐在了玻璃上。
“滚!”
马领神经质地叫起来。他把手中的啤酒朝外面泼过去,全部又被玻璃挡了回来,弄得满桌狼藉。小孩下意识地躲了一下,又马上贴回到玻璃上,气焰嚣张地继续挑逗马领。罗小鸽皱着眉头瞪马领,起身去向服务员反映情况。服务员从后面喊出两个膀大腰圆厨师模样的男人。众人浩浩荡荡开出门外,小流氓早狂奔而去了。
趁罗小鸽去处理问题的功夫,马领问马袖:
“你打算怎么办?”
马袖边吃边说:“拿掉啦。”
她说得是那么的果断和简洁,仿佛一切的艰难困苦,只消一扬手便会——拿掉。
马领拳头砸在桌上,一碟金针菇跳起来,翻过去。
罗小鸽面带愠色地回来。
马袖说:“小鸽姐你别理他,他就这样,从小就是。”
罗小鸽的表情复杂,她克制着自己,同时又要把她的克制表示给马领。马领感到乏味,居然希望那个小混蛋再次出现在外面,用他邪恶的表情来刺激自己。
清蒸鱼上来时,罗小鸽反复查看完鱼头,最后断定这不是她挑的那条,那条她专门做了记号,在鱼鳃上插了支牙签的。服务员也帮着她找,把一条鱼反过来掉过去地查看,还是没有找到那个记号。
罗小鸽说:“不要了,不要了,你们换了条鱼。”
服务员说:“绝对没有。”
罗小鸽说:“那么牙签何在?”
服务员说可能落在烹调过程中的某个环节了。
罗小鸽可能正陷入在某种别捏的情绪里,需要借题发挥,她傲慢地说:
“那我不管,牙签在,鱼留,牙签不在,鱼去。”
马领勃然大怒:
“罗小鸽你傻啊?在这里给人讲文言文!”
罗小鸽怔在那里,随即手捂着胸口熟练地咳起来。
“请问这条鱼是去是留?”
服务员不怀好意地问。她是个乡下姑娘,此刻她努力用糟糕的普通话来发问,就是显得不怀好意。
马领看她半天,挥手让她赶快走开。
马袖边替罗小鸽捶背边说:“小鸽姐你要好好休息,我走的时候再来看你,你不要理这个疯子。”
罗小鸽马上停住咳嗽,纳闷地问她:
“你不住你哥哥那儿?”
马袖说:“不了,我有地方去。”
马领黑着脸盯住马袖,马袖不看他,说道:
“我吃好了,先走了。”
她和罗小鸽亲昵地拉拉手,然后就这么走了。
罗小鸽严肃地看着马领。马领和她对视着,越来越沮丧。突然他起来向外跑去。冲进夏天的烈日中,他向街两边张望,已经没了马袖的影子。
回去的路上罗小鸽指出:
“我发现你对你妹妹太紧张了。”
马领说:“我不否认,她是我妹妹,我们一奶同胞,血浓于水。”
罗小鸽说:“可好像不太正常,过分了点儿。”
“过分吗?就算是吧。我活着没什么动力,就是为了这么几个亲人,父亲,母亲,妹妹,”他停顿一下,看看罗小鸽说,“当然,还有你。”
罗小鸽扬扬眉毛,终于憋不住笑起来。
两人手刚拉在一起,马领就觉得脑袋后面被什么东西“叭”地一下砸中。用手一摸,放到眼前,定睛端详,是一些颜色好看的糊状物。回头看,脚下有只吃剩下的冰淇淋盒。一个衣衫褴褛的小混蛋飞快地向远处奔逃。
“冰淇淋,是冰淇淋!”
罗小鸽用一种颠扑不破的聪明口吻指出,她很兴奋,仿佛只要不是狗屎,就是一件值得快慰的事。
马领受到启迪一般,着迷地凝视着自己花花绿绿的手指。
罗小鸽紧张地看他:
“别生气,千万别生气,你冷静一些,我求你,别再发作啦。”
马领本来已经升起的怒意被她的请求阻挡住,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于是他只能迟疑地将手指伸进嘴里,专注地舔食起来。
罗小鸽绝望地大声尖叫,掉头就跑。
4. 抒情
回到家,罗小鸽已经先到了。她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躺在凉席上,脑门上搭着块湿毛巾用来降温。在头顶转动的吊扇和脑门温度的共同作用下,毛巾一会儿就干了。身边有只水盆,盆里浸着三四条毛巾。她又起来换一条湿的,然后重新躺下,好像真的很舒服的样子。马领在一旁静静地看她,心里柔软下来。并不是这个场面——吊扇、女人和湿毛巾——本身引人动情,是这三样东西奇妙组合在一起时的那种画面感,以及隐喻着的那种爱情的本质性价值,让人不禁柔软。习惯了,他想,真是,这个女教师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谋求一些微不足道的安慰,并且,在微不足道的安慰中自得其乐。
罗小鸽哼哼唧唧地说:“放假了你陪我去大连玩。”
马领说:“你们有假期,我没有,我还得工作。”
罗小鸽啊了一声:
“你原来也有工作的啊,你那也叫工作吗?”
马领说:“当然叫‘工作’,不叫‘工作’叫什么,你说说看?”
“要我说吗,”罗小鸽眨着眼睛看天花板,“你那叫玩笑。”
从她哈着热气的嘴里发出来的“玩笑”这个词,有一种性质相反的细小的忧郁。
马领说:“玩笑就玩笑吧,反正比跟一只抽屉经年累月地搏斗强。”
罗小鸽笑起来,说:
“你真是对那只抽屉念念不忘啊。抽屉那么令你厌恶吗?抽屉是什么?抽屉就是规律与秩序,能够让一切井然有序,而你,缺乏的就是对于规律与秩序的服从。”
然后她认真地看着马领说:“我看你还是找份正经工作吧。”
马领不想让刚刚好起来的情绪被破坏掉,在她身边躺下,也用一块湿毛巾冰在头上。这一冰的确让他平缓了许多。
他说:“我看我还是继续玩笑的好。”
罗小鸽把手伸过来,拉住他的手说:
“这样下去不行,你们这种玩笑开得不合时宜,你出去看看,现在的人谁还敢这么混日子,你们要搞事业,就该有副搞事业的样子,不能弄得像儿戏。”
马领把五根手指分开,和她的交错在一起,抓住,松开。
“儿戏?”他说,“这个定义不错,这可能就是我选择的方式,没什么可抱怨。”
“为什么?”罗小鸽说:“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呢?”
是啊,为什么呢?对此,他只有振奋起精神,用一种诗歌般的格律来回答,因为不如此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没办法——
如果我不能做我喜欢做的事,
那么我所能做的
就只有不去做我不喜欢的事,
这不是同一回事,
但是
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最好的事。”
罗小鸽支起胳膊,趴在他眼前看了半天:
“那么,什么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问题,马领当即被问住了。是啊,该如何说明呢,什么才是他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他说他所喜欢的事情无外乎是站在麦田里守望岁月,罗小鸽这个女教师一定会立刻鄙夷地指出,这不过是塞林格之流的爱好,言外之意甚至是说他根本不配这样的喜好,那么他只有敷衍了,尽管也不无真诚。
“这还用问吗?”他说,“我喜欢做的事情不就是和你在一起吗?”
“可是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你已经做到了。”
罗小鸽的思维依然清晰,并没有丧失必要的逻辑性。
“可是还不够!还不够!好的爱情之路必然是遥迢万里,我现在依然没有能力做到最好。”
他只有这样虚张声势地诡辩下去。
罗小鸽陷入了沉思,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她起来重新换上条毛巾,也替他换了一条,随即换了一个话题:
“你妹妹还和那个男人在一起吗?”
马领把两人交错在一起的手指使劲握住,连他都觉得痛入骨髓了。
罗小鸽叫起来:“痛死人啦!”
这一痛,就有效地终止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话题。
罗小鸽把腿压在他身上,带着疼痛的余悸说:
“礼拜六我要和几个姐姐去吃饭,不来你这里了。”
“知道了。”
马领伸手顺着她的腿抚摸。
她说:“你不许生气啊。”
他说:“怎么会,我早习惯了。”
她握紧他的手,不让他向上延伸:
“你不许不高兴,我们也是血浓于水,一奶同胞。”
他说:“是啊,是啊,就是认识到了你也是别人的妹妹,我才这么爱你,不愿意伤害你。”
她攥紧手问:“真的?”
马领抬起身子认真地看着她:
“真的。”
天,生活里就是这么一点仅有的柔情了,其余的就全是海水般咸涩的泡沫了。马领坠入柔情之中,同时有一点点抒情的凄凉。
“我病啦,”看着他没有反应,罗小鸽又说,“我病啦。”
马领说:“我知道,我知道,做爱太多了嘛。”
罗小鸽紧抓住他的手有所松动,任由他向上移动。他们开始接吻,逐渐专注。她从凉席下摸索出只避孕套给他。
他仍开说:“今天不用这玩意儿。”
“为什么?”罗小鸽勾住他脖子问,“为什么啊?”
他说:“不想用,如果你总是这么麻烦,我倒不如去自娱自乐。”
罗小鸽问:“怀孕了怎么办,啊?”
他焦躁起来:
“怎么办?什么怎么办?拿掉!”
罗小鸽在他近乎粗鲁的动作下很快兴奋起来,突然用手抵住他:
“叫我,你叫我。”
马领问:“叫什么?”
罗小鸽深吸口气,脸色泛起红晕,她说:
“你叫我‘妹妹’。”
马领觉得脑子里蒸腾出一股瘴气。
“妹妹。妹妹。”
罗小鸽呼吸急促,答应着,又要求道:
“你叫我,叫我,叫我——马——袖。”
马领停住,双手撑着身子瞪着她:
“妈的,你才是个真正的疯子!”
罗小鸽笑得天花乱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