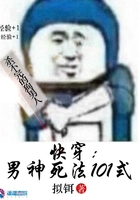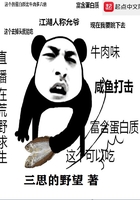小说的解读,可着眼于要素。除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外,尚有主题、情感、结构、细节及场景等。再就是着眼于体式,有小小说或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体式不同,特点就有所不同。还可从类别入手。所谓类别,就是内容及表达上的特色。诸如情节小说、性格小说、心理小说、问题小说、诗意小说、散文化小说等,往往各有侧重。先说情节小说,这是较为传统的。就情节本身来说,有开端、发展、高潮及结局之分,有的还有序幕与尾声。古典小说大都以情节取胜。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就选文来看,可分为几个段落:开端是沧州遇旧;发展是听说仇敌到来即买刀寻敌,而三五日未见消耗便自心下慢;高潮是去看守大军草料场而亲闻陆谦阴谋,于是奋起反抗杀死仇敌;结局自然是逼上梁山。整个情节,波澜起伏。就在这样一个故事情节的进程中,既写了林冲的善良安分、忍辱负重,又表现出正直侠义、疾恶如仇。由于情节是人物成长的过程,因而情节与人物分析还可结合起来。
性格小说,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主。情节及环境等,都要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因而人物形象的分析,常常成为解读的重点。比如鲁迅的《孔乙己》,就是先突出人物的形象:“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然后围绕着这个人物,讲一些相关的琐事。比如偷书,偏说窃书不算偷,强为辩解。又如喝酒从不拖欠,显得品行比别的酒客好。再如分茴香豆给小孩吃,却说什么“多乎哉不多也”。这些琐事都很有表现作用,显出孔乙己不失质朴,却又不能安于小事过活。至于人物的最后出场,则是坐在一个蒲包上,极为落寞,从而活画出一个深受科举毒害的读书人形象。小说的人物形象有扁形与圆形之分,扁形人物多突出一些性格侧面,圆形人物则较为复杂。大体上说,像孔乙己这样的形象还是趋于扁形的。但如《阿Q正传》中的阿Q则就是圆形人物,其性格被归纳为精神胜利法,包含着许多在对立中互相转化的性格要素,如自高自大与自轻自贱、渴望革命而不理解革命等。
心理描写本是塑造人物性格的一种方法。比如《林黛玉进贾府》,本是通过林黛玉的眼睛来介绍贾府的。由于外祖母家非同一般,再加上初来乍到,“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言行如此矜持,但内心的想法则不然,因而文中多有心理描写,从而表现出人物的真实来。比如与贾宝玉的相见,“黛玉亦常听得母亲说过,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衔玉而诞,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外祖母又极溺爱,无人敢管。今见王夫人如此说,便知说的是这表兄了”。“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这都是由间接了解而来的想法,及至见了面。“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眼熟到如此,不仅打破了先前的成见,还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从而表明心灵的相通。当然,即便心里感觉如此,却不会在言行上表露出来,仍是矜持使然。小说中若加重心理描写的比例,就成了心理小说。比如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墙上的斑点》,就是写面对墙上的一个斑点,展开许多联想。自由联想及内心独白,都是意识流小说中常用的。而意识流小说,大都是侧重于心理的小说。
哲理小说,着眼于表达作者对世事人生的看法,多有哲理寓于其中。比如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父亲一直在河上漂流,就是不肯上岸。父亲在找什么呢,也许就是标题所说的河的第三条岸,但现实中是并不存在的,只能是一种超越世俗的人生追求,或者说某种理想。至于父亲与现实的联系,那就是需要“我”去给他送食物。“父亲,孤独地在河上漂流的父亲需要我。我知道他需要我,尽管他从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因这件事责怪父亲。”长年累月,“我”的头发也渐渐地白了,仍等待着,终于父亲听见了“我”的呼喊声:“他听见了,站了起来,挥动船桨向我划过来。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我突然浑身战栗起来。因为他举起手臂向我挥舞,这么多年来这是第一次。我不能……我害怕极了,发疯似的逃掉了。因为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有机会接近了,仍是无法沟通或交流,表明各自的孤独更是永久的。
再说一说散文化小说。散文化小说是淡化情节的,虽有故事,但大都提供一个框架。以故事为框架,可包容较多的细节或场景。以鲁迅的《社戏》为例,作者先讲都市戏园里人声嘈杂,让人不耐烦,来反衬出乡间空阔地带演出的社戏另有意味,尤其是连带着儿时的记忆。于是作者便写小时候看社戏的事,颇有铺垫。一群小伙伴想去赵庄看戏,先是没有船,有了船又没大人来划,然后是小伙伴自己撑了去。作者便以不无抒情的笔调描绘了月下的景致:“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对小孩来说,这既是看戏,也是贪玩。于是回来的时候,便又去拔罗汉豆来煮。而第二天六一公公送来大碗的豆,却没有昨夜的好吃,自然此后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小说中所写的对社戏的回味,饱含着对童趣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