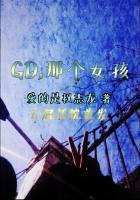即使此刻,我坐在阁楼的旧藤椅上,依然是冰冷的。这里没有空调,只有一个破旧的电扇,上面积满了灰尘,我没打开。我怕声音扰乱了自己,会感觉不到你。
我还是先套回那件宽大的睡袍吧。我不想让自己裸着身体去展开那一桩桩不堪回首的记忆。那里面夹杂着的不光彩和不体面,也许会让阿哥你忍不住闭上眼睛,皱一下眉的。
让我先来告诉你吧,在这七年的城市生活中,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女子。我已记不清具体日期了。我只记得这个城市的天气有些凉了,我已添了衣服。
那个夜晚,我和平常一样端着酒水推开一个包房的门。我记得那个门牌号是512。
一个女子裸着上身,五六个醉酒的男人,粗鲁地狂笑着,目光个个淫猥。其中有一个站起身,上前捏了捏那个女子的乳房。嘴里吐出一口烟雾,眼里盛满轻薄之意,说"这么小,也出来卖!"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般阵势。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一个男人立即冲着我喊叫,怪怨我酒水送得不及时。
我涨红着脸,极力掩饰内心的惊慌,将酒水送至茶几上。
茶几是玻璃做的,上面溅满了水,很滑。手一抖,一瓶红酒摔跌在地上,酒瓶破了个洞,像一个伤口,往外汩汩地冒着殷红的血。
所有的目光全集中在我身上。那些目光都是一样地幸灾乐祸,一样地隔山观火,有一种终于可以找点事出来做做的快乐和轻松。
我不知如何是好地站着,只觉得脸在烧,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那个女子打破了这个局面。她一边穿回衣服,一边开口说话,神情中没有丝毫的慌乱和尴尬,就像是看一场毫不生动的电影片断。
她说,"我已让你们看了,该给我钱了吧?"
有一个男人说,"你太不性感,否则就带你出去,给你双倍的钱。"
那女子也不生气,向他们摊开一只手心。意思是:她只要索取她该得的那一份。
男人给了她两百块钱,然后掉头转向我。一对眼睛在我身体上下求索,似乎想要找到什么答案似地。
他问我,"愿不愿意跟我出去?只要你跟我出去,我不会亏待你!"
我不知道他叫我跟他出去干什么?我已被吓坏了。
我看见正欲离去的那个女子,慢慢回过身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像电影慢镜头一样刻在我心里。她很深地看我一眼,然后慢慢走回来,像下了一个决心那样,把两百块钱放在茶几上,轻描淡写地说,"她不是这儿的'歌女',酒钱我替她赔给你们。"
她就是虹霞。我要跟你好好说说她。
这七年来,是她帮助我一起找你。然而,又是她,让我们咫尺天涯,永远擦身而过。
那夜,是她替我解了围,把我从刀尖上救下来。她用她裸身赚来的两百块钱买去了我的心。
想来也奇怪,那一瞬间,我感觉她与我离得很近。那种近,有着温暖真实的质感,互相可以交付内心。
就这样,她闯入了我的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每当我回忆起和虹霞的初次见面,义无反顾地把所有的情感都向一个陌生人倾泻的时候,我便会想起我父亲。父亲曾对我说过,不要太相信陌生人,就算对身边最亲的人,也不能太相信。
现在回忆起来,父亲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一脸肃穆。肃穆中带着难言的伤痛和悲愤。
父亲为什么会伤痛?他悲愤什么?那时我太小,来不及将一切都弄明白,父亲就撒手走了。
但我在一路行走的过程中,并没有记住父亲的话,或者没有时间去想起。我把父亲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在"万乐迪"歌厅门口,我曾看见一个背影很像父亲的男人,头发有些乱,衣服一样旧灰。我很想他能够转过身来。就像多年前,父亲站在屋檐下,听到我的脚步声,便会转过身来,朝我露出笑容。那一次,我好像记起过父亲的话,但依然没有放到心里去。
那么多年,我总在想父亲。我知道父亲爱我。我爱的,他也爱。父亲也爱你。他喜欢我跟你在一起。但是父亲的眼光还不够远,他没有看见我们会这样无缘无故地分开,错过一生。如果父亲能预知,他一定不会让我把爱放给你。
如果父亲能够预知,那么,他也一定不会把爱放给母亲。但父亲已经无法回头。母亲是他生命中唯一爱过的女人。但却背叛他一生。
父亲的死,一定和母亲有关。长大后我一直这么认为。虽然我毫无头绪,也找不出证据。但我相信直觉。我相信直觉有时候比任何证据更准确。
我越来越怕那份直觉。有时候心底里的直觉,就是一种预感。我总是能预感到噩运,而不是好运。
是不是噩运特别让人揪心,才会产生出一种更为强烈的感觉?
小时候,我最怕失去父亲。夜里做梦,总是梦见父亲走了,走到我再也寻不着的地方。每次哭醒过来,仍心有余悸。
父亲说,那是因为我太怕失去他,才会做这样的梦。
父亲真的走了。走到我再也寻不着的地方。我觉得我的梦境和预感,是对父亲的诅咒。是我的诅咒让父亲离开了这个人世。
还记得父亲走的那天流鼻血,黑红黑红的,像一抹魂魄,挣扎着从父亲鼻孔里爬出来,告诉我他不放心我。他对不起我。他把我一个人扔在人间。让我从此成为孤儿。
那天父亲的魂已离了身,他一定已看到我身后的局:我命中的男人,注定要一个个地离开我!
如果父亲生前就能预知,我注定在失去他之后,还会失去你。父亲他会不会不死?会不会因为舍不得我,而为我活下来?
渔船未靠近码头,便遭台风袭击。船撞在礁石上,裂了身。跟父亲同船的几个人,都说父亲和他们一样紧抓着缆绳和船板。其实台风并不凶猛,不一会便平息了。人人都抓着船板,慢慢游回了岸。但父亲却没有上岸。有人看见他放了手。父亲让自己在海浪里浮沉。
就算没有缆绳,没有船板,父亲的水性很好,身体结实得像牛,渔船出事的地方离岸不远,父亲怎么也能游回来。但父亲放了手,他没有游回来。
那天把父亲打捞上来的人,对父亲的死议论纷纷。他们都知道父亲是个水性极好的人,他们不停地摇着头,叹着气,表示他们的惋惜和难以理解。
--我恨父亲!
我知道父亲一定是自己选择了放手。一定是落水的那一瞬间,突然激起了他积郁多年的伤。他知道他的伤口已永远不能愈合。父亲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让伤口永远消失。
那天你抱住我。你说不能这样怀疑父亲。一个人不会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但我感觉到你的身体也在剧烈地抖。
就像此刻,想起父亲不明不白的死,我仍然会止不住地颤抖。
3.
虹霞却不信命,她总说命是可以改变的,是捏在手心里的东西。她相信所有的付出总有回报。虽然,她的付出并不一定有预想的回报。但她始终坚信:不是不报,只是时机未到。
所以,她总是让自己一边放弃,一边前进。而我却总是在回头望。像有一只魂,在我身后跟着我。
那个深秋的夜里,虹霞带着我穿过马路,穿过重重霓虹,去到她的出租房。
那是一个小套房,在老而旧的高层建筑里,像浮在城市深处的岛,充满尘世沧桑。我租住的阁楼却在城市边缘,没有那么多似鬼火一样闪烁的霓虹。一到夜晚,便会被黑夜完全吞没。
她说,"你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吧,反正在这个城市里我也没有亲人。"一句话,惹得我心里一酸,有一种惺惺相怜的感觉。
房间里有两双拖鞋,一双女式的,一双男式的。她把女式的那双递给我,自己趿上那双男式的。
她说,"已好久没有男人来了,你放心,以后也不会有了。"
她朝我眨了眨眼晴,晦涩自嘲地笑一下。
我叫她"阿姐"。
她笑得泪直流:"城里人不会这样叫,乡下人才这么称呼。"她让我把"阿"字去掉,直接叫"姐--"。长长地拖出一个音来,听上去娇媚动人。
她顺手点燃一根烟。她抽烟的姿势大方而落寞,轻轻吐出烟圈,吸入鼻腔,再吞入喉咙,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那样娴熟老练。
她说,"一个女人在江湖上混,就得学会抽烟。"
她将她混迹的地盘,称之为"江湖"。
她教我抽烟。她说了很多关于烟的好处。烟能让人定神、静心、从容,烟能让女人变得优雅,多出几分姿色。一句话,一个女人学会抽烟,是走进"江湖"的关键。
我模仿着她的样子,吸进一口,再吸进一口,呛得大声咳嗽。呛出一脸泪水,咸咸的。
虹霞说,她第一次抽烟也是这样的,呛得满脸都是泪,多抽几根便习惯了。
她又教我喝酒。红酒。她说女人在饭桌上,最好不要点白酒或啤酒。最好喝红酒。红酒美容,关键是看上去性感。
举着红酒杯的女人,会让人觉得很性感。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在我面前说"性感"两个字。只觉得脸在微微地烧。
红霞在说着她的"江湖",说她在江湖中的见闻。而我一次次说起和你在海里的那一幕。那一幕被我夸大了,最后成了虚幻的景。
我羞涩地说出"一条鱼"。我是你的一条鱼。你是我的渔人。但你把我放回了海里,从此天各一方。
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发现自己被颤动的气流包围着,那种颤动是奇异的。
那夜,我彻底忘了父亲的话。父亲让我不要相信任何人,也不要喝醉酒。女人喝醉了酒,不仅伤身,还会容易吃亏。
父亲不会知道,在这七年里,我再也没有离开过烟和酒。
我一杯杯地往胃里灌酒。风从窗外吹进来,有点微微的凉。那夜的月亮,是个不发光的影子,窗外的夜是汪洋大海。我已变成一条鱼,潜入海里。我在水中细细捕捉你的喘息,轻声呼唤着你的名字。
那一夜,我醉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我翻了一个身,踢去被子,却踢到一个女人的身体。才想起自己喝醉了,和一个叫虹霞的女子睡一起。我扶着头,浑身难受,不知哪儿在痛着。
发觉天已大亮。我急急忙忙穿衣下床,想着还要去饭店打一份工,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八点。
虹霞拉住我,不让我走。说今后不要再去干这种老老实实赚几个小钱的勾当,那样永远发不了财,也翻不了身。她让我跟着她混,总有一天会混出头的。
我不知道怎样算混?哪天才能够混出头?虹霞在这个城市里混了好多年,为什么一直没有出头?
虹霞望着我,笑里藏着诡异和无奈。她说,"如果我有你一半的资本,我早混出头了!"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资本?那天我没有离开虹霞的出租房。我听了虹霞的话,留了下来。
我留下来,并不是我已定下心来要跟着她混了。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一下床,全身虚脱,软绵绵的,双脚像无处着落。我担心这样出门会出事。
就这样,我又让自己回到她那张床上去。醒来时,时间指向下午四点。阳光已换了方向。
虹霞坐在床边等我。她的手里夹着一根烟,玩弄着,没有点燃。她说我在梦里落泪了,但不敢叫醒我。
我沉默着,有些害羞。我记得很清楚,我脑子里全是水,你带着我在海里游。你变成了一条鱼,随着海浪越游越远,我奋力追,追得没有了力气,终于还是追不上你。于是,我落泪,哭出了声。
在一个女人的床上,我梦见了你,我又失去了你。有一种心被迷失的空荡感觉。
那天下午,我很奇怪我竟然把一切都告诉了虹霞,就凭她两百块钱把我救下来,再捡我回家。也有可能她的某根神经对上了我的某根神经。在这之前,我从未将我内心里的事说给谁听过。
我不时地做着深呼吸,第一次一吐为快。等我将心里的话全部倒空之后,如同快窒息的人突然得到了氧气。
我舒了一口气。她抱住我,拍拍我的背,让我从此与她姐妹相称。从今以后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她再次要求我把我租住的阁楼退了,搬过去跟她一起住。
我搬了过去。
但我没有退掉阁楼。
我需要一个为你等待的地方。我怕哪天你找来,阁楼已换了主人。
当我租下这个阁楼的时候,我将地址写在纸上,用油纸布包了,埋在桂花树下。我在桂花树下做了个记号。将树枝插在泥土上,并在地上写下"等你来找我"这几个字。我以为哪天你会回家,一定会去看看那棵桂花树。
回去那天,我经过你的家。你的母亲坐在一把摇晃的竹椅子上,拐杖握在手里比人高出一半。
我的脚步声很轻,但她好像已感觉到是我。她转过身去,不愿理我。她一定听说了,我也去了城里,她怕我来城里找你,缠上你,给你带来不幸。
那一刻,我有个奇怪的念头,我觉得你并不在杭州这座城里。也许你的叔叔又搬家了,连同你一起搬去了另一个城市。否则,我为什么总是遇不上你?
但是,我后来问了好几个村里的人,都说你叔叔一家在杭州。但也不能完全确定没有搬走。
第二次回去,二零零四年的秋天。你的母亲已在两年前离世。村里人说,你跟你叔叔一家都回到家奔丧。丧事办得很大。全村的人几乎都请到了。都说你跟着你叔叔有出息了。你开着轿车回家,从此改头换面。
而我,竟然不知道你回去过,也不知道你母亲离世的消息。我已多年没回家。对于那个家,我已心灰意冷。那里已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人。
但那时,我知道你还活着,活得很好。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你有没有找过我?
你有想过我吗?
我的地址就埋在桂花树下,你居然动都没去动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