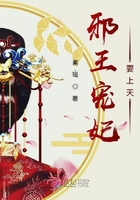我的公司在曼哈顿一栋气派的摩天大楼里。那天,我正在整理文件,准备稍后下班时,电话响了。是秘书璐熙打来的,她半个小时前提早下班了。璐熙的声音里有种莫名其妙的惊慌:“我不小心把一个包裹遗忘在我办公桌上。它很重要,必须立即送到盲人协会去。盲人协会离办公楼不远,穿过几个街区就到了。您能帮我送去吗?”
我答应了璐熙的请求。我刚走进盲人协会,还没来得及开口,就有人径直向我走来:“欢迎您光临!我们马上就开始。请坐。”然后指了指他旁边的空位。
一帮人坐在那里,我被安顿在视力正常的那排人里,对面则是一排失去视力的盲人。
一位大约25岁的年轻人,站到了房间前面,开始解说:
“我是今天的辅导员。待会儿,请失去视力的朋友,先了解坐在对面的朋友。你们必须认真地感知对方的脸部特征、头发状况、骨骼类型以及呼吸频率等细节。我说‘开始’,你们就行动。先摸头发,注意体会卷曲和顺直、粗糙和细腻等区别。并且,猜猜它是什么颜色。然后是额头,感觉它的硬度、尺寸和皮肤的肌理。接着研究眉毛、眼睛、鼻子、颊骨、嘴唇和下巴,最后是脖子。辨别对方的呼吸,平静还是急促?聆听对方的心跳,快速还是缓慢?好,开始!”
我觉得毛骨悚然,恨不能插翅逃离这个恐怖地带。这以前,如果不经我同意,我决不允许谁触碰我的身体。可对面的年轻人已经伸出手,接触到我的头发。天哪,实在太别扭啦!慢慢地,他的手移到我的面颊。我难受得浑身冒汗。他快听到我心脏的节奏了,马上就知道我惊慌失措。不能让他摸清我的心态。深呼吸,镇静。不要示弱,不要失态。当这宛如炼狱般的过程结束时,我不禁长长地舒了口气。
年轻辅导员的声音再次响起:“接下来,轮到视力正常的人去感知各自对面的搭档。请你们闭上眼睛,把他们当做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默想您打算了解些什么。比如,他们是谁、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梦想是什么等等。请先从头部开始,感觉他们的发质,猜测一下会是哪种颜色。”
我摸了摸“搭档”的头发,有些干燥,还有些髦曲。可是,我想不起他的头发是哪种颜色。我从不留心任何人的头发,自然谈不上记忆了!事实上,我没有正眼瞧过谁,只是不停吩咐别人,任何人对我而言,都像可有可无——我从来没有真正注意和关心身边的人!我认为:我的生意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接触、什么感觉、什么了解他人,完全和我拉不上关系。
手滑过年轻人的眉毛、鼻子、面颊和下巴,我的心底渐渐有一股热流涌动,灵魂里最敏感、最柔软、最脆弱的某个部分,不知不觉间被触及。那个部分,我不敢示人,更不敢自己面对,一直被我小心地隐藏。我突然感到寒意森森,期盼尽快远离这栋大楼,而且,永远不要再来。
“梦想”这个词忽然窜进了我的思绪。那个年轻人有什么梦想吗?我觉得自己有些奇怪:他和我非亲非故,无牵无挂。我为什么会关心?我有两个十来岁的孩子,但我对他们的梦想一无所知。我猜他们关心的不仅是汽车、运动,还有女孩吧。我们很少深谈,彼此几乎可以称作“陌生”。我也不祈求他们会喜欢我。至于妻子,我们各自为营,也无所谓交流。想到这些,我的汗越来越多,呼吸更加急促。当年轻的辅导员说停止时,我立刻缩回手,有种解脱的释然。
“下面是这次活动的最后环节。每个人有3分钟,和你们的搭档交换彼此的体会。失去视力的朋友先来。”
我的搭档说:“我叫亨利。在您没有赶来之前,我以为自己又被遗弃了。我很感谢您能够及时赶到。感谢您有勇气接受陌生人的‘亲密接触’。因为,尽管您遵从了辅导员的安排,内心却非常抵触。我还发现,您的心非常‘大’,但它十分孤独。您希望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爱,却不知道如何寻找到它。其实,我很钦佩您敢于直面自己心灵的胆量。您想逃离这栋大楼,但最终坐了下来。我第一次来这里时,也有同样的念头。不过现在,我很坦然,不再惴惴不安地思考我是谁,也不忌讳在他人面前哭泣、惊慌,甚至恐惧。我不再把自己藏在工作里,率性地想笑就笑,要跑就跑,即使在人前跌倒也不介意。这些朴素简单的情感,都是我在盲人协会学到的。我从心底接受而且欣赏它们。您应该多花一点儿时间在这里,认识真正的自己。”
我望着双目失明的亨利,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擦干眼泪,无语凝噎。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地方,可以让我得到这么多无条件的爱、尊重和智慧。
我记得只对亨利说了一句话:“您的头发是棕色的,您的眼睛很亮。”亨利,大概是第一个让我记住别人眼睛的人。我其实是个盲人,亨利不是,他能穿过黑暗看清他自己。
活动结束时,我才想到璐熙的包裹。我把它送给辅导员:“我的秘书让我转交的。很抱歉,来晚了。”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始作俑者,我的秘书璐熙。这段经历以及以后每周去两次盲人协会的事,成为了我心灵的秘密。
我无须向别人解释,但开始去领悟人们之间的爱。我不会向我华尔街的“朋友”透露半点儿风声。我知道,在残酷的现实里,我必须保持高高在上的状态,否则——任何一个破绽都可能授人以柄,让我遭到迎头痛击。
但从那天起,我开始学着尊重自己、爱自己,也学会尊重和了解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