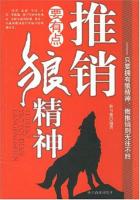“眼睛看到的,和实际经历的,总是有着巨大的差距,就你现在这生活,哪像是客人?这穿着用度,这前呼后拥,说你是王后娘娘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啊!”
打量完布置得素雅精致而不失堂皇的璃苑,瞟了一眼门外鸦雀无声地站成整整齐齐两列的一等侍女,竹邪凤目邪光闪烁,似笑非笑,嘴中啧啧声不断。
我窝在热乎乎的炕上,裹得像一个雪白的蚕蛹,懒懒地翻了个白眼——凤竹邪,只有在出了大事又想卖弄的时候,才会这样废话不断。
“怎么,这醋味儿还没消?我说呢,怎么一进门就闻到一股酸味,我还以为是你长期不出门待在被窝里捂臭了!”
“狗嘴吐不出象牙……”
“啪!”
一个软绵绵的羊毛枕头凶狠地砸向他,他笑着轻快地一闪,伸手抓住枕头。
“这是哪家养在深闺的小姐啊?这是在抛定情信物呢,还是在丢杀人武器?几顿没吃饭了?”
“凤竹邪,你给我消停着,等我武功恢复了,你就继续耍贫嘴吧!”我半眯凤眼,发怒了。
“等你功夫恢复了——你在抱着什么幻想?你难道还要等澈涟主动给你送来解药?傻姑娘,别说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大师兄了,就算他有心给你送药,如今天日又是个什么形势?他有这个功夫跟你厮磨?”
竹邪敛起三分邪气,两分调侃,定定地看着我,很认真地道。
“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得无比难听。”我哼了一声,扭头翻身对着里墙不理睬他,却难掩一瞬间有些黯然的眼神。
身后传来轻盈的脚步声,竹邪走到床边,立了半晌,伸手摸了摸我的头,轻轻地叹了口气。
“兰雍的决策,想必你已经听说了,凤家的生意之所以遍及天下,其实仰赖的是天下太平,如今烽烟四起,诸侯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自立为王,凤家身为天日皇族后裔,本不该袖手旁观,但祖训如此,我们亦无话可说,我和兰雍站在局外看这场龙争虎斗也不错,只可惜你却深陷局中,我们岂能抛下你不管?”
听到这里,我心底早已惊疑不定,一个翻身坐起看向竹邪,却看到他望向我的眼底那来不及收回的沉重的担忧,像一块巨大的黑铁,沉甸甸地压向我的心头。
“好好的,说这些做什么?我们凤家早就决定保持中立,锡勒或天下诸侯以及澈涟,谁能凭自己的本事得到天下,凤家也愿将凤家的财富献给朝廷,用来初步治理和融合国家,其余的,凤家暂不考虑。这不是我们当初说好了的吗?”
竹邪睇着我微笑,坚定地摇摇头。
“你恐怕不知道,金凰令已经撤出了赤越两国,云莫离柳是非纪红绡领着他们向北而来,你除了收留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不是我们野心勃勃想要参与到这数百年前就注定好的倾覆重生的结局中,而是,命运不放过我们,在将我们一个个拉到他的轨道上去,沿着他的规则走下去!”
“你在说什么?”
我心底愈加不安,不由得一把拽住竹邪的手,却发现他的手心中,握着一个小小的瓶子,大概握了很久,那瓶子都有些发热了。
竹邪微微一动,我按住他的肩膀。
一根一根掰开竹邪的手,一个小拇指大小的透明琉璃瓶静静地躺在他的手心,瓶中装着一种深红色浓稠的液体,半满,缓缓地在瓶中流动着。
“这是什么?”我吸口气,轻声问,压根没发现自己的声音颤抖而沙哑。
“你的,解药。”竹邪抿唇,凤目底闪过一束光芒。
“怎么可能?”
我的解药?变异惑盅的解药?不是说这个需要下盅的人的鲜血做引子吗?起先药引应该是那个凤女的鲜血,后来经过西国一行,惑盅在我体内被澈涟改变,除了澈涟的血,恐怕无人能解。
“听兰雍说,澈涟,从你离开后,一直挺消沉的,朝政也不怎么用心,直到越国的反叛爆发,他才振作起来,兰雍就趁他消沉的那段时间,弄到了一点新鲜的血,可惜配解药花了不少时间,你身边那几个护法,要不是为了将解药带给你,怎么能容忍兰雍将纪门的精英们代替他们派到你身边?”
我的脑中纷纷乱乱,竹邪告诉我的话,化作了一条一条滑溜的蝌蚪,在我的脑海中游来游去,就是不肯集中到一起。
“西王遭人暗杀,暂时杀手身份不明,前天,西国公主白荷轩登位,继任西王王位,立刻下令西国将士全力提高警戒,做好一切迎战准备,自己则戎装检阅;而赤王与越国交界,战火令赤王十分害怕,便下旨任兰雍为相,兰雍等白荷轩一登上王位,就从西国赶回了赤国。”
“是么?”
西王,爽朗豪迈的西王被人刺杀了?那轩儿该有多伤心,虽然她以前一心想出家,可从来没有起过抛开相依为命的父亲的念头,各国间的气氛已经白热化到这种程度了?
“从今以后,你不仅要做好人身安全,更要注意饮食,凤家的人,渐渐被命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兰雍名虽为相,实则把持着整个赤国,西国白荷轩与你交好,又与兰雍相恋,南方三国,凤家已得其二,还有燕国的……,从今往后,惦记上我们凤家的人会会骆绎不绝,世人皆知凤女是凤谷所有人的掌上明珠,针对你的危险,恐怕会比我和兰雍多几倍不止。”
王宫西北方一个偏僻的小道,恺恺白雪掩映着一条羊肠小道,两边意外地栽种着不知名的植物,被雪压得弯了腰,竟然仍是一身绿墨般的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