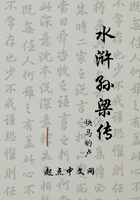却说季意如只因一时冲动中计,在去往学宫的窄巷遭遇埋伏。奈何季意如走得匆忙只有曾茂随行,如今只得趴在车厢底不敢抬头不说,唯一的战力曾茂也中箭负伤,形势可谓万分危急。
“想不到,我竟会栽在几个无名小卒的手上!”季意如来到此间的几日里常常幻想自己也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足以彪炳史册的业绩,却不想忽然间就莫名奇妙地中了埋伏,已是性命难保。
“曾茂中箭了,快围上去!斩杀季孙意如!”
正当季意如胡思乱想之际,不远处传来的命令声更是比飘落在他后颈上的雪花更具寒意。
“天亡我也……”
“诶呀!宗主快别说丧气话了,他们冲过来了,快拔剑。”曾茂说着又是一箭射翻一名刺客。
季意如闻言赶紧翻了个身,摸到左腰上佩戴的剑鞘,右手刚把长剑拔出一半,寒光闪过,两把锋利的长剑便朝他脑袋上砍来。
“锵!”季意如抬手挡住右侧袭来的剑刃,与此同时左侧的刺客也被曾茂一箭射落。
即便季意如迅速扭头躲闪,剑刃还是险险的擦过季意如的脖子,划出一条细口。
曾茂看在眼里,心中焦虑万分,奈何还有两人向他扑来,实在抽不出身。他左腿受伤行动不便,手中又只有一把木弓,与两人缠斗落在下风,这会儿身上多处挂彩,已是强弩之末。
就当季意如快要支持不住时,后方传来熟悉的声音:“快、快上。”
刺客听到呼喊,不自觉抬头去看,季意如抓住空当,一脚踹在那人手臂上。刺客站立不稳当即摔下马车。
季意如赶紧趁着空隙起身,寻找方才摔下马车的刺客,却见其人一瘸一拐地往远处巷口逃去。
眼见自己是抓不住那人了,季意如将手中长剑掷出,扰乱了围攻曾茂的一名刺客地进攻。曾茂乘机反手一弓甩在那人脸上。“扑通”一声,那人重重倒地,直接是不动了。
另一人眼见阳虎带人围了上了,自己无路可退,竟然直接提剑自刎,歪倒在地上,脖颈上血流如注,看样子也是活不了了。
“还跑了一人,你们几个快追。”阳虎先吩咐人继续追击,又走上近前,拜道,“属下来迟,请宗主恕罪。”
“先把曾茂送回府里医治。”说着季意如跳下车,摸了摸左颈的伤口,冷哼道,“怎么回事?”
阳虎看见季意如披头散发的狼狈样,脖子上还受了剑伤,咽了咽口水,把头埋得更低。“宗主走后,我当即率众赶来,不想还未走多远就有几辆马车堵在道上,所以晚了。”
“看出是哪家的马车么?”季意如冷冷地问道,“还有那个报信的仆从可曾捉住?”
“看不出,但那个仆从被子泄扣下了。”阳虎小心地回答道。
季意如刚想点头称好,却不想追寻刺客的士卒回报:“禀宗主,刺客不见了……”
“你说什么!废物!他有腿伤,还能飞了不成!”季意如顿时火冒三丈,转头看向阳虎,“你即刻去传令关闭所有城门,挨家挨户搜查,敢有不从者视为同党一并诛杀!”
环顾四周的几具尸体,感受到空气里浓浓的血腥味以及脖子上的伤口的疼痛,季意如不由捏紧了拳头。季意如本以为自己迁出曲阜的举措会让曲阜的暗流沉寂一段时间,自己也可以腾开手应对咄咄逼人的南蒯,没成想他的忍让反而让有些蠢货以为有机可趁。季意如心中暗道:那就要让他们知道惹怒他的代价。
“先回府。”季意如踏上已经准备好的矮凳,在士卒的搀扶下,登上马车。
待马车刚刚调转方向,季意如却是想起公之和公父靖还在学宫,于是吩咐两名士卒道:“你二人快去将二公子、三公子接回府里。”
“诺!”两人领命而去。
“走吧。”如今情况不明,没有多少侍卫相随,季意如也不敢在此处多逗留,还是尽早回府为妙。
风中的雪花越飞越密,季意如看向阴沉沉的天空,他知道马上曲阜就会迎来一场大雪。
待到马车行驶到季孙府附近时,季意如便看到了阳虎方才所说的那几辆马车,不过这会儿已经被一线排开,整齐排列在道路一侧还未被拖走。
季意如不由打量了一眼,总共六辆马车,的确是没有任何徽识,形制也很普通。
不一会儿,季意如便回到季孙府。待到马车停稳,季意如赶紧下车询问侍立在门口的冉怀,“怎么样,曾茂在哪?伤势如何?”
“您这是。”冉怀眼见季意如狼狈的模样就急欲呼唤医师。
“一点小伤不碍事。”季意如制止冉怀,又问道:“我问你话呢,曾茂在哪?带我去见他。”
“诺。”
片刻之后,季意如便随冉怀来到曾茂的床榻前。
屋里光线很暗,看不清曾茂伤势如何,但依着空气里弥漫的浓重血腥气,可以想见曾茂伤的不轻。
“宗主。”曾茂眼见是季意如前来,还欲挣扎起身。
季意如连忙上前扶住曾茂道:“快别动。你有伤在身,不必行礼。”
“属下惭愧,让宗主受伤了。”曾茂叹了口气,摇摇头。
“何愧之有啊,若不是你,我早就命丧黄泉了。”季意如轻拍曾茂肩膀道。“对了,你与几名刺客交手,可知其身份。”
“不知,但几人身手都稀松平常,不会是三桓的人。”
“我知道了,你且安心养伤,不要胡思乱想。”
说完季意如到后庭将头发重新梳理好,戴上头盔,又披上许久未穿的戎装后来到中庭。
“子泄,那个仆从呢?”
“咬舌自尽了。”公山不狃沉声道。
“自尽了。”季意如闻言冷笑道,“狠角色还真不少啊,看来有人真想‘留住’我。”
公山不狃心知季意如心中恼怒,但还是劝道:“宗主,为今之计,该是大开城门,告知鲁人有刺客行刺未遂、用以安稳人心才对。”
“有人要杀我,我差点死掉!我却还要大开城门放刺客离开不成。”季意如闻言情绪有些激动,“我有士卒五千,加上叔孙、孟孙两家兵力过万,我何惧之有!”
“孟孙自是会全力支持宗主,叔孙却说不定了,争端一起,让南蒯得了便宜不说,还会让您背上犯上作乱的骂名。”公若也连忙劝道,“宗主就此作罢吧,等收复了费邑,届时您要如何复仇,没人拦得住你。”
“别说了!我意已决,骂名又如何,南蒯又如何,不斩杀幕后之人,我决不罢休!”
“宗主、宗主!”
季意如对门口的侍卫吩咐道:“拦住他们。”
看着季意如远去,公输叙叹道:“宗主如此意气用事,今后恐怕还会再起事端。”
“今后?眼下不就是么。”公若摇摇头,插话道。
“我担心的倒不是如今曲阜的局势,而是晋国的态度。倘若是晋国以‘犯上作乱为由’攻伐季氏,到时候情势可真就危险了。”公山不狃沉声道。
“的确如此,不止晋国会伺机而动,楚国急欲东进,势必也会想着来分一杯羹。”公输叙道。
“不行,让宗主这么胡来,怕是会葬送季氏前途。等宗主离去,子泄,你去寻孟孙家宰,我去寻执政,公输司徒便留守季孙府,等候消息,如何?”公若看向身侧的公山不狃和公输叙。
“好。”二人相视一眼,点头称是。
不说公山不狃几人如何谋划,只说季意如迎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固执地领着一队侍卫向府门外而去。
随着耳边的呼声渐渐模糊,其实季意如也大致明白了公山不狃的意思。
打开城门便是向卿大夫们妥协,表明自己不在追究刺杀之事。同时也告知民众他季意如没死,鲁国还没有变天,得以安稳人心。
而且细细想来此事的确查不得,一查便准会与国君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说到底没有国君的首肯,那些卿大夫也没那个胆子来刺杀季氏宗主。加之昨日子家子又和国君发生了争执,更是印证了国君参与其中甚至就是幕后主使的设想。
可季意如左想右想,就是咽不下这口气,非得查出个结果来,哪怕是背锅的也行。
思索间,两道少年身影便从门外向他急切地扑来。
年龄稍大一些的是季意如的二弟公之,稍小些的是三弟公父靖。
公父靖看见季意如脖子上的伤口,连忙问道:“大哥你没事吧。”
“没事,一点皮外伤。”季意如嘴角挤出一抹微笑,说着又看向公之,“二弟埋着个脑袋作甚,莫非你真出手打了司铎。”
“我没有。”公之连忙抬头看向季意如。
“既然没有就打起精神,今日之事与你无关,你也无需自责。”季意如拍了拍公之的肩膀道。
“好了,大哥还要去找仇家算账。你们都留在府里,哪也不准去。”
说完,季意如便领着一众侍卫径直走到门口乘上战车往城东军营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