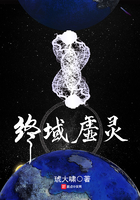翌日,天色未亮。
“立冬有多久了?真是越发冷了。”季意如还没睡舒服,便被冉怀早早唤醒,像衣架子一般被一件件服饰套上。虽是冬日常服但也是繁复的紧,也需得早起,不然要是因为这是耽误了家朝就难看了。
“算起来有一个月。”冉怀小心地捧来一套精美的组玉佩,将系壁系于革带,“不过似乎今年是要格外冷一些。”
“怎么说?”季意如微微皱眉,毕竟农业社会对天气十分依赖,季意如自然格外重视。
冉怀一边将系壁下端遍施透雕的珩玉以及壁、瑗等一一理顺,一边回道:“沂水已经开始结冰了,比去年早了许多天。”
听冉怀这么一说,季意如心中焦虑的同时,忽然想起前几日还在凛凛寒风中建造郎囿的民工们,想着待会儿便要将这是妥善处理。
等到各项事情照规矩一一办妥,东方也露出了鱼肚白。季意如缓步迈上前庭的高台,而太阳也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橙红的阳光铺洒在远处沂水及其南北岸的雪地上,被朝阳照透的水汽氤氲,如梦似幻,宛如仙境。暖色的阳光洒在古朴庄严的正殿上,廊下整齐列队的士兵手中打磨锃亮的铜戈迎光闪烁。
感受着渐渐温暖的阳光,季意如稳稳地登上最后一阶。
“宗主到!”
迎着家臣们各异的眼神,以及侍卫的高呼,季意如缓步走到首位,心中暗自松了口气,虽然走动过程还是有玉璧轻微的碰撞声,但也算是成功地避免叮叮当当响个不停的尴尬局面。
“拜见宗主。”眼见着季意如转过身,众位家臣跪拜行礼,异口同声地呼道。
季意如也是头一回见这阵仗,只觉着口干舌燥,下意识舔了舔嘴唇,“诸位请起。”
眼见得差不多,季意如便率先落座,宣布家朝开始,“今日议政,诸位可以畅所欲言,不必拘谨。”
只见季意如话音刚落,便一人起身上前道:“宗主,臣有要事禀报。”说话之人满头斑白,衣着朴素,正是季孙氏家宰公山显。
季意如也知道此人在季孙氏中的地位崇高,连忙应道:“先生,请讲。”
公山显微微一礼,正色道:“禀宗主,今早得报,沂水在前夜开始结冰,算起来比往年早出八日之多,可见今年冬天将比往年寒冷。如此,一来要准备更多木炭以及冬衣以备严寒,二来要提防东夷因猎物匮乏而下山掳掠。”
季意如正有面对严寒的担忧,而公山显这么一说,倒是瞌睡碰到枕头。
“我正有如此担忧,准备物资之事还要劳烦先生。”季意如顿了顿,“至于后者,老祁、虑癸何在?”
“臣在。”二个中年人上前听令。
“命你二人为费邑司徒,协助南蒯做好防备。即日启程,不得有误。”季意如这般吩咐也是有道理的。
如今的费邑宰是故去重臣南遗之子,此人依仗着父亲的功劳很是倨傲。而季孙意如也不是客气的主,于是两人便互生嫌隙,奈何此父子二人在费邑的军队之中素有声望,季意如也是动他不得,只好派老祁、虑癸借着防备东夷的由头前去分权。
待二人领命出了正殿,又有一人趋步上前道:“臣阳货(阳虎)有事禀报。”
季意如看着眼前长得忠厚老实的年轻人,简直不敢相信这便是《论语》中提到的那个奸臣。倘若季平子知道当初他以“货有益而无害”起名的阳货险些葬送了季孙氏,不知会是怎样的表情。
“讲。”对于这个危险分子,纵然季意如知道此人从前季平子赏识,却是演不出什么好脸色。
不光阳货觉着季意如语气反常,堂下坐着的诸位家臣也微微侧着脑袋相互交换眼色。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阳货都站出来了,岂有退回去的道理,便硬着头皮回到:“禀宗主,昨日曾茂去了营地,今早又不见其人,此事不得不防啊。”
听闻此言,季意如心中一凛,面上却是不变颜色,转而询问公山显,“先生可知此事。”
“请宗主恕罪,臣观宗主闭门不出,不许群臣探望,其中颇有蹊跷,便令曾茂率兵于外,以备有变。”公山显赶紧趋步上前请罪。
虽说公山显此举出于公心,但还是让季意如十分忌惮,不经宗主允许,家臣就可以任意调动军队,实在是让他有些无法忍受。远的不说,就说南蒯一人便让他十分难受了。季意如心中有些不忿,面上却是不表露出来,且先混过这次家朝再说。
“阳货,你先退下。这本是我的过错,将事情隐瞒了许久,让诸位心忧。”季意如先是诚恳地向堂下众人表示歉意,又摇摇头,哀叹一声,开始胡说八道,“传言说我病了,确是如此,只是病不在身,而在心中啊?”
不待众人接话,季意如轻轻站起身,走到堂下,环视一番周围的家臣们,继续说道:“那日我回府之后,确实略有不适,便想着小憩一会儿,却不曾想越睡越沉,做了一个噩梦。”
眼见着季意如欲言又止,阳货连忙出声接话:“敢问宗主梦到何物?”
季意如心中暗暗叫好,奸臣也是有奸臣的好处,便又做悲痛状道:“楼台宫室皆成灰烬,山河千里尽成焦土。”季意如说完闭上眼睛,深深吸气,“更为奇怪的是,当我醒来却是想不起许多事来,故而几日里闭门不出,才堪堪理清思绪。”
季意如此言一出,四下皆寂,家臣们或面露惊恐,或眉头紧锁,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说话。毕竟这还是先秦时期,人们十分敬畏鬼神,将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归结于上天的预示和惩戒。
沉默许久,德高望重的公山显感觉越来越多的目光汇集在背后,不得已才缓缓说道:“宗主所梦,该是昊天赐下的警示。如今鲁国国小民贫,周遭狼群四顾,局势每况愈下,可惜鲁国之内也是暗流涌动,人心向背。如此多事之秋,宗主之梦,正应此景啊。”
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堂下群臣顿时就炸了锅,也顾不得礼仪交头接耳,你一言我一语,整个正堂躁动起来。
“肃静!”冉怀站在堂前大吼一声,霎时稳定了隐隐要喧闹起来的气氛。
“诸位,既然昊天将警示降下,便是不忍生灵涂炭,不忍我季孙覆亡。如此我当奋发图强,以为表率,而诸位也应尽心竭力,恪尽职守,以报昊天恩情。”说着季意如又环视堂下群臣,“当此之时,诸位可有良谋?”
话音刚落,便有一青年男子起身出列,趋步上前,其人身形修长,丰神俊朗,正是季孙家宰之子公山不狃,“禀宗主,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子泄,直说无妨。”季意如正色道。对于这位历史上最终因为政见不合,最终彻底与季平子反目的心腹重臣,他是一定要彻底收为己用的。毕竟他季意如是讲道理的当代好青年,可不是无法无天,嚣张跋扈的季平子。
“臣以为,鲁国之患恐不在他国,而在萧墙之内。我季孙手握重兵,位高权重,国君已是忌惮万分。事实上,百年积怨之下,这曲阜城已是一口滚滚油鼎,一旦有奸人作祟,便会热油迸溅。臣以为既然执政之位在叔孙,宗主不若转而他居,将这烂摊子交与叔孙,我季孙自去厉兵秣马,整顿吏治,以备有变。”
“子泄之言有理,不过我该转居何处啊?”季意如微微颔首,表示赞同,不顾群臣惊诧,又接着问道。
“依臣之间卞邑是为上选。”公山不狃快速回到。
“看来子泄早就是成竹在胸了,可费邑城高而民多,商贾云集,经营已久,何以弃大城而就鄙邑?”季意如笑了笑,心中暗道此子甚合我意,又接着问道。
公山不狃恭恭敬敬地拜倒:“宗主心中已有计较,有何必问臣呢。”
“哈哈哈哈——”季意如放肆地笑了笑,“好!我意已决!诸位回去各司其职,加紧准备,明日我便面见君上,转而居卞。子泄留下,其他人便回吧。”
“散朝!”冉怀适时高呼。
“臣告退。”众家臣纷纷告退。
待家臣们离去,季意如才吩咐道:“冉怀,你去取些鲁贝分发给郎囿民工,便说是严冬里的补偿。子泄你随我去后庭走走。”
“额,宗主这不妥吧。”公山不狃不敢答应,毕竟后庭有府里的女眷,他一个家臣在后庭走动实在是太无礼。
“哈哈哈,我已将侍妾女婢全部遣散,只留下冉怀和几个服侍的寺人。如今你大可去得。”季意如拍拍公山不狃的肩膀笑道。
“宗主这又是何必呢?堂堂的鲁国大司徒的府中岂能无一女子。”公山不狃打趣道。
“我为宗主,身为表率,当此之时,应当克勤克俭,又岂能留恋于温柔乡中。”季意如认真说道。
“此时何患之有,宗主何不直说呢?”公山不狃看了眼一脸认真的季意如。
“子泄不也没说吗。”季意如轻笑道。
公山不狃摇头轻叹:“也是,如今费邑是去不得了,南蒯此人居父功以自傲,本就是个败类,如今却是明目张胆地征召士卒,如今已有六千之众。而眼下我们只有不足五千士卒,一旦他起了贼心,将局势搅浑了,反倒让他人捡了便宜。”
季意如点点头,收起笑意:“是啊,我派老祁、虑癸二人前去,也只为试探其人,若是他聪明就该分出兵权。”
二人说话间,便到了一路走到了中庭。
一丝丝寒风透过门窗缝隙钻进偌大的殿宇,黄色的灯焰微微摇摆,将微弱的光芒投射到一张粗糙的皮卷上。仔细打量,原来是一副地图,而地图前正站着两个青年人。白衣者侍立于侧,赤衣者负手而立,正是公山不狃与季意如二人。
“宗主请看,我季孙城邑大致都在东蒙山与尼丘山之间,西北有卞邑临近曲阜,东南有防邑邰邑分别与鄅国莒国相邻,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倘若能除去夷人之患,便是个可靠的去处。”公山不狃叹息道。
“夷人也是人,只是不服教化,以鱼猎为生罢了。待到大雪封山,食物匮乏之际,自然会下山掠夺。”季意如微微摇头,并不同意公山不狃后半句话,“转居卞邑之后我欲派人入山与之协商,若能化干戈为玉帛,又何必兴兵劳民呢?”
季意如毕竟是后世之人,看问题的眼光与古人颇有差异。在他看来,不论是在中原人还是东夷、淮夷、百越乃至狄人都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中华儿女。他们只不过是迫于生存以及文化差异而与中原人交恶。和谐共存,互相交融,汲取彼此可取之处才是长久之计。
当然这些都是出于互相尊重的前提之下,如若是对方蛮不讲理,凶残成性,侵害百姓,那也必须贯彻“虽远必诛”的理念。
对于长期听闻夷人之害的公山不狃而言,季意如的说法实在是有些荒谬,在他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更具说服力。“宗主前些时日,不是还欲剿灭之么,今日为何又要怀柔之呢?”
季意如被问得一愣,毕竟他也不知道季平子的态度。“额,我在梦中好似历经一番生死,颇有所悟,已不再是从前的意如了。”
季意如回想来到此间的几日里的见闻,一时感慨万千,不待公山不狃接话,又道:“如今天下看似风波平静,实则是暗流涌动,波谲云诡。所谓平分霸权,不过是丧失霸权的遮羞布罢了,当今的晋楚已远非昔日的晋楚了。”
季意如微微摇头,又看向公山不狃。“纵然二者仍是六千乘的大国,可是人心已散。晋国的卿族各自为政,平日里勾心斗角,纷争不断,楚子昏庸,荒淫无度,重用佞臣,如此种种皆亡国之兆也。”
公山不狃有些不解,问道:“可这又与鲁国何干?与夷人何干?”
季意如思索片刻又道:“当然有关,我且问你,晋楚失霸之后,谁最有机会成为新的霸主?”
“吴国。”公山不狃稍加思索便脱口而出。
季意如本来是觉得吴国崛起不就是历史大势么,脱口一说,没想到似乎点醒了公山不狃,于是只好接话道。“说说看。”
“晋楚吴三国淮上纷争数十年,如今看来晋国既然未邀吴国参与弭兵之会,便是鞭长莫及,抛下吴国不管,意欲牺牲吴国耳。可惜晋人不曾想,吴人勇猛,居然能几次挫败楚军。以当今形势而言,楚国腐朽,每日积弱,吴国兴盛,每日愈强,依我看至多两代,吴人必定能大败楚人。”
公山不狃说着又指了指鲁国南方。“原来如此,彭城,彭城乃要害之地。适时吴人必经彭城北上,以图称霸。而彭城周围淮夷四顾,如此以来东夷便是决定局势的要害之一。”
看着一脸激动的公山不狃,季意如微微错愕,又道:“倘若楚国胜了呢?”
事实上季意如始终认为历史存在一个大趋势,即便是他的到来对这个世界有所影响,但应该不至于使得根底深厚的楚国陡然亡了。
“楚国若是胜了,或再无可敌之国。”公山不狃皱眉道。
季意如看形势不对,这要是再说下去,他肚子立刻就没货了,赶紧转移开话题。
“不过日后之事谁又说得清呢,只是须知眼下鲁国或说我季孙危机深重罢了。”季意如不再看图,又从案上拿起一卷竹简递给公山不狃,“子泄请看,这是我新制之历,你看比之当下所用之历如何。”
季意如前几日饱受旧历之苦,实在是没弄明白现行历法究竟是怎么回事,便在公历基础上加上二十四节气做了这新历。
这下轮到公山不狃一脸错愕了,捧过竹简看了许久,又把竹简双手奉还。“这这这,宗主勿怪,臣却是不善历法,宗主或可询问梓慎大夫。”
“好吧。”季意如接过竹简,点头道。
沉默间,冉怀回府复命打破了尴尬气氛。
公山不狃适时说道:“宗主,眼下转居卞邑之事事务繁杂,若是无要事吩咐,臣便告退了。”
“子泄稍候。”季意如唤住公山不狃,又从腰间解下一块玉璧递给他,“将它转交给令尊,持此玉璧便如我亲临。这几日倘如有奸猾之辈不服号令,无需问我,令尊可自行决断。”
捧过季意如的玉璧,公山不狃深深吸了一口气,“谢宗主。”
“去吧。”季意如点点头。
“臣告退。”
季意如望着公山不狃的背影远去,心头有种说不上来的滋味,呼出一口长气,又转身回到简陋的地图前。
“事情都办妥了?”季意如问道。
冉怀赶忙上前回道:“办妥了,匠人和庶民都对宗主感恩戴德呢。”
“那就好,来帮我掌灯。”季意如一边看图一边说着。
冉怀闻命便捧过油盏,走到季意如跟前。灯光照亮了季意如所指的地方,宋国。既然季意如穿到鲁国,那么宋玉容该是大概率穿到宋国,毕竟他一个半吊子历史爱好者除了宋国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和宋密切相关的。
季意如看了一眼在一旁掌灯的冉怀才想张口又算了,想来他也不可能知道宋国茫茫人海中某个叫玉容的人。
冉怀迎着季意如的目光说道:“宗主是有什么打算吗?”说完冉怀便将目光移至季意如胸口,以免显得咄咄逼人。
“鲁宋两国很久没有互相聘问了吧?”
“的确如此,宗主是想与宋国交好么?”
季意如闻言却是不说话,只是轻轻叹息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