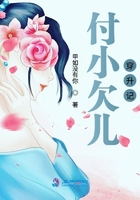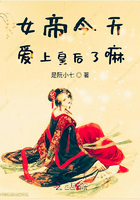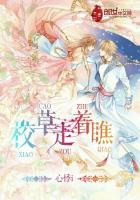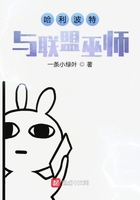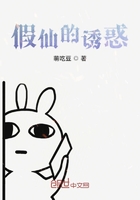天蒙蒙亮,梁家村二十多户人家便开始活泛起来了。已经到了秋末,各家各户都在抓紧时间晒粮食。
天也亮的越来越早了。
已经焕然一新的王家屋棚也开始热闹起来。先起来的是大娘,自从收完了地里的粮食,大娘就开始负责做饭了。
有了点存粮之后,大娘也会不时地煮上一碗米汤,所以现在我们也能时不时的喝一碗稀汤了。
当然对于我来说还是吃不饱,每天还是饿的挺难受的。
不一会二娘也起来了,还喊上了我,带上家里的脏衣服准备去河边洗刷。
半月前我碰上了去县里的牛车,便先斩后奏的去买了一匹最便宜的布,针线也没忘,又好说歹说把一些碎布头啊什么的带上。上次来县里累了个半死,却只记着买吃的了。
回来之后让二娘拿了五百个钱,大娘虽然不大高兴可是也没办法,总不能不给吧。
于是我们现在一人差补了一身新衣。也不算新衣,大娘把我们的旧衣拆开来配上新布料,这才有了件“新衣”。
这些天二娘正和村里的大娘们学做布鞋呢。想来不久便有鞋穿了。
在此之前我们都穿的是草鞋。
早饭吃的是菜糊糊配上一点小米煮的“菜粥”。放了点盐调味也不是那么难以入口。
这几天我正准备晒点青菜做酸菜。和大娘打了声招呼,托人买了五只大坛子。说是大坛子也就半人高。我觉得不太够吃,只不过家里的盐只够这么多了。
家里原有一亩的菜地,青菜种了一小片,剩下一部分的芦菔,也就是萝卜,还有一部分的野韭菜和豆子。
那上次的植物根茎就是二娘随意挖来哄我的了,大娘竟然也不阻挡。
看来傻了那么些年,姐妹几个多少有怨气啊,又或者是觉得我有些挑剔?我也不大清楚。
秋末的河水还是有点冷的,洗完衣服两人的手都有些红。太阳渐渐出来了,我们得赶回去和大娘一起把粮食背到村口晒,村口有片晒粮食的平地,是村里人特意收拾出来的。
而四娘带着五郎就去那里守着不让鸟儿偷粮食,二娘去学做鞋了,大娘就带着我去收菜。
前些天的柿子我没卖,说服了大娘要晒成柿饼,那时候卖给县里的大户人家,也能得不少钱。
把一些青菜和萝卜收了,青菜稍微过水,萝卜切成丁,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一会儿,去去水汽。
因为要用淘米水泡酸菜,这几天我们都是喝的稀饭。倒是把家里的伙食改善了些,虽然也吃不饱。
大娘说过了这几天就不能这么破费了,家里的存粮天天这样吃怎么抵得住。
我算了一下手里的现钱,本来有十五贯,一贯是一千文,做房子花了一贯买一些家具用了一贯,又添了些过冬的棉花,零零散散用掉了三贯。还好还好,和大娘偷偷商量着打个地窖还有钱打。
本来也没想着做地窖的,可是前天存了点积分就开了1527看看下有没有什么金手指之类的,意外被告知过两年这个燕国要起战乱了。
我就决定先存些粮食。大不了可以先去买些。黍子一斤才五文钱,一贯能买两百斤呢。
这个梁家村还是离燕国的首都有点距离的,往上过了小河村再过一个大河村就到京都附近了。燕国的皇帝对粮食这一块看的比较重,重农抑商,但是和记忆里熟悉的那样,寒门无贵子。
等我们把地里的菜收回来后已经是过了两天,柿饼已经晒的差不多了。
才和大娘她们说柿饼的时候得知这边还没有这种说法的,当季的水果大多是当季吃,最多放在地窖里保存,可稍稍放的久些。正好让我钻个空子,换点钱来过活。
因为是野柿子,个头不是很大,个别的还比较酸涩。将那些品相好的挑拣出来,剩下的再挑些去送给村里人做做人情,姐妹几个一分也不剩下什么了。几大框野柿子就剩下两筐百来个了,再加上剥皮晒干,到最后只有一坛的样子。
晒好的柿饼是漂亮的橙黄色,带上一层薄薄的白霜,小小的一个分外诱人。一个最多五郎拳头大,讲究点的够两口,急性子的一口就没了。
这天吃完晚饭,我去厨房里开了放柿饼的坛子,拿了五个出来给姐妹几个甜甜嘴。
平时的吃食实在简陋,一分甜味在嘴里更是放到无限大来看。柿饼又比新鲜的柿子软糯可口,姐妹几个一尝眼睛就瞪大了。又因为小小的一个,就算是五郎的小嘴巴也只不过多分了两口。
“怎么样,味道如何?”我眨了眨眼睛问看着我的大娘,等她说出我想要的答案。
“好吃极了!三娘!”二娘是个嘴快的,在大娘回答前就没忍住先开了口,又和四娘五郎两个勾眉搭眼一番,惹的大娘也有了些许笑意。
“你说,若是让木匠打个小盒,里面再垫上油纸,一个小盒里放上几块,能卖到大户人家去吗。”
虽是问句,但是语气让人无法反驳,几个孩子埋头一想,觉得问题不大。
“油纸就不必了,也是一笔花费,盒子就很好了。”二娘提议道。
我和二娘商量了一下,才知道油纸不便宜,想着降低成本也不错,盒子包装本来就比路边上人家草纸包的讲究多了,还有的都没有包装呢。于是就决定去掉油纸。
大娘是最高兴的了,本来就她年龄最大,又有好几个人要养,这下有了来钱的路子了。不必一味种田死磕了,肩上的担子也轻了许多。
不过田也是要种的。
“但是你这柿饼不过也就是晒晒,没什么诀窍,到时候有心人明眼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再一个,若是到人家的庄子上,吃多了也就知道了。”
年龄大了还是仔细周到的。
我料到这些了,将我打算先卖着一季打个开头,再带动村里人一齐晒,我自有办法再做个新鲜的玩意儿拿出来说了。
看我信心满满的样子,大娘也不疑有他,不再多说什么了。
第二天,便从木匠那里打了五个个六寸的木盒,分别装上五块柿饼就做上牛车去县里了。
我打听好的是一户商贾,在这个云县里也不算数一数二的,但是也比我们这些农户富裕许多,主要是看着他们家人个个白白胖胖的,想是花个几文钱在这初冬里吃上点新鲜玩意也不算做什么的。
巧的是那户人家也姓王,我去敲门的时候也算有个搭话的由头了。
敲开了门我先问了好,开门的是他家小儿子,十岁的样子,我将那柿饼拿出来给了他瞧,他一闻着味儿就将他娘喊了出来。
“一个两文嘞,这是柿饼,就是柿子晒出来的,买几个给甜甜嘴罢”
鸡蛋一个才一文钱,黍子一斤才五文钱,不过也抵不住那小儿缠。
最终那妇人买了一盒。只不过没要我的盒子,盒子我还多收十文钱的。找木匠打的盒子一个五文凑了五个,要不然得要我六文一个。
这样卖效率太低了,最后我决定将这些个柿饼卖给县里的大户,和县令沾亲带故的那种,那家果然把剩下的都买了,甚至连盒子一齐收了,还喊我如果还有就都拿来。
我答应过两天带来。
五盒柿饼,盒子打了二十五文,就是成本费,一个卖十文去掉成本四个盒子就赚了二十文,加上二十五个柿饼一个两文就是五十文,合计净赚七十五文。
不错不错。
家里还有七十个柿饼,再打十三个盒子,十四个盒子加上柿饼能赚二百一十文。
看来还得去讲一下盒子的价钱,没必要做那么实诚嘛,薄一点粗糙一些都可以的,反正人家也不一定看得上这小盒子。
又转头去买了十斤盐,一个大的瓦罐,去屠户那捡了些猪大骨,外加了两斤肥肉回去炼油。两百文没有了。再加上在药堂买了半斤生姜用去二十文,走的时候我还问大娘要了两百钱,扣去坐车的四文和买了十六个肉包子花了十六文,我手里就只剩下三十五文钱。
想着家里啥都没有,我又咬牙买了黍子压的面粉,六文一斤我买了五斤。
回到家时交到大娘手里就只有五文了。大娘叹了口气,倒也没说什么。几个小的到半夜里还笑着谈论着买回来的吃食。
第二日我又和木匠讲价,单子还算大的,十四个小木盒,也不要什么装饰,只给我便宜了十文钱,收了六十文。
中午的时候我就将猪大骨煮了,加了点生姜去腥,肉香味飘了半个村子。
还好秋收之后家家户户都食补过了,倒也不觉得太突兀。
煮汤用的是我新买的大瓦罐,喝汤管够,骨头炖的软烂,嚼一嚼都能吞下去。
生姜还能去寒气,就着蒸的窝头,孩子们都吃了个肚儿圆。脸上也有了丝红润了。
“吃的和过年一样。”这是几个孩子的心声。
原先只有过年的时候,王翠儿才会割点猪肉回来让大家尝个肉味,现在两天便能喝一碗蛋汤,现在又喝起了肉汤,而且吃得饱饱的。菜里也有油味了,还有柿子和梨吃,还喝了糖水,三娘还带回来了花肉能炼油,还有肉包子和面馒头……
就算是王翠儿在的时候,也没有吃的这样丰盛的。
大娘和二娘,四娘和五郎,一齐看向了我——这一切变化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