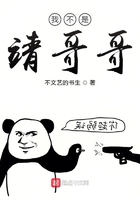齐相宜面上的神色并不好看,苏絮暗自猜测着,只怕香橼带过来的消息必定不是什么顶好的消息。她眼睑不住的跳动,再不看齐相宜,垂首拿了茗茶呷了一口,以平复惴惴跳动的心绪。待苏絮再抬头的时候,便瞧见齐相宜起了身,从她身前走过时,微顿了顿脚步。苏絮立时懂了齐相宜的意思,回首将茶盏撂在桌案上,细不可查的颔首。齐相宜瞧见她的神色,才继续往外去。她长及曳地的裙摆从苏絮的脚边划过,静谧无声。
待齐相宜走了小半刻,苏絮才起身。对着太后微微一福,柔柔笑道:“臣妾去更衣,凉快凉快。”太后正全神贯注的看着台上刀马旦耍花枪,随意点了点头。苏絮便悄声的下了看席,从下面的回廊往后院去。
院子里香橼守着一处厢房,苏絮回身与春如道:“回去取那件雨过天晴色绣玫瑰纹的蝉翼纱外裳,月白青葱色云天水漾绸子地儿的留仙裙,也能凉快儿一些。”春如喏喏道了句是,苏絮才往厢房去。
她迈进门,便瞧见了齐相宜愁眉苦脸的撑着下颌。面上忧愤不已,方才腰间垂下配着羊脂缠花玉玦的络子乱乱的散在裙摆上,丝线被来回来去绞散了。苏絮缓步走近,坐在她身边,轻声道:“怎么,有不好的消息?”
齐相宜咬一咬唇道:“姚木槿那肚子当真是安稳,这般折腾,却还不小产。方才香橼说,她跟着回了御医院,细细打听过了。姚木槿没小产,安稳这呢。现下宣了淮安王妃去宣曲宫,我只怕于咱们没有半分的好处。”
苏絮闻言,虽然心里也极是不快,却仍旧敛容,安慰齐相宜道:“今次不成便也算了,当真生下来,却也未必能安安稳稳的养大。你也晓得,宫里阴气重,生养孩子有多不容易。这种伤阴鸷的事儿,不如就此作罢。”
齐相宜听得苏絮的话,瞧出了她迟疑不决,萌生退意。当即眉心一颤,鼻尖便有些酸酸的不舒服,她牵出帕子挡在鼻子前,稳了稳心神,道:“若当真由着她把孩子生下来,必定是要封妃的了。如果是个皇子,她既有出身,淮安王那一边也是她的势力,再加上与淮安王一向亲近的博陵王。姚家如今因着鲜卑忽然来犯,又有冀州的兵权在手。那个皇子的背后,有多大的支持!”
苏絮不是没有齐相宜这样的顾虑,她紧紧抿唇,睨着齐相宜沉吟着开口,“二皇子也有顾家支持……”
“纵然顾家是士族之首,可再大也大不过亲王。淮安王妃是姚家的人,博陵王妃是兰陵萧家的。还有淮安王的同母姐姐同昌长公主,博陵王的姐姐清河长公主。”齐相宜摆首极是忧心道,“妹妹该晓得,后宫前朝,一向绑在一块儿的。现下趁她根基未稳,倒也好对付她。只怕等她生子封妃之后,咱们便是再难撼动她了。届时,协理六宫之权也要与她姚氏分一杯羹。”
苏絮极是犹豫的凝着齐相宜,牵唇勉力一笑,劝道:“虽然我不是士族出身,可好歹除了顾家,弘农杨氏的当家祖母是汉阳长公主的嫡亲姊妹。士族有顾家与杨家两个,还有两位嫡出的公主。”
齐相宜不以为然的笑起,摆首闷声道:“妹妹别忘了,同昌长公主与清河长公主的夫婿是谁!到底是延泓与妹妹这边不及姚木槿那边人多势众,为公为私,她这孩子也不该生下来。”
苏絮听着齐相宜这话,忽地升起了从前不曾有过的恐惧感。她骤然惊惧,如皇后、宣顺夫人那般,实在不得不计划深远,防患于未然了。或者,自己心里那颗欲望的种子,历经今日与江沁澜关于太后的对话后,便被浇灌出来。原本在心里隐隐约约总觉得万无一失的东西,如今被齐相宜这样点播一下,越发惴惴。她蹙眉,将自己的思绪稳住,小声道:“皇上惦念着皇后,不会轻易放弃泓儿的。”
齐相宜微微叹息,手指敲击着桌沿儿,发出“笃笃”的声响。一字一顿道:“时间!再刻骨铭心的东西,只怕也要被时间磨平了。”她语顿,停了手指上的动作,蓦地抬头,清澈的眼眸仿佛照进了苏絮的心里,“妹妹敢保证皇上会一直待妹妹如此,会一直待延泓如此吗?延泓还是三、两岁的黄口小儿,要长成总得个十年。十年后的事儿,谁又说得好呢?你若不信,便只看看林倩蓉的下场。”
苏絮听着齐相宜的话,忍不住紧紧的咬着嘴唇。她从未有过像今日这般的惧怕和忧虑,她这才忽然惊觉,这两年霍景嵩对她的宠爱,让她渐渐也有恃无恐起来。如今齐相宜便仿佛当头棒喝一样,一盆冷水兜头罩脸的泼在她的身上,令她前所未有的清醒下来。便如林倩蓉处处苦心孤诣的算计,还是被贬黜赐死。如今姚木槿已经成为她们的敌人,若是不想被鱼肉,便要早早的把那点子她祸害自己与齐相宜、江沁澜的机会早早掐死、扼杀。苏絮下意识的连连点头,嘴唇有些发白,迭声道:“姐姐说的是。”
此刻院子里传来了明快的笑声,一听便晓得是延泓等人。齐相宜忽然起身,上前几步推开了那窗子。延淅遮着眼睛,听着旁边怯怯的笑声和脚步声,去抓月夕。夕阳从窗子透进来,金灿灿的拢着齐相宜。可齐相宜回首看着苏絮的眼神,是深切的怨毒,她冷然道:“告诉昭云归,他既是院使,总有办法将那孩子拿下去。”
苏絮心里闪过一丝侥幸,她想昭云归心里有她,只要她说出来,昭云归必定会为她去做的吧。她鬼使神差一般的点头,却蓦地被仅有的半分清明攥住了神思,眉头紧蹙,又摇了头道:“不,不齐姐姐,我不能让昭大人做这样的事儿。姚木槿,她肚子里的孩子总是无辜的,总是……”
残阳的光照在齐相宜的脸上,血红血红的耀目。她听见苏絮这话,浑身禁不住有轻微的发抖,几乎要失声痛哭起来,她上前两步,箍住苏絮的双臂,反问道:“难道我的孩子就不无辜吗?我的泽儿就该死吗?妹妹,你可怜姚木槿,她会可怜咱们吗。这样的人,难道你还要等着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吗?”
苏絮心猿意马,“没有,我没有可怜姚木槿,我只是可怜那个孩子。咱们总会寻到她的蛛丝马迹,到时候把那孩子养在姐姐膝下……”
齐相宜仿佛听见笑话一般,“还没生下来,有什么好可怜的。这时候没了,不过是一滩血肉。可等他生下来,”齐相宜长长的一声叹气,“生在帝王家,该是多悲苦的一件事儿。有那样的母妃,必定会踏上夺嫡这条路。若他有朝一日成为延泓的障碍,你难道还说他是无辜的吗?絮儿,你心太软了,你如今还是看不清。你受了这么多的苦,难道还不晓得如何在这宫里安稳的活下去吗?你之前下了狠心,如今又要退缩。你怕什么,你过不去什么?”
“要踩着别人的尸骨,吞着别人的血肉活下去。”苏絮方才不过是有一瞬间的不忍,可想起齐相宜的双生子,到底将心狠了下来。她反手握住齐相宜,连声道:“今晚,今晚我就宣昭云归来储元宫。”
齐相宜不理苏絮的这番话,极是认真的盯着她,重复道:“絮儿,你总在顾虑什么,你总在为难什么?你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可迟疑不决的?”
苏絮思绪纷乱,答不上齐相宜的话。挣脱了齐相宜的双手,她仿似极为疲惫的靠进了圈椅中。也不言语,她说不出来心里到底顾虑着什么。半晌,苏絮才以细不可闻的声音,颤颤的开口,“姐姐,我怕当真下了这个手,终其一生,我都要活在不死不休的争斗中。我怕,再没有全身而退的机会。”她说出这番话,极是无力道:“从头至尾,我都只期盼被一个人捧在手心儿里呵护照顾。我也是想与人无争的啊”
这话说的齐相宜微微发愣,她忽然闭目,方才隐着的泪,从眼角落下,折射的阳光,仿佛金子似的。她极为缓慢,凄绝道:“我又何尝不是呢?可,咱们早就没了退路了。”齐相宜话落,二人便是都禁不住心里的酸涩,默默相对无言。
待春如送来衣裳,苏絮换过之后,两个人才勉强整理了神色思绪,又重新返回看席。
期间敷衍的闲谈自不必提,到了掌灯时分,这场熬人的戏终于散场。苏絮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储元宫,免不得又是一阵沉思。
白檀瞧着她兴致索然的拨着烛台上烧的发黑的烛心儿,忍不住询问道:“娘娘回来便是怏怏不乐的,可是有什么愁心事儿?”
苏絮微微摇头,放下了手里握的银剪子。闭目,深吸了一口气,才幽幽道:“白檀,先问问皇上今晚歇在哪。若是不过来,就让人去请昭大人过来。小心一些,别惊动了旁人。”白檀道了句是,苏絮再不说旁的,合衣蜷着身子躺在了罗汉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