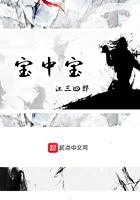陈双躺下没过多久,天已大亮。他觉得脑海沉沉地,混乱不堪。他原来心思单纯,信念坚定,想到什么便做什么,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刻苦努力,终究会到得想要的。但自从与刘一魁等人相识,尤其听到那些关系到洛彩凤的预判之后。无形中多了几分焦虑,使得他局促不安,已很难像以前那么从容。
陈双想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见到张大勺子起身做饭,就起身帮手。张大勺子伸了个懒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看上去精神很好。
陈双忽然间才觉得沉睡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羡慕不已。心道:“我要是能像大勺子这样,没有一点烦恼,吃饱了睡,睡起来吃,就很好了。”
张大勺子转身看了一眼陈双,脸上一惊。道:“陈双,怎么你的眼睛又红又肿的?你小子是昨晚没睡吗?还是被人打了?”
陈双觉得双眼有些刺痛,在眼圈四周的穴位上按了按,刺痛之感有所减轻。心道:“张大勺子并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还是不要告诉他了。”道:“没什么,大勺子,你别在意我的眼睛,我照样能帮你做饭。”
张大勺子道:“那好,就做些最简单的,你去马车上匀三斗米,淘洗干净了拿回来蒸。”
陈双道:“小事一桩。”
陈双匀了三斗米,装进一口大锅里,拿去河边淘洗。他记得昨天来的时候,西北边上有条小河。沿路行出不远,来到河边。见河水较浑,听到上游有马的鸣叫之声,转到上游一看,见有十来匹马在喝水,搅浑了河水,十来名军士在河里洗漱。马鞍已被卸下,放在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陈双见到马鞍,想起林梦梦说过的话来,格外注意。眼光向马鞍上扫去,只见每一只马鞍都鼓鼓的,敞口处发出银灰色的亮光。陈双又走近些,从敞口处看去,见那些马鞍里都装满了白银。此刻亲眼得见,证实了林梦梦说的话并无虚假。
陈双心道:“林梦梦没有骗我,起镖之前,王晖就已经将镖银分装在马鞍里了。除了王晖乘坐的马车之外,其他马车里根本没有镖银。”
陈双叹了口气。又想:“王晖是奉朝廷令旨,跟我们振兴镖局合作的,这种事情应该让我们知晓。可他却将我们蒙在鼓里,害我们一直以为十五万两镖银已不翼而飞,为此担惊受怕,这杂碎当真可恨。哎!可话说回来,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保住镖银,虽然他行为可恨,但总算尽职尽责,两两抵消,也算平衡了。”
一名军士见到陈双,叫了一声,从河里跳出来。怒喝道:“你来干什么?”
陈双道:“我来河边淘米,见下游的水不干净,就上来看看,没想到你们也在这儿。”
那军士认得陈双是振兴镖局的镖师,听他是来淘米做饭,这才没有计较。却向其他同伙招呼道:“快上来,别洗了,看好东西。”那军士看着马鞍,向其他同伙努了努嘴。
其他军士便从河里走出来,谨慎地把马鞍套上。陈双见他们搬动马鞍时,颇为费力,似乎那马鞍比平常的沉重。再次确信,马鞍里定是装了镖银。
众军士骑马走开,陈双默默地淘洗了米,拿回来给张大勺子下锅。
张大勺子炒了几道菜,吆喝着开饭。
众人从各个营帐内走出,散散地围一块大草坪上。席地而坐,待将饭菜端来草地上之后,便即开饭。
王晖高声说道:“吃饱就上路,都给我麻利点。”
众人一齐开饭,各吃各的,席间并无一人说话。陈双转头向林梦梦看去。心道:“这姑娘也当真厉害,竟然早就知道王晖将镖银藏在马鞍里了。可惜她与我们不是同路的。她虽然聪明,却将聪明劲都用到邪路上去了。”
见霍山和刘一魁就守在林梦梦的旁边。又想:“霍山和刘一魁对她着了迷,竟连吃饭也要守着她。等吃过饭,我再劝劝他们,叫他们别来打镖银的主意。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和睦相处,我还当他们是朋友。”
陈双吃了几口,又转头看去,看到卖画之人施常珍,见他也在大口大口地吃饭。记得初次遇到施藏珍时,施常珍神情儒雅,谈吐不凡。跟着镖队奔波几天后,已变得不修边幅,为了吃饱饭也不再顾及平时养成的斯文形象。
陈双又看到邻桌的黄继业和书童吴师德。此二人倒十分低调,黄继业吃得很少,便放下筷子。
陈双心道:“黄继业自称是个落魄书生,但我看他并不像书生,这年头战争频繁,就算满腹诗书,也无用武之地。他的眉宇间总透着一股郁郁不展之感。此人定然怀揣着极大的抱负,偏偏不得志。这里众人当中,只怕黄继业来头最大。”
陈双暗自将众人品评了一遍,心里寻思着,这次护送镖银与他们本无关系,待将镖银安全送到剑门后,就为他们求情,让王晖放过他们。
陈双琢磨了一阵,又转头吃饭,狼吞虎咽地扒了一碗。正要起身舀饭的时候,忽然觉得一阵头晕。想是一夜没睡后,神志不清。陈双深吸口气,想要收摄心神。但脑袋越来越沉,眼前金星乱冒,全身轻飘飘地,竟站不稳了。
陈双察觉不对劲,想要大叫提醒众人,嘴巴大大张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抬头看去,见张勋、张大勺子都已倒在地下。另外一边,王晖也已倒在地下,两百名军士横七竖八地躺着,都已一动不动。
陈双又见黄继业倒了下去,书童吴师德,卖画的施常珍,林梦梦和她的两位师兄都已倒在地下。他心中想:“这是怎么了?他们为什么全都晕倒了?莫非是中了毒吗?”想到此处,陈双心底下泛起一丝惧意。但觉得头皮越来越沉,全身发软,慢慢地倒下。两只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上,就此昏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