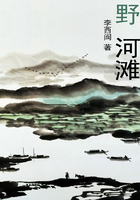1、
上海的party,沾上一次就永远脱不了干系,总能接到party的邀请信,品酒的、卖首饰的、比基尼的、爱车一族的,还有gay吧来的——一看就知道是群发的,连我的性别都不知道),倒是有一个庆酒吧开业一百天的“银来银往(取“人来人往”谐音——祈祝福的)party”,听来还有点意思,每人付一百块,随意品酒,送对对银戒指。
决定和杰瑞再混一次上海的party。
“Hi, Jerry!”刚在门口付了钱,就听到一个粘粘的声音叫杰瑞。里面party 打扮的媚惑男女已经开始蠢蠢欲动,端了杯子在音乐间影影恫恫地穿行,并不见得有谁。
一抬眼,自楼上下来个女人,修长、丰胸、极短的头发,吊带抹胸湖蓝色长礼服装,整片背露着,客气却又不乏矫情的笑。
“Hi Yanyan! How are you? This is just your bar, right?”杰瑞惊讶的语气。
是颜艳!她这样性感、诱人、自信……,我觉得有点窒息;迎着她过来,我一边堆起自然大方的笑,一边仔细看她——在上海美女见得多了,便学会了一种防御嫉妒的本事:细看了挑毛病——遗憾的是,借暗光和彩妆的便宜,毛病挑不出太多,不过她的扁脸、大嘴却是明摆的事实。
打过招呼,她一转身旋进客人中间,从头到脚散发着酒吧特有的气息。
“哎,如果当年我和她同时在公司,你会选谁?”我仿佛要向杰瑞讨什么旧债,一边取了酒和戒指。
“嗨嗨,你这个问题不成立,拒绝回答!”杰瑞眼睛四处看着,机警的样子。
突然看见了大卫——他也曾是颜艳的同事,难怪会来捧场;他的伴儿——竟然是贝!突然鄙视自己曾经对他的介意,心下涟漪泛泛,仰了头迎着他们过来。杰瑞自有他的惊讶,却是不动声色。
大卫束缚着身心,看不出心情;而贝借了暗光和彩妆的便宜,强着一张脸冲我们笑,扮嫩的样子。
贝走开的时候,杰瑞笑着问他:
“嗳,什么时候开始的?”
“嗨,就是上次你说让我去看一个摄影展,还记得吗?她,”他突然压低了声音凑过去对杰瑞说,“她非常性感。哎,果然啊,到中国来都可以找到漂亮女人,嘿嘿嘿嘿……。”一副坏笑的模样。
杰瑞也恍然大悟地笑了,全天下男人一说到女人和性,全变成了同一张下流面孔。
杰瑞还没忘摸摸我的头说:“儿童不宜。”我笑着白了他们一眼,没想到那次和杰瑞的摄影展拉皮战倒成全了两个孤独的人儿,因了我们的祸而得了他们的福,也算成人之美了。
“你什么时候去广州?”杰瑞又问。
“下个月吧。”大卫答道。
“那她怎么办?”杰瑞朝外扭了下头意指贝。
“呵,不当真的,你以为她当真吗?”大卫鼻子里轻哼一声,笑着摇摇头。说着把自己的那枚银戒指放到招待小姐的托盘里,还不忘说声“谢谢”。
杰瑞不在的空儿,颜艳尽主人之宜过来陪聊。Party上大家都讲究一种姿态,酷的那种,尤其是这种只讲英语的party,我当然也会。
“you look so pretty, Yanyan.”
“thank you, you too.”
“so, where’s Pitt?”我笑着问.
“oh, you know what?”交际地一仰夸张的笑脸,却又小了声音用中文秘密地说,“他回去和他的韩国太太”,更小了声音,‘摊牌去了。”说时对远处不知什么人挤一只眼睛,吐个性感的舌尖儿出来,不用看准是个男的。
“那你也要到美国去了,不久。”我跟她碰碰杯。
“我才不稀罕呢!”语气虚伪得轻腻,“真正的白领,那些美领馆的女孩子才不稀罕出国呢,生活在上海多么方便,周末飞到香港去购物,照样可以穿最新款的Dior”,又看我一眼,“你和杰瑞将来要做丁克了,啊?”上扬的掖揄声调,自呷一小口酒。这会儿我才看清楚,她笑的时候眼睛却是死的,不过是两颊的肌肉机械性的上提而已。
丁克?不要孩子的丁克?这个女人什么意思?
“搞错了吧,那叫朋克,杰瑞本就很朋克的不是么?他说我们要生十个孩子的。”我自卫地辩护道,心里有上升的火气。
“吓,十个孩子?听说过gay跟女人生孩子么?”她的眼睛离得我近近地,手轻轻抚着我的脸庞,“你不会不知道吧?——啊!”突然她尖叫一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见她脸上被人泼了酒,刚扭曲地回脸,又听到“bitch”一声咒骂,她又挨了一记耳光,站不稳摔倒在地,尖叫声痛苦又古怪——我惊得回头,杰瑞怒气正浓,前额的头发搭下来,眼睛里冒火。
全场皆惊,我正发愣,被杰瑞一把拉出了酒吧。
“这个女人,一次次引诱我,我拒绝了她,看她可怜,编出我是gay的谎言,不想她这样恶劣!”杰瑞拉过我的手放在他的手心里,一边招手叫出租。
这样又酷又帅的保护,让我感觉像白雪公主遇到了王子!
2、
一个月后的一天半夜,电话铃大响,挣扎着拿起来,那边先是吃吃的笑,我马上听出是橄榄,迷糊地应一句:
“干嘛大半夜的吓人!”
“哈哈哈哈,打搅了你和你的大情人了吧。不不不,是丈夫——天那,这个词儿说出来可真别嘴啊。”她还笑不停,估计又喝了些酒,后面的背景乱糟糟的,不是在热闹的街上就是在餐厅里。我眯眼看一下表,两点多,应该是她那里的晚上八点多。
“什么事快说啊?你这个臭女人。”我真的很困。
“吆——恭喜你啊,恭喜我们未来的美国公民还不行啊。”
被她说得我心下一个劲儿地笑,醒了大半。“哎,你生意怎么样啊?”
“从来就没这么顺利过,从来就没有!你可不可以想象,我忙到连理头发、修眉毛,甚至剪指甲这样的事都没有时间做啊!我算看透了,这做生意就得有后台有背景,一个人干,累死了气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呵呵呵呵,那我再去巴黎吃住你埋单啦,哈哈哈哈。对了,子秋怎么样?有她的音信吗?”我又问。
“她回巴黎有段时间了,你不知道吗?”
哦,我心下轻松地叹口气,却又生气她不够意思。
“她有信给你的”,橄榄略一沉吟道,仿佛知道我的感受,又说,“她还是很自责,常说起不该跟他丈夫离婚,唉,何必呢!真不知她怎么想的,这么好一个米歇尔给她搞得神魂颠倒的,人家都追到山东去了;回来了吧,又说要和人家分手,米歇尔都和他老婆分居了,在法国,分居就意味着离婚啊。不过还好,她最近带了一团,周游全欧洲,游客只有一个,还是个美国人!回来后她好像感觉好多了,男人就是女人的一贴药,用上就好!”
“嘿!用上就好?有的药就是毒药,用上就死。”我反应强烈。
“呵呵,现在学得行了!可以跟我辩论上个回合了。”她总是进退自如,满身是嘴,“跟你说正事儿。我让一个回上海的朋友给你捎了点儿东西——你一准喜欢——算是结婚礼物吧,也有子秋送你的。这个朋友到时候会联系你,她叫夏祺,我把她的联系方式给你邮箱里……”没说完,另一个粗粗的男声插了进来:“把妹妹你也给我邮寄过来。哈哈哈哈……”一阵放浪形骸的笑声。
“去去去,说正事儿呢,”橄榄赶了那个人,转而又对我:“别听他的,今晚使馆组织活动,是人不是人的都来了——哎,老贾”声音惊慌得变了调儿。
“喂,怎么啦?橄榄?喂?喂?” 电话那头橄榄没了声音,只听背景嘈杂,完全摸不着头绪。
突然一阵嚓嚓呲呲的声音,然后电话就断了。
3、
“咣——”地一声,那个跟在橄榄后面嬉皮笑脸的男人猝不及防地被挨了一记狠拳,应声倒地。
橄榄惊呆了,老贾何至于出手这么重!这个人不过就是开了两句玩笑嘛,平日里跟她开玩笑的人多了去了。
人群里乱了起来,那人的几个朋友慌着扶起他来;也有人把老贾推开一边的。
那人站起来,愕然地看着老贾,立马回了神儿,上前就要揪老贾,却一下被横在老贾前面的橄榄往后一推,退了几步,他突然有些明白了什么,又在众人的簇拥下退出了房间,一边口中不甘道:
“德性!赖蛤蟆想吃天鹅肉,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呸……!”
“你要我怎么做才行?!”老贾眼里的憔悴混合了无奈还有些些的恨意。甩下这句话便往门口走去。
橄榄急急追了出去。
双双坐在附近的一个餐馆,这个餐馆老贾以前带橄榄来过,非常巴黎,家常的那种格调,一切材料都是自家准备自家烧制的,包括酱蜗牛、芋泥起司,还有不断翻煸直至熟透的蜜汁土豆;成熟妩媚的女老板开心的时候,是允许某个超额消费的客人当众抚摸她挺拔的乳房的——当然是隔着衣服,所以这家看似随意风流的餐馆,价格绝对不菲。
老贾即使在心情如此糟糕的情况下,也不会带橄榄去个普通的地方。
还是热烘烘香烘烘的一屋子人,老板娘穿的紧身上衣胸前一对山峰呼之欲出。
老贾进门便叫了一大杯冰啤酒,一气儿喝下大半。
“你要我怎么做才行?!”盯着橄榄,他已经压抑自己太久了,他太喜欢这个女人了,任天天见面,却丝毫无能为力。
橄榄怎么能不知道。两个人的心从来就都没有停止过冲动,但橄榄却坚持住了,越是自己在乎的人,她越不想越过雷池。
“你的老婆呢怎么办?”拿一个指头在空中挡了他的嘴,“嘘——别告诉我你要离婚,你离了我了也不跟你。”轻声说着,头扭向了一边。
“我敢打赌没有人会比我对你更好!”老贾也伸一根指头作打赌的手势,斜了眼看着橄榄,果敢的表情。
他们是一类人,橄榄一开始就知道。但是她有一股自己也不清楚是为什么的拗劲儿,那就是绝不会跟她真正喜欢的人上床,除非他能娶她;但一想到让老贾离婚以及随之而来的俗而又俗的可能的情况,她就觉得头疼,她没有那个耐心,也没有那个兴趣,更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所以她不是不想,多少次醉意蒙蒙的时候,她多想要他,但是她都坚持过去了,她知道自己对老贾,这辈子注定将是有缘无分的。
对于老贾,上床也并非他的终级目标,但作为一个正常男人,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合为一体是他对她爱的一种渴望形式,那绝非霸占的私欲,可他似乎永远无法做到让她和自己极限靠近,老贾遇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欲爱却不能;离婚他不是没想过,没有问题,但橄榄似乎也无意和自己结婚,她到底要做什么?她到底爱还是不爱他呢?这么长时间了,难道喜欢也没有吗?不可能!不可能!老贾快要疯了!
“我承认,老板——但你应该了解我,我这个人比较自私,我,只爱自己!我不爱人,人也别爱我!我怕欠人情!”橄榄拍着胸脯,喝自己点的Evian纯水。橄榄根本不知道自己所云为何,她只想老贾死了这份心。
“可你已经欠了!我给了你工作,我给了你机会,你认识这个认识那个,你自己也开始赚大钱了,那么你是不是应该还我的人情了呢?”老贾激动万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但说完马上后悔了。
“贾老板,我明白了”,橄榄点着头轻轻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你这是讨债来了,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爱我”,语调提高,一个“爱”字说得意义非凡,老贾的眼泪都掉下来了,“那好,我还你的债,我给你想要的东西,Comfort Inn就五分种的路,如果嫌不够高档,咱们打车去铁塔下的那个希而顿,订最好的景观房间,我付帐。”说着,忽地站起来。
老贾却垂下了头,他真不知自己是怎么了,话越说越错,事情越搞越糟,摇摇头,
“我是爱你的,你什么都不欠,你欠的只有我对你的爱。”说着,老贾的眼泪一粒粒滚了下来,虽然他低着头,但橄榄看得一清二楚。
什么也没说,橄榄掉头冲出了这家餐馆,泪抹湿了一脸,她清清楚楚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爱他,我爱他……”,可让她心痛的是,为什么真爱一个人却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