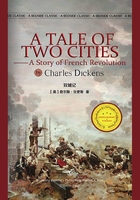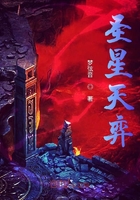1、
不愿杰瑞出差,我郁闷烦心走平路竟也扭肿了脚,不能走路;这让我想起上学时候成绩糟糕,极怕挨骂终至生病一样,均属于潜意识的强大驱动力所致;但不同的是,生了病遭爹娘可怜免予责骂;但扭了脚只能徒增伤痛,不仅于事无补,反添一份人情——一日三餐本可电话外卖,但杰瑞体贴周到,特邀大卫前来照顾,实在有些画蛇添足。
不像是帮忙,倒像是工作,大卫像个忠诚的卫士,看护着被围困在城堡里的瘸腿的公主。他每天早晨报个到,晚上下班又过来值班,还要照顾一日三餐。几次想婉言谢绝,却怎耐他来得那么自愿,做得那么自然,倒让我觉得跟他客套都是多余。因为每次去开门很不方便,我就干脆把杰瑞留下的那张门卡给他使用。
其实他在中国也寂寞,除了看美国卫视就是盗版碟片,现在变成拿来我们一起看,也正好可以提高我的英文。说实话,跟杰瑞在一起,英语不太会有提高,因为他的中文越说越地道,兴趣倍增,更没有说英语的机会;但和大卫,讲英语是必须,于是学会了很多生活语言,比如美国人怎么说饿了,怎么说打扫房间,怎么说交朋友等等,都完全不是用我们学过的那些生词硬句,和他熟了之后,更是学会了怎么说大便小便甚至打嗝放屁,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是没有哪本教科书会教给的。
一天,他把专门从美国带来的吉他拿过来,向我小露了一把。他边弹边唱,是那首《老橡树》,我初恋时候最喜欢听的一首美国老歌。看他深邃的眼睛和专著的神情,我的心突然觉得酸酸的,那一刻我恍惚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个人,又让我想起了自己那段刻骨铭心生死相许的的纯纯岁月。他唱完了,冲我一笑,我也回他一笑,本想为他鼓掌喝彩,抬起的手却抹去了腮边的一滴泪。
那晚的我很不平静,脑子里充满了要写的东西。我写到很晚很晚,忘记了时间,也根本不知道是怎么歪靠着沙发就睡着了,恍惚中,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却使劲睁不开眼睛,只觉得额头被人轻轻吻了一下,接着是嘴唇,温热的,还有一股薄荷的清新气息。我使劲张了眼睛,看到了那双熟悉的深邃的眼睛,在深情地望着我。我没有力气晃了晃头,只说了句“no”就又昏睡过去了。
再当我从沉睡中醒来的时候,发现天已经大晴,阳光照满整个房间。朦胧中一个意识被唤醒,大卫真的来过吗?还是只是梦幻?转头看见桌上的羊角面包和罐装果汁,我知道是他早上真的来过了,他吻了我?我好像,好像还说了“no”?这算什么?这又怎么可能?为什么我的心会有种抽紧了的轻快感觉?这不可以!我有杰瑞,我甚至不能在感觉上对他有丝毫的不忠。呵——多少天都没有想杰瑞了。现在是不是扯平了呢?他有KTV不清不楚的一幕,我心下对另一个人有了些好感。现在有些想到他了,我跟大卫是不可能的。
有太阳陪着,这天就过得很快。快六点半的时候,公寓前台有电话上来,问有没有叫了外卖?我愣了下说没有。送外卖的在电话那头大叫说是个老外让叫的,那个人叫“大围”,我一想,“大围”应该就是“大卫”吧。于是让人上来,付了钱。那个晚上,大卫没有来,也没有电话。我写不下东西,独自看了一晚上电视,我落落寡欢些什么呢?
2、
下周一清早,大卫又来了。
他手里抱着个早餐纸袋,看见我,打个敬礼,爽朗一笑,露一口白牙,问候道:
“周末可好?”
“好啊,谢谢。”我尽量平静地笑着说。
“来,吃点东西吧;我要赶去上班了,”
我点点头,说:“以后如果早上来不及就不要给我送了.”
他顿一下,又笑了,说:“难道你要解雇我吗?”
我笑了笑,摇头说:“不会呀。我要解雇了你就找不到比你更好的了。”说完又后悔,其实自己不想给他,也不想给自己造成什么误会。
“那就好。等我晚上来看你。”他又定定地看我一眼,走了。
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他每天都给我带吃的,该去针灸的时候就扶了我出门叫车陪我等等,我们也还会在一起看碟片,只是他不再给我弹吉他唱歌,也把门卡客气地还了给我说他怕给我弄丢了,其实丢了还可以再配,他的借口太明显。
爱恋这个东西就像炮竹,埋在地下不去碰就永远是安全的,但是,一旦点燃了那个芯,就会迅速燃烧爆炸。对于这一点,我和大卫都不是稚嫩少年,都十分清楚。
转眼又到了周五,我的脚肿消了不少,不过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要彻底复原还需熬过这许多天才行。就像我对杰瑞的感情,就很难回复到当初的依恋和信任了,所以每次当他提及结婚,我心里都不明朗,像隔着一层半透明的纸,似看得见又似看不见,觉得自己把握不住。杰瑞好像从周三开始都没有给我电话了,他在干什么呢?
叮——咚——有人按门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