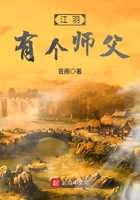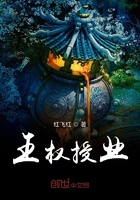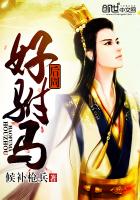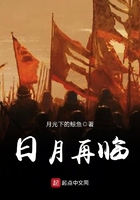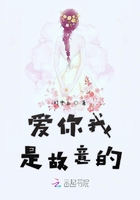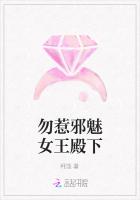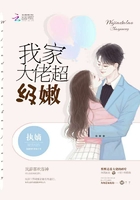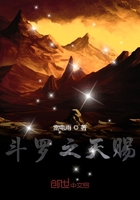大方脉分会的学术交流会继续进行。
接下来发言的是朱肱,他曾于十年前考中进士,自号“无求子”。
朱肱:“各位先生,晚辈十年前便立志要使仲景幽深之学说大白于天下。那时我还年轻,未能全然理解伤寒之理,便想到天下学医之人也必然会有与我类似的感受,故晚辈在这十年间综合分析仲景之书,以通俗之文字、问答之形式,来阐述伤寒证治的异同,使人明白易懂,如此,仲景之学便可流行于天下。”
王叔和赞曰:“此举甚好,不知书名为何?”
朱肱:“既然是问答,那就叫《无求子伤寒百问》吧。”
此书后来更名为《类证活人书》,又名《南阳活人书》,流传甚广,以至于后世之人一提到伤寒,便只知道《南阳活人书》,却不知道仲景之书,可见其影响范围之大。
甘遂:“敢问朱先生近年来对仲景之学可有创见?”
朱肱:“我不敢说这是什么创见,我只是前人既得成果的搬运工罢了。”
甘遂:“不知先生是怎样搬运的?”
朱肱:“甘大人,仲景之术虽妙,可《伤寒论》一书还是存在一个缺陷,那便是:‘症多而药少’!”
对此我深有同感,《伤寒论》里面的很多条文只有症状而没有给出对应的治疗方法。
甘遂:“先生说的是,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朱肱:“自仲景立论以来,世间已经过了八百年,在这八百年之中,无数医家创制了很多好方子,我要做的便是采集此间诸方,诸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以补充仲景之书。”
甘遂:“先生好魄力!知其所长,明其不足,师古而不泥古!甘遂佩服!”
朱肱:“甘大人过奖。”
朱肱这么做无疑是在与整个学界为敌,毕竟当时的人崇尚“注不破经”,皆视《伤寒论》为绝对权威,不敢做一丝一毫的增减。
朱肱接着说:“若要说《伤寒论》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地方,那必然是‘六经’。”
所谓六经,是指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
甘遂:“那先生以为,仲景所说的‘六经’当为何物?”
朱肱:“依在下愚见,此六经即为‘足之六经’!”
一时语惊四座。
所谓足之六经,是指以足命名的六条经络:足太阳膀胱经、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
将伤寒六经与足之六经联系起来,这是朱肱的首创。
现如今朱肱这一论断已被学界所接受,但在当时,这无疑是朱肱投向医学界这片平静湖面的一块巨石。
王叔和问道:“先生此言可有证据?”
朱肱答道:“证据不难找到:发热、恶寒、头痛、项强、腰背痛,这些症状之所以一起构成太阳表证,就是因为这些症状都发生在足太阳膀胱经的循行部位。”
王叔和:“若是依先生之见,只能将病位定在某一经络,而经络循行范围甚广,那看病岂不是略显粗糙了?”
朱肱:“王大人此言差矣,看病自然不能到此为止,这只是个开始。”
甘遂:“那接下来又应当做些什么?”
朱肱:“治伤寒,须辨表里。”
甘遂:“表里如何辨别?”
朱肱:“脉证合参!脉有表里阴阳。”
甘遂:“何脉为表?”
朱肱:“浮、芤、滑、实、弦、紧、洪,此为‘七表阳脉’也。”
甘遂:“何脉为里?”
朱肱:“迟、缓、微、涩、沉、伏、濡、弱,此为‘八里阴脉’也。”
朱肱对脉象的这一分类方法也成为了后世论脉分纲领的先驱。
“哈哈哈,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下今日遇到二位先生真是三生有幸!在下知道自己回去该做什么了。”说话的不是旁人,正是自开会以来未曾说过一句话的成无己。
甘遂笑道:“哈哈,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想必甘大人也发现了,那我便在此明言:成某方才听到朱先生用《灵枢·经脉》之言来解释六经,顿觉豁然开朗,又想到仲景曾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提到过,他也曾撰用《素问》《灵枢》,可见用《内经》来注解《伤寒》,这条路必会充满无限的光明!”
我知道,成无己言出必行,从那之后,他把余生的四十多年都投入到这项宏伟的事业中去,坚持不懈,老而弥坚!
自从有了它的注解,《伤寒论》得以广泛地被天下学医之人理解和重视,自那以后,伤寒学派迅速发展,针对《伤寒论》的学术研究蔚然成风。
这都是后话,先来看看成无己在此次研讨会上有何高见吧。
成无己转身面向庞安时、朱肱,说:“方才我已经注意到二位先生对于症状的鉴别尤为重视,而《伤寒论》一书,条文纷繁复杂,症状多如乱麻,实在不利于应用。”
朱肱:“成先生可有解决办法?”
成无己:“大要不过三条:定体、析证、明理。”
朱肱:“请先生明言。”
成无己:“假若有一伤寒发热之患者来看病。我们需要知道发热者,发于皮肤之间,散而成热,这便是‘定体’。”
朱肱:“何谓析证?”
成无己:“发热一症,有潮热、有寒热,二者皆与伤寒发热类似,但又存在着差异:潮热是有时发热有时不发热,寒热是恶寒与发热交替出现。分析各自的特点,这便是‘析证’。”
朱肱:“何谓明理?”
成无己:“发热有表里轻重之不同,属于表证的是因为风寒束缚阳气,属于里证的是因为阳气入于阴中。其病机各异,医者须了然于心,这便是‘明理’。”
甘遂:“如此一来,《伤寒》之理便越发明了了!”
成无己:“在下想将《伤寒论》中50种症候的病状和病机都如方才这般细细辨析,汇总为《伤寒明理论》一书,希望能让更多的同道找到学习《伤寒》的门径。”
没错,他做到了。
“妙啊!妙啊!”是从屏风后面传来的声音。
什么?这屋里竟然还有人?!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从屏风后面走出来。
甘遂道:“小许,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回大人,今天轮到我来分会值日,有点累了所以就在屏风后面靠着墙睡了会儿。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大人们已经在开会了,我寻思也不方便打扰,就在里面待着不敢动。”
“哎,你啊!”甘遂转向其他人,说:“诸位莫见怪,这小子是太医局的学生。”
“晚生许叔微,见过诸位前辈,方才听了前辈们的高论,晚生受益匪浅。我也感受得到,前辈们为了能让我们这些初学者更好地理解仲景的医道,可谓是煞费苦心。晚生谢过各位前辈!”
众人皆笑。
“不过,”许叔微话锋一转,“作为学生,晚生自认为还是更了解学生最需要的是什么。”
甘遂:“哦?那你说说看。”
“回甘大人,当今学生学习《伤寒》最大的困难乃是背诵!学医之路千万条,背书永远第一条。背不下来,一切免谈。”
“你小子说的有几分道理嘛,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谢大人夸奖。晚生想到的办法便是将《伤寒论》编为歌诀,这样一来,朗朗上口,合辙押韵,背诵起来就容易多了!”
甘遂:“是个好办法,你准备怎么编这个歌诀?”
“回大人,刚才成先生的话启发了我,我准备按病症来分类编写,就叫《伤寒百证歌》吧!”
“好,书成之后交由本官批阅,若是编的好,就在全国刊行。”
“谢大人!我这就去写!”
后来许叔微系统归纳《伤寒论》中载述之证候,将证候总论及分证内容共编列为100种。包括伤寒脉证总论歌、伤寒病证总论歌、表证歌、里证歌、表里寒热歌、表里虚实歌等及《伤寒论》中所见之多种证候,均以七言歌诀予以阐述分析。不仅介绍伤寒诸证,还兼述治疗方剂,是后人学习《伤寒论》的重要参考书。
本次大方脉分会的学术交流会就到此为止了,反正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那不如就在这里好好学习吧,正好有一大堆《伤寒论》的参考书就要编出来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面还有我们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