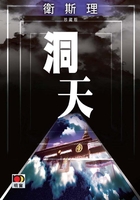世界上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偶尔有一天,出现了人生轨迹的交际,更多的人的交际只是一个点,或是几个点。只有极少数人的交际,是一条线。更少更少的人,他们的前半生没有任何交际,后半生的轨迹却是完成重合的。这需要怎么样的聚变?这需要怎么样的一种力量?
1-1.
十五年后,春暖花开。
边境地区,多条大江交汇地带,位于省东部城市,锦绣。
江开水暖,渔船复航,江面依旧江水滚滚,两岸冰雪融干退尽,裸露出黑土丘壑。江边细沙松软,被往来行人与摩托压出一道道不规矩的印子。
江边铁皮渔船一艘一艘,紧紧地挨着,沿着江堤排开。船身都很旧,水面以下刷着暗红色的油子,船身刷灰黑色油子,船舷上简单写上几个数字,歪七扭八的,算是船号。船上偶然有几个人渔民,或翻弄着网子,或坐在船梆上歇息,抽着烟,看别人各自忙碌着。
船上的妇女脚上穿着黑胶皮靴子,上身穿天蓝色棉袄,头上系着粉色头巾,自头顶半包裹着脑袋,在下颚系上。色彩鲜艳跳跃,虽然刺眼,但朴实中透着时髦的心思。像是累了,在船头上坐着,呆滞地看着江中心亦或是对岸。她身旁穿迷彩服的男人在猫着腰干活。
江边有几辆摩托车停放着,车的后座两边都挂着大筐。湿拉拉油黑油黑的,还搭拉着枯草。这挂着鱼筐的摩托,离得老远就能闻到它散发出来的鱼腥味儿。
摩托是市场里的鱼贩子们骑的,前来买新打上来的鱼回去卖。贩子顾不得脚底下涌上来的江水,都穿着及膝盖的胶皮靴尽量靠近铁船。看样子是来得晚了,走了好几份都是卖光了的,有几条船还有几条稍大点的鲫鱼,看样子是不怎么好的,又没有几条。那人走了几份,好歹买了半筐小鱼回去。
小鱼尽是些柳根子和川丁子,不死心,就又回去把刚才看的那几条剩下的鲫鱼兜罗回去。船上的渔民们倒是乐观,笑着收拾渔具打算回家吃饭。
收获有多有少,卖光了最好,卖不了带回家自己吃也行,打鱼的人总是乐观的样子。不像鱼贩子那般计较,更不去算计秤杆子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
随着夜幕降临,江边恢复了沉寂,晚上就起风了,江水里浪花的响声很大,江边开始显得萧条起来。
城里的大市场也快收摊了,卖鱼的,卖菜的,卖农副品的,还有外贸商品一应俱全。商贩们都忙着收拾摊子,结束一天的经营。
街面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几辆摩托车经过,但还是冷清。
开春以后,摩托车就全都出来了。冬天是不行的,下起雪来路面滑不说,冷是最主要的,刮着大烟儿炮就连走着都费劲,哪还能骑个摩托。
好在开春儿了,一起好像都活过来了。
1-2.
因为离边界近,只有一江之隔,所以这样的边境地区的贸易自然是红火的,和外国人做买卖或者是物品交换,好像都挺兴盛。
在大市场外面不远的一条街面上,有一个福顺渔馆,到晚上才开始人多。临着街道的一个红砖的平房,挨着街的拐角,门面不大不小,能有一百多平方。
福顺鱼馆开业几年了,算是市里的老馆子。鱼炖得好,价钱又不贵,请客吃饭适合来这里,大鱼小鱼都有,炖菜也可以。前几年生意不好,这两年变好多了,经商的,跑运输的,都到馆子吃饭。于是这里成了鱼龙混杂之地,各路消息汇集之地。
出了大市场往南走,就能看见一个破旧的牌子,写着福顺渔馆四个字,门口高杆上挂着一个钨丝灯泡,照亮门口以及一部分街道。
鱼馆里烧了自制锅炉,墙壁上安了几组暖气片,所以店里十分暖和。
四个二百瓦的钨丝灯泡,把屋内照得铮亮。时间还早,也有个两三桌吃饭的,很安静,客人很少说话,都低着头专心吃饭,或是偶尔抬眼看几眼电视。电视摆在吧台酒柜上面的架子上,重播着周润发版的《上海滩》,可惜画质不好,电视尺寸还小,就像看旧版连环画本,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多是没客的时候店员解闷用的。
魏连山虽是个老板,倒也没个老板架子,跟着厨师在后面收拾鱼,从门帘缝看了一眼前屋,见没有新的客人来,那一个服务员倒也能忙活得过来。人要是再多就不行了,到时候还得找个人才行。小山心想。
大雷还不到十七岁,从乡下出来打工也有段时间了。他爸爸就是个厨子,他本是出来学家电修理的,因为粗手大脚的,总也学不好。还是在饭馆上班好些,活干得粗糙但是却有力气,也不用费脑子,一心一意地给魏连山卖力,也得到他不少关照。
大雷的脑子有一点弱智,所以肯用他的老板不多。魏连山不嫌弃他傻,傻点好,没有心眼,只知道一心一意地干活,只知道谁对他好,他便向着谁。外人是看不出来大雷傻的,顶多会觉得他毛手毛脚、愣头愣脑的,但要是接触得久了,处得长了,是会发现他不太对劲的。愚钝之中,伴有轻微多动症。
大雷正看着电视机入神,门外进来两个人。
这俩人一进屋便大声地说话,嗓门老高,四下寻摸了一遍,才坐下,搬动凳子的声音非常大。
小山以为前屋有人打架了,赶紧又看了看,见没事,又继续杀鱼。这俩人看样子像是社会上的混混。
大雷哪能想到那么多,见来人粗手粗脚,毫无礼术,赶紧起身,拿着菜单过去招呼。
大雷:“哥,吃点什么?”
“这儿不是鱼馆儿么?!”穿军大衣的瘦子反问。
“对呀。”
“那你他妈还问?!上这儿不就是来吃鱼的么?!”瘦子点了根烟,翘起二郎腿。
“吃鱼是吧,那……哥,你想吃什么鱼?”
“开江鱼。”另一个男人抢着说道。他皮肤黝黑,灰色的破旧棉袄上沾了好几块白灰,都干了许久,像是个刮大白的。
大雷陪着笑脸回道:“不好意思,哥,咱家没有开江鱼。”
军大衣瘦子立刻不耐烦起来,扯着嗓子嚷起来:“这不是鱼馆儿么?怎么他妈就没有开江鱼?”
大雷赶紧给人家解释:“哥,你来晚了,江都开了快一个多月了,吃开江鱼你得赶上开江的那几天来。”
刮大白的起身就要走:“那还吃啥了,走吧!”
小山心想这俩人来者不善,走了也好,这样的人也是不好伺候的,真要是在这儿喝多了,不定发生什么口角呢。
军大衣瘦子起身刚要走,看见边上桌子的俩人吃得香,忙问:“他们吃的啥?”
大雷见客人问起,赶紧回答:“炖鲢鱼。”
军大衣又坐了回来:“就给我来那个!”
刮大白的也回来坐下,问大雷:“还有什么好吃的特色菜没?”
大雷见客人没走,心里暗喜,熟练地介绍起菜色:“咱家鱼馆儿以鱼为主,江里的‘三花五罗十八子’基本上都有,大鱼有马哈鱼;中不溜的有鲤拐子,鲫瓜子,草根棒子,鲢鱼;小鱼炸着吃也特别香,川丁子,柳根子。”
“有啥特色菜没有?”军大衣也问。
大雷听客人口气,像是打算大吃的,便得意地介绍道:“黏鱼炖茄子、鲤鱼炖白菜、鲫鱼炖豆腐、鳇鱼炖土豆,这都是咱们店的特色菜。名贵菜也有:清蒸白鱼、煎焖马哈、浇汁重唇、红烧鲟鱼。”
刮大白的一听菜都不像便宜的样子,赶紧问道:“全他妈是鱼呀?有别的吗?”
大雷不耐烦地回道:“现在刚开春儿,青菜少,只有土豆,白菜,酸菜,豆腐,粉条,鸡蛋也有,还有炸花生米。”
费了半天劲,二人总算点好了酒菜,开始大吃大喝起来。小山不敢掉以轻心,躲在后厨暗地里观察着这俩人。
大雷边看电视边招呼着客人,听这二人说话的口气,定是社会上的混混,谈的都是打架斗殴的事情。而且越是喝酒,就越开始口若悬河,大肆吹嘘起来,听得大雷这孩子满脑子眩晕,摸不着边际。
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唾沫横飞,烟雾缭绕。
大雷心里开始偷着骂这俩人,恨不得他俩吃完了赶紧滚蛋才好呢。
可越是这么想,反而越是喝个没完。喝了一个多小时,俩人愣是把一瓶北大荒白酒给喝完了。就又叫大雷拿一瓶来。
大雷看了一眼这二人,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可是又不敢劝说,转眼朝魏连山看了一眼,小山朝他点了点头,于是大雷又给他们拿了一瓶。二人这个酒量,看得大雷心里瘆直慌。
也见过很能喝酒的,高度的白酒能喝个半斤就算厉害的了。听说过有特别能喝的,一次能喝个七八两酒,还有能喝一斤的,但只是听别人说说而已,大雷可没亲眼见过。
眼看着第二瓶白酒也快没了一半了,大雷开始感觉到事情不妙了。
刮大白的早就喝得嘴都瓢了,也说不上话,就听军大衣一个人口若悬河。大雷听不清他说的什么,磕磕巴巴的,还手舞足蹈,几度把酒瓶子扒拉倒了,稀里哗啦地发出声响,甚是没有酒品。刮大白的假装镇定地给军大衣点烟,手哆嗦着,划断了好几根火柴才给点好。
这一顿想是那军大衣付账,大雷心想。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这俩人都已经喝走好几桌客人了,终于像是要走了。果然,又等了片刻,刮大白的扶起军大衣,二人往门外走去。
大雷赶紧追上前去:“哥,还没付账呢!”
军大衣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弄得有点清醒过来:“多少钱?”
“四百。”
“……抹零之后四百。”大雷赶紧又补充道。
“什么破玩意这么贵?”
“哥,真是四百,都算好几遍了。”大雷陪着笑脸解释道。
军大衣脸拉得老长,一摸兜里,好像钱不够,视乎丢了面子,瞪着眼珠子骂大雷:“小兔崽子,哥们出门吃饭从来不带钱,知道吗?我是大刚旅社的,想要钱自己过来拿!”
说完,俩人直接走了出去。大雷想上去阻拦,哪是对手,被一把推了回来。
大刚旅社,魏连山听到这个名字时心里震了一下。
听说是一个叫大刚的人开的,那人他不认识。听闻尽是些流氓混混在那里聚集,耍钱喝酒斗殴什么的。
他见大雷被推搡了一把,实在是坐不住了,霍地起身,大步追了出去。
流氓是不想去招惹的,可要是真有谁先招惹了魏连山,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魏连山原也是个暴躁脾气,两句话不入耳,马上就要动手。这都快要二十五了,性格自然稳当了很多,可是在这边境城市里面开馆子,什么黑道白道的都难免打交道,没有点魄力也混不到今天。
人还没走远,魏连山追了上去。
“二位二位,付了帐再走,好吗?”
刮大白的狗仗人势地对魏连山说:“不是告诉你了么,记大刚旅社的帐!”
小山伸出手做出拦截状:“不好意思,本店概不赊账。”语气铿锵有力,语速快而清晰。
军大衣见有人阻拦,一把拨开小山的胳膊:“你他妈谁呀?”
刮大白的见小山的脸色有点急了,拉着军大衣就要走。魏连山指着他们恶狠狠地说道:“你们到底付不付账?”
军大衣开始耍无赖:“就他妈不给你!能怎么着?!”
说着,他上去想和小山纠缠,刮大白的见他二人都喝醉了,又赖人家的帐,心里有点发虚,拉着军大衣赶紧走掉。魏连山哪肯任他们耍赖,一直跟着要酒钱。
“行啊,有胆量你就跟来拿吧!”刮大白的心里盘算,等回了旅社,人多了自然不怕跟这小子动手。
两个醉汉在前面走,魏连山也一路紧跟了过去。
1-3.
大雷见他老板出去追流氓,心里开始慌了,一个人在饭馆里面坐立难安,不知道如何是好。要是时间久了还没有回来,就得找人出去接应,去派出所找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么晚了人家肯定是下班了。大雷就这么胡乱寻思着。
正慌着,有人进来了。大雷一看来人是姜忠毅,像是看到救星,赶紧迎了上去。
姜忠毅一进屋不见魏连山,便问大雷:“你哥呢?”
大雷红着眼圈跟忠毅说:“刚才来了俩流氓,吃完饭赖账不给,还推搡我,我哥追他们要钱去了。”
忠毅见大雷像是受了委屈,感觉事情严重,赶紧问大雷:“上哪追去了?”
“大刚旅社,那俩流氓可横了!”
忠毅没再细问,赶紧追了出去。
大刚旅社忠毅是知道的,在社会上也是臭名昭著了,那帮人打架斗殴无恶不作,小山一个人去肯定是要受欺负的。想到这儿,忠毅急忙出门上了吉普车,直奔旅社方向驶去。
一路上,忠毅都在担心小山。刚才他进屋之前见着小山的长江摩托还在门口停着,以为他在店里呢。小山有一股傻子似的执着劲,被欺负他很少忍,跟人家打架是极容易发生的事,人少还好,对方要是厉害茬子,难免这回是要吃亏了。忠毅想,一会儿实在不行的话,车后头还有一根铁撬棍,想起那根铁撬棍,忠毅心里像是立刻有了寄托,狠狠地踩着油门,吉普车在夜幕中狂奔着。
魏连山跟着两个混混来到了旅社,没想到又来了两个混混,原先的那两个喝多了,并不可怕,可新来的这俩像是清醒的。而且他们的态度更是蛮横,明知道是到了人家的地盘了,语气肯定是要硬起来的。看样子要钱是没戏了,可又不能不要,就硬着头皮跟人家要。吃饭给钱,还想赖账?
这两位更是无理得很,人家管你钱不钱的,又没去吃你的、喝你的,追着到人家店里来了,本身就是流氓痞子,正愁事儿少闲得发慌呢。没说几句,上来就给了小山一拳头,连拉带拽地把魏连山弄出了旅店外。
军大衣和刮大白的也跟了出来,四个人打他一个,魏连山连着挨了好几十拳,场面混乱,不知道打哪个好,只好先死命地护着脸。肯定是打不过人家了,好歹也是四个大老爷们呢,可不能就这么跑了,总得抓住一个还两拳,要不自己挨这顿揍实在是太亏了。
魏连山猛地发力,一个踉跄差一点摔倒,紧接着脖子被锁住了,屁股又被踢了一脚,这一下是真的站不住了,摔倒在地上。
倒下以后是最吃亏的,全然没有反抗的能力,接连又被踹了好几脚,对方都是穿的大皮鞋,踹得他鼻口淌血,肚子抽蓄着疼得要命。肚子和脑袋只能是护着一头了,腿好像是断了,早都木掉没有知觉了。
怎么着也得等到机会抓着一个。魏连山的脑袋好像也被打糊涂了。
姜忠毅离得老远就看见了旅社门口的打斗,他开着吉普车一直朝着人堆里冲撞上去。刮大白的躲得快,差一点就撞个正着,这一下可把他吓得魂都没了,几乎就要栽到壕沟里去,坐在地上半天愣是没起来。
姜忠毅下了车,也顾不上拿那根铁撬棍了,抓住了一个混混的头发就拿拳头一个劲儿地打。
众人一看来帮手了,全都顾不得魏连山了,朝着姜忠毅着呼过来。
魏连山一看姜忠毅来了,立刻又有了体力,拼着狠劲儿站了起来,抓着一个流氓朝他脸上连续打了好几拳。那人踉跄了两步,小山也不顾别人,就盯死这个打。把人家使腿拌儿放倒在地上,又骑上去打。
流氓们本来是占了上风的,没想到突然又来了帮忙的,不下狠手是不行了。其中一个流氓跑到了壕沟边,看见刮大白的在那瘫坐着,鞋也吓得甩丢了一只,看来是顶不上去了。他便捡了一块大石头,本想打姜忠毅,一看魏连山骑着自己兄弟打,所以也没去想手下轻重,照着脑袋就是一石头。
魏连山被这一砸顺着脑袋往下淌血,顿时急了,也不去擦血,死盯着刚才砸自己脑袋的不放。那人见一石头没把对手打趴下,反而激起了人家的愤怒,腿开始软了。姜忠毅一看魏连山的脑袋被开了瓢,也急了,这俩人全都开始下了狠手。
1-4.
围观的一看是大刚的弟兄跟人家打架,也都离得远远地看着,谁都不敢上来劝架。可现在是四个人打人家两个,大家觉得不公,暗暗地为被打的捏了一把冷汗。这血淋淋的场面并不多见,见一次让人揪心一次。
早就有人去告诉文刚了,等他跑回来一看,这边早打得热火朝天。他细看那两个被打的,伤得好像是不轻,再这么打下去,是要在自己的家门口闹出人命来的。他再一看院子前面停着的吉普车,虽然不知道来路,但是猜想那人肯定也是有些门路,这么一想,赶紧又叫了一个人,把打架的都给拉开了。
魏连山见这人能有一米八五的大个头儿,身体强壮,大长方脸,目露凶气。猜想这人应该就是社会上传言的混混大刚。
大刚对魏连山说:“别在我这块儿闹事,赶紧回家去吧!”
魏连山本来就脑袋被砸得疼,一听他放出这话,马上又急了:“吃饭不给钱,还打人,还有没有王法?!”说着又要上去打。可是刚要使蛮力,却发现早就没有力气了,浑身上下哪都哆嗦。幸好忠毅扶了他一把,再一看忠毅,他脸上也挂了彩,眼窝好像被打青了。无奈之下指着文刚骂道:“臭盲流,你给我等着!”
“等着就等着!”文刚一看自己的兄弟也有伤,但是跟对方比起来算是占了便宜,又不知道对方来路,为什么找上自家的门来打架,就想着先这么消停下来再说。
忠毅赶紧把魏连山拉上吉普车,叮嘱他捂住脑袋的伤口,带他找大夫去了。小山还在赌气,摸了一把伤口,见血都干了,也就懒得捂了。
这个时间,诊所早都关门了。好在忠毅认识一个当大夫的朋友,知道人家家里住哪,就拉着魏连山找去了。
“那大刚是社会混混,咱以后得小心点。”忠毅的年纪比小山大,社会见识广,做事稳当。魏连山跟他比起来更像是个弟弟。
文刚等魏连山和姜忠毅走远了,把大伙叫进了屋里,问是怎么一回事。军大衣告诉他说在人家馆子吃了饭,有四百块钱的酒钱,叫记账,人家不肯给面子,还一直纠缠,就打起来了。
文刚一想这魏连山也算是附近做生意的,本该给些面子,加上又是自己人理亏,以后他要是非得要这酒钱,就还给人家。但决不能明着服软,他们兄弟在这一片,不会被任何人欺负,从来都是他们欺负别人。
高大夫住在一楼,早都睡下了,听见有人敲玻璃,赶紧起来看。他用手电筒一照,见姜忠毅带着一个伤者,这才开了门,把二人请了进来。高大夫跟姜忠毅也并不熟悉,但是认识他父亲,两家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来往,就是遇上了打个招呼。去年在乡下出诊,正要回城里,姜忠毅看见了,认出了高大夫,倒也没不理会,用他单位的小吉普车捎带着他回来了。就那一次算是正式熟识了,忠毅也才知道这高大夫家的住址。
家里没有什么药物,就简单地给魏连山的伤口消了消毒,拿块纱布给粘上了。
姜忠毅本还担心得缝针,仔细一看,见魏连山脑袋上的伤口并不大,只是破了一个口子,伤口周围有些肿起来了。
高大夫给魏连山拿了一块湿毛巾,让他把脸上的血擦擦。魏连山跟人家也不熟,又是半夜里把人家给叫起来,心里感觉过意不去。所以赶紧说是不用擦,可是高大夫实在热情,连说了好几次没事没事,执意让他擦血,他就只好接了毛巾擦了。擦完了又在洗脸盆里给人家洗了洗。
给魏连山包扎完,高大夫又给姜忠毅看伤。
姜忠毅并没有什么外伤,就是眼窝有点青,鼻孔里有些血迹。高大夫拿了一根棉花棒把忠毅鼻子里的污血清一清,又拿了一根新的,蘸了药膏,在鼻孔里抹了几圈。
临了,高大夫也没多问,这一看就是打架来的。
忠毅要给药钱,高大夫执意不收,忠毅也为难起来,又不知道该给多少。临走只好又谢了人家一回,心里想着上次拉了他一次,这回就当他还自己人情了。
1-5.
文刚可不是什么善类。这人算是这一带的一霸,从小到大,打过无数架,也是个动不动就拿刀子的主儿。
文刚他爸是粮库的保管员,脾气非常暴躁,可没想到生个儿子更霸道,从小就不上学,十来岁就敢打老子,没到二十就拿刀把人给捅了。好在没有捅死,跑到乡下躲了好几年,他爸陪了人家好几万块钱,要不然他家也不至于受穷。
躲了几年看没事了,文刚就又回城了。原以为能干点正经事情,没成想还是个败类,一点都没改进。后来在农贸市场做买卖,又是因为打架,干不下去了,开始跟着一班闲散人员到处偷盗,专门去乡下偷粮食偷牛偷农资,偷完了再回城里卖掉。又不肯走远了偷,都是在附近的乡镇里行动,也被抓了几次,抓住了就和人家打,所以远近乡镇全都知道他是个大祸害。
后来家里人也不管了,全当没有这个人。他又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些钱,开了个旅社,没看见赚到什么钱,他又想开个KTV。
文刚认识七个混混兄弟,加上自己一共是八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这就是出了名的锦绣八条龙。
旅社本来就不赚钱,文刚又好赌博、好吃喝,赚的钱连房租都不够交的。后来人家房东来要,他就赖着不给房钱,房东看他太硬气,也不敢撵走他,实在拿他没办法。
1-6.
从高大夫家回到鱼馆,已经快十一点了。
临走高大夫给包了几片止疼药,魏连山也没心思吃。问姜忠毅怎么这么晚还来,忠毅说他白天跟经理下乡,晚上才回来,本就晚了,又没吃饭,想着来找小山蹭口酒喝,再回家睡觉。结果没成想,酒没蹭着,蹭着一顿打。
魏连山这人平时不怎么喝酒,只是抽烟,其实他很能喝,就是没大隐。有人让他应酬,他也喝,但都不醉。不像姜忠毅,自来酒量就不好,还馋酒。
十个司机九个骚,还有一个大酒包。那一个酒包就是姜忠毅,这话是魏连山说的。
魏连山原先也当司机,跟着姜忠毅在一个车队上班。后来没干两年就干不了了,他总得回家照看他妈,所以不能老在外面一跑就是好几天。后来姜忠毅也不干了,下来给经理开小轿车。开大车跑运输太累,没几个吃得了那苦。
魏连山弄了个炸花生,小葱拌豆腐,还有一盘油炸小鱼,陪着姜忠毅喝酒。
厨子已经回去了,大雷负责在店里睡觉看店。他见俩人回来脸上都挂了彩,也不敢多问。
魏连山感觉脑袋有点迷糊,也不知道是被砸的那一石头,还是酒劲儿上来了。等他陪着姜忠毅吃完,又给他送走,已经快要半夜了。
1-7.
第二天一大早,姜忠毅还在睡觉,他妈就把他给叫起来吃饭了。
隔了一夜,眼窝还是有些青,姜母问起,他就开始打岔。
姜母就象是心里开了窍一样,凡事跟明镜一样,儿子不愿意多说,她也就没有多问。
吃饭的时候她问她儿子:“你最近见着小山了吗?他那馆子咋样?”
忠毅不敢把打架的事告诉她,只是说:“还行,就是员工少,客多的时候好像忙不过来。”
姜母说:“咋不多请人呢?小山他妈那病又不能没人照看着,说不上啥时候犯病,他又得看着他妈,又得维护着馆子,可够他劳累的。”
“可不是么。”姜忠毅吃完饭就出了门,姜母问他下了班回不回来吃饭,儿子回答说没事就会早些回来。
收拾完桌子,姜母就去了东边的邻居家,说好了是打扑克牌的。她不爱打麻将,觉得摆弄起来太费力气,糊的还慢。姜母体态肥胖,心胸豁达,是个急性子。平时就爱打扑克,也没有别的嗜好,唯一心里面挂着的就是她儿子忠毅。忠毅比小山还大一岁呢,可到现在还没结婚。人家小山虽然是离了,但也算是结过婚的,哪有她儿子这么大还没结婚的?
她总出去打牌,一出去就有熟识的人问她,她还得费力气跟人家解释一遍,说并不是她们家儿子有啥毛病,是叫前一个对象给耽误了,要不也早就结婚了。她原先没想到那个姑娘做事这么绝,说是跟着她叔出国做贸易,后来干脆就不回来了,忠毅白等了她两、三年。
忠毅到现在还没结婚,都是叫她给耽误了。姜母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东边的邻居跟姜母关系不错,听见她这么说,猛地想起个茬儿来,就跟她说:“城里我有个远房亲戚,她们家来了一位客人,是外县来的姑娘,那姑娘我见了一次,大眼睛,大高个,长得挺带劲。”
姜母这么一听,忙问她:“那姑娘多大了?”
人家告诉她好像是二十二,她对人家说:“二十二咋还没对象?”
那邻居看姜母动心了,就跟她说:“那姑娘家境不好,家里就娘俩,挺穷的。要是你们不嫌弃她出身,我就带你去看看去,除了这方面其他都挺好的。”
吃完中午饭,姜母就跟那邻居去了。一路上邻居还在跟姜母夸赞说:“那姑娘长得可标致了。”
姜母心里早就盘算好了,穷点就穷点吧,长得端庄就行了,忠毅这岁数也不能再挑了。
想着想着,脚底下的步子就越发地快了。
1-8.
晚上吃饭的时候,姜母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件事跟忠毅说了。
忠毅的态度倒是不卑不亢,在他的心里面,这两年早就把去国外那个女孩淡忘了。只是他没想到这么快,他母亲就找到合适人选。
姜母说:“我都跟邻居你周姨说好了,等你放假就把人家姑娘叫出来,跟你见见面。”
忠毅问他妈:“你咋这么着急?你和我爸着急抱孙子了?”
姜母说:“抱不抱孙子是次要,你都老大不小了,有合适的就得抓紧订婚。虽然你的工作不是铁饭碗,但咱们家也算是衣食无忧的富裕人家,你爸早就把你结婚的钱攒好了。”
姜忠毅比魏连山大一岁,快要二十六了。要不是给耽误了几年,现在也许已经结婚了。他们家原先在乡下养黑熊,养貂,确实是专业户,后来他爸又去做花岗岩生意,赚了些钱。忠毅不喜欢养这养那的,也不喜欢做生意,为人太实在,原来是在车队当司机,开大车拉木材,后来认识了魏连山,俩人处得关系很好,像兄弟。魏连山不干了,他也不干了,下来以后就给经理开小车。
姜忠毅的性格谦和,平时凡事都由着母亲,可真要去跟人家见面,不由得有些紧张,后来几天就一直在心里斗争,老是想着见面的事,每一想起,心就跳得厉害,耳朵发烫。
眼看着就要跟人家姑娘见面了,他也忙活起来,能想到的准备都给做了。洗衣服,剔头,擦皮鞋。头见面的几天,他天天刮胡子,猛一看着确实年轻了许多,就是刮得太勤了,下巴的皮有些生疼。牙也是天天都刷好几次的,刷完对着镜子瞅白不白,这才注意到他自己的脸上已经有皱纹了。
看来真是老了,见面的事还真得抓紧,不能再托了,眼下首要的事情就是这个。
1-9.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星期天,忠毅一大早就起床了。晚上也没有睡好,精神一直就这么亢奋着,血脉翻腾的。心跳得太快,怎么也慢不下来。快天亮的时候好像也睡着了,朦朦胧胧的,并不踏实。他妈跟他说过那女人的模样,人并不丑,就是家庭不太好。他觉得条件不高反倒好办,这桩事情容易成功些。真要是条件好的,他也未必敢去见人家。
起来以后对着镜子先是看眼窝,过了这几天功夫,已经不青了。然后穿了件新洗过烫过的白衬衫,外面套了个薄毛坎肩。是深灰色的,肚子上有一块几何图案,他故意没把西服上的那两颗扣子系上,好显得时髦些。就是西服太次了,料子也不好,有些发白又有些发灰,说不上是什么颜色。皮鞋倒是擦得铮亮,那是昨天晚上就打过鞋油的,要不然早上怕来不及拾掇,那新擦的鞋油味道很难闻,所以擦完鞋放在窗外晾了一宿。这都是事先就考虑好的。
吃过了早饭,忠毅就要准备出发。车都发动了,姜母又把他叫了回来,让他在家呆半个钟头再去,她怕人家起不了这么早。忠毅又在家坐了一会,又上院子里把车擦了一次。
这是他们单位的吉普车,单位里其实也是有车库放这车的,但是他喜欢下了班就把车开回家去,省得上下班再骑自行车了。
约莫着又过了半个钟头,忠毅开车先去了周姨家。一敲门,周姨很快就来开了,人家早都准备好了,正在等着忠毅。这周姨一见忠毅,很是热情,也没耽搁,上了吉普车,带着忠毅相亲去了。
路上,经这位热心邻居周姨介绍,跟他相亲的这个姑娘,名字叫徐晓芸,今年二十二岁,佳河县来的,现在住她老姨家里。刚来没几天,那孩子人也老实,到了生地方,还没怎么出去。
忠毅越听越靠谱,不自觉地,脚底下踩油门的力度就狠了。所以没一会儿,俩人就到地方了。
忠毅和周姨刚一进院门,就有妇人出来迎了,周姨介绍了一下,忠毅向人家鞠了一躬,叫了声老姨。
忠毅这才注意到妇人后面站着的姑娘。
他心想这个就应该是给我介绍的对象了,心里这么想,但是也没好意识直接问,这家人也是糊涂,都到了屋里,才想起跟忠毅介绍。
“忠毅呀,你坐你坐!”
忠毅刚把屁股沾着椅子面上,才听得那妇人说:“忠毅呀,这是我们家晓芸,我是她老姨。”
他这刚一坐下,就又站了起来,冲着晓芸点了点头,笑着问了好:“你好。姜忠毅。”
徐晓芸见姜忠毅有些呆笨,人又腼腆,有点想笑,又不好意思,但是脸上还是浮现出笑意来,好在这个时候忠毅向她打招呼,她就笑着回了句:“你好。”
姜忠毅坐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最后还是徐晓芸招待得周到,叫他坐下,又给他倒了杯白开水。
忠毅看着那水,又不自在起来。放在那里不喝的话,好像会显得他不满意这亲事。他为了显示他很重视徐晓芸,赶紧拿起来喝。但是那杯子拿起来很烫手,想喝也喝不下,于是只能左手倒右手,放下又端起来。
忠毅的眼睛不敢四处看,气氛好像挺尴尬的,心里想着说些什么才好。
幸亏听得徐晓芸的老姨跟他说:“忠毅,你妈呢?”
“在家洗床单呢。”
“我还想说哪天找你妈打扑克呢,以前也没一起打过,这回好了,可以让你周姨以后叫上你妈,我们总能玩到一块儿。我打得也不好,就给凑个牌搭子呗,哈哈!”
姜忠毅说:“我妈她打得也不好,就是老爱玩儿,大钱不敢耍,白玩又觉得没意思。”
徐晓芸她老姨自打见了姜忠毅,心里很喜欢,跟忠毅絮叨个没完。周姨见她话太多,马上插话说:“忠毅呀,晓芸刚来咱这儿,哪都没去过,你带她溜达溜达去。”
徐晓芸她老姨也不傻,当即就明白了话里的意思,就跟忠毅说:“是呀是呀,你俩出去转转吧。”
姜忠毅可算松了口气,站起来就要走。徐晓芸倒是也没说什么,跟着姜忠毅后面,等到俩人都上了车了,姜忠毅才敢正式地瞅了徐晓芸一眼。
姜忠毅对徐晓芸的喜欢,就是从这一眼开始的。
世界上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偶尔有一天,出现了人生轨迹的交际,更多的人的交际只是一个点,或是几个点。只有极少数人的交际,是一条线。更少更少的人,他们的前半生没有任何交际,后半生的轨迹却是完成重合的。这需要怎么样的聚变?这需要怎么样的一种力量?
但这一切的聚变都是因为最初多看的那一眼开始的。所以这一眼就成了之后一切连锁反应的导火索。
姜忠毅眼前的这个徐晓芸,大高个,双眼皮,皮肤白皙,牙齿洁白,脸上隐约两个酒窝,不是很明显。头发乌黑发亮,左右各扎着一个俏皮的麻花辫子,还留了刘海,那刘海上的头发,一根是一根的,顺滑的很。耳朵上带着银耳环,清新素雅,衣服虽是旧的,竟然一尘不染。脖子上围着大红的毛线围巾。那围巾非常显眼,把徐晓芸烘托得像个新娘子,娇嫩高贵得很。
这个不错,这个好。姜忠毅心里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听见徐晓芸说:“姜忠毅,我们去江边吧?”
忠毅被这一句话惊讶到了。他没想到这个徐晓芸外表羞涩,性格还挺开朗,倒显得他拘束得很。
还有就是,平时要是别人直呼他的名字,他总觉得厌烦,可是听着自己的名字从徐晓芸的嘴里说出来,怎么听怎么顺耳,喜欢得很。
徐晓芸是个极其懂事的人,大方端庄,话虽不多,却句句能说在点儿上,很是得体。她见忠毅有些局促,倒是个好人,样子土了些,却也能接受,她家条件不好,能有个这样的对象也是不错的。
她刚才的话其实也是想帮忠毅解除尴尬。
“好……你去过我们这里的江边了吗?”忠毅问完突然觉得自己等于白问。晓芸说:“没有呢,我特别想去看看!”
“那咱们走着。”
吉普车朝江边稳稳地开了过去。
路上,晓芸突然问道:“你抽烟吗?”
忠毅赶紧回答说:“我不抽烟。”
“那你车上咋有烟呢?”晓芸看着挡风玻璃前的那一整条香烟问道。
忠毅说:“那是单位发的,准备拿去给小山。我又不会抽。”
晓芸问:“小山是谁呀?”
“你不认识,他是我的一个好兄弟,开鱼馆的,改天我带你去尝尝他那的手艺,很不错的。”
姜忠毅载着他的相亲对象,心里美滋滋的,他没想到一贯不被他看好的相亲之举,也能够遇到心仪的。
很快,到了江边,两个人沿着江堤边散步。
时值春暖江开,浪花缓缓地拍打着岸边的黄沙,有些风,将徐晓芸的发丝吹起,撩拨着她白嫩的脸颊,也撩拨着忠毅火热的心。
江心,水流湍急,就像执意要走却根本无法留住的人。
该走的走了,该来的来了。生活总是残酷中带着一丝美好。
徐晓芸当然不是第一次看见江,但是这里的江肯定是第一次见。她没有见过海,生平第一次感觉心怀开阔的时候,就是当下了。她试着深深地呼吸,努力地感受着这里的空气。
随后,她就这么沿着江边一直走着,一直看着,她能感觉得到每一步所留下的脚印,以及它们的深浅,甚至它们的心情。忠毅一直挨着晓芸身边,无论走多远,他都愿意陪着,这个姑娘太好了,虽然说不上哪儿好,可就是让人喜欢,不想放弃。
晓芸喜欢这里的景象,一只只渔船,织网的妇女,嬉戏的儿童,喜欢挂着鱼干的木头架子,喜欢白花花的渔网,像是老人雪白的头发。
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走出了很远。他们俩就坐在江岸边聊天。
和一个活生生的自己喜欢的人就这么坐着,也是件幸福的事。人生要是能遇见让自己决定去爱的人,即使等得久点儿也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她要是愿意跟我好,我会爱她一辈子。
忠毅现在的心还悬着,除非等到领了证,她才是他的人。
晓芸:“这江里面都有什么鱼?”
忠毅:“那可多了,得有六十多种。出名的就是‘三花五罗十八子’,大马哈是最有名的,还有最常见的鲤拐子,鲫瓜子,白鲢,川丁子,柳根子。你钓过鱼吗?”
晓芸:“当然钓过!我钓鱼可厉害了!我钓过老头鱼,还钓过泥鳅呢!”
忠毅:“泥鳅还能钓上来?”
晓芸:“能呀,你不信?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鱼钩刚好勾在鱼肚子上。”
忠毅:“哈哈,那我们下次去钓鱼吧?”
晓芸:“好呀!那你有鱼竿儿吗?”
忠毅:“小山有,我下次去拿。”
晓芸:“你和他的关系很好吗?今天听你提他好几次了。”
忠毅:“当然了,我们俩都出生入死好几回了。”
晓芸:“你是说……你们这里很危险吗?”
忠毅:“哈哈,当然不是!我们这里很好,有城市,有农村,有农场,渔场,荒原,山脉,大江,自然物产很丰富。山林中野生动物也多,还有丹顶鹤呢。贸易业也很发达,大市场每天都有很多外国人来。”
晓芸:“我很喜欢这里,很喜欢这个江边。”
忠毅:“是嘛!那太好了,以后就别走了。”
晓芸:“我老姨也说让我在这儿找工作,就别回佳河了。我也想,但是我妈一个人在佳河,我又怕时间久了想她。”
忠毅:“以后可以把她接过来呀。你想想看,你老姨也在这儿,算是有个实在亲戚照应着。而且我也在这儿。”
实际上忠毅最想说的是最后面这句。他对徐晓芸是百分之百的满意,他想试探一下徐晓芸对他满意不满意,毕竟是经过介绍人正式介绍的,好歹得给个意见不是。
可他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人家,拐弯抹角地聊天,也找不着试探对方的机会,费了半天劲才想出这么一句。他实际上是想说,我也在这儿,你要是觉得这门亲事行的话,就别回去了,留这工作吧,咱也方便抓紧把婚事给办了。
可是这直直的大白话,谁好意思恬着脸说出来。真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的,本来好端端的人,真要是这么说了,那还不被看成流氓或者结婚狂了。
他要是不说后面那句还好点,一说出来,晓芸就察觉了。她也尴尬住了,不知道回答什么才好,看样子忠毅对她是很满意的,那就好,要是反倒他不满意,那就糟了,传出去也没脸见人了。晓芸是个好强的人,日子苦点无所谓,但是绝不能抬不起头来。
最后晓芸的回答是:“恩,那好,要是有合适的工作,我就不走了。”
忠毅一听徐晓芸松口了,心里的大石头就放下一半。看来这一回他的婚事是有着落了。
1-10.
姜忠毅和徐晓芸站起身刚要往回走,远处的荒草丛中传来阵阵说话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二人举目远望,看见几个穿着警服的人在寻找着什么。
“没事,附近总有渔民打架。快走吧。”
为了不在徐晓芸的心里留下本地治安不好的印象,忠毅催促着晓芸离开了。
就在江边的荒僻处,有一个天然形成的凹陷区,此刻数名刑警队员正在此地出现场。
是的,没错,就在姜忠毅和徐晓芸刚刚坐着的地方不远,已然成了凶杀案现场。
刑警队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安小峰,正蹲在凹陷区里的一具尸骨旁边查看着,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稚嫩之气,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守在那堆烧得所剩无几的人骨头旁边研究了半个多小时。
“我觉得是人骨,错不了。”安小峰说。
“这么快就做出谋杀案的判定了吗?”说着话的人是站在凹陷区边缘的一个中年男人。
话音刚落,正好有一位辖区派出所的警员搜查完现场周边,看见凹陷区的两位生面孔,忍不住打听起来:“二位是?”
“锦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全树海。”站着的中年警察亮出了证件,他的眼镜虽小,却很有神,让人肃然起敬。
“锦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一大队,侦查员,安小峰。”说这话的大学生仍旧蹲在尸骨旁,完全不理会身后的人。
“哎呀,久仰大名!老全您亲自出马办的案子,估计很快就可以破了。”
“去去去,别溜须拍马,老全也是你叫的?!”安小峰终于站了起来。
那警员赶紧冲老全点头哈腰,转身忙去了。
“对,没错,是谋杀案!”安小峰斩钉截铁地说道。
“那你给我分析一下这起谋杀案件吧,大学生。”
“咦?不是说好了嘛,以后别管我叫大学生。我都毕业了,现在是一名正式的刑警队员!”
“职业生涯的第一个案子就碰上这么棘手的案子,你够倒霉的。大学生!”老全逗趣道。
“你还叫我大学生是不是?那我可管你叫老头了哦?!”
“好,你先说案子吧。”
“说就说。你觉得很棘手吗?我怎么觉得一般。从烧剩下的尸骨判断,死者应该是一名三十到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性,头骨有明显的碎裂痕迹,应该是致命伤。所以我判断,死者是被人用钝器敲击头部,导致颅脑重度损伤死亡,死亡后,被抛尸在这里,用汽油进行焚尸。所以,这一定是谋杀,而且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行呀,不错。”
“就这四个字评价?”
“嫌少?”
“你不同意我的判断?”
“在新的证据出现之前,我暂且同意你好了。”“这么勉强?”
“不然呢?”
“不然你给我说出点新的看法出来呀!”安小峰明显不服气。
老全只好指着尸骨说:“尸骨灰里残存着没有燃烧尽的塑料块和麻片,附近荒草里有一条被压过的痕迹。说明尸体是被装进一条麻袋里,然后被人用一辆摩托车驮到了这里。凶手用一根塑料管抽取了摩托车油箱里的汽油,然后直接浇注在麻袋和尸体上,点燃后,连同塑料管也扔进了火里。凶手是一个人,男性的可能性更大,二十到三十五岁之间,体力极好,可用轻松地扛起一个男人的尸体,应该是常年从事体力劳动者。从他焚尸的步骤来看,应该是之前计划好的,不是临时起意来这抛尸焚尸。”
“嗯,凶手之前到这边踩过点。”安小峰不得不赞叹姜还是老的辣:“那为什么非得烧掉呢?扔进江里冲走不就完了嘛?!”
“凶手也许跟死者认识。或者,凶手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
“看来很难找到尸源了。”
“没错。尸体燃烧得很充分,仅剩头骨和躯干部位的几根大骨,还被烧得变了形。凶手应该是晚间烧的尸,而且他当时守在这里很长时间,直到确保尸体烧得差不多才走的。”
“这心理素质,太牛逼了!”
“也许是惯犯。先从有前科的查起吧。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