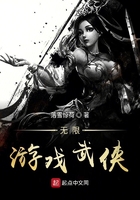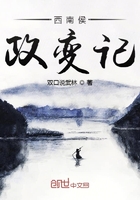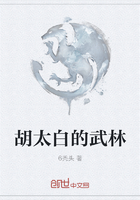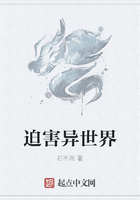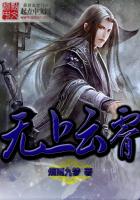皇帝策奉庭暴病而死,英年早逝,登基十年,好色贪淫,昏庸无能,但是多亏了众臣都是才华出众的一代名臣,终究落得个有功无过评价,但朝廷众臣都知道,他这十年好吃懒做,骄奢淫逸,宠信亲信,四次大规模扩充后宫,新建三座宫殿,内藏库比国库还要充盈,幸亏朝政大权都由三大家把控,实际上就是太傅和丞相的斗争,军队全部把控在冷秋泉手里,到了最后,禁军羽林卫都让余槐荫把控。十年来,策奉庭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朝政,这也是三大家对他的容忍的极限。虽然没有太多的骂名,但朝廷争论过后,还是定庙号为顺,为大景思宗,谥为大景顺帝。
策奉庭驾崩,太傅亲自主持国丧,但谁能继承大宝,登临九五,成了难题,三次大朝没有商议出来结果,朝臣出了三种意见,怎么三种呢?太傅主张迎立皇子,宗室请先皇兄弟回京,冷秋泉一方有要睿宗嫡系血脉怡王世孙。
冷秋泉本来是军职,本不涉及朝政,但在纪南国走后,冷秋泉罢黜军职,改兵部尚书,封安国公,大将军由大司马齐知锋担任,齐知锋已经七十有余,是冷秋泉父亲的旧部。
咱们说冷家说的少,实际上冷家势力只是不在朝政,不在六部,大景军职都出于冷门,冷家军功起家,势力盘根错节,在军中声望鼎盛,势头压过太尉和大司马,到后来,太尉和大司马都由冷家出来的老人担任,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荣誉。除了其他的边军,没有冷秋泉同意,兵部调令调不动兵。但是有一点,当初纪南国死守户部,卡住他的命脉,牧汉经把控吏部,他在朝廷没有文臣势力支持,而且穆宗死前罢免了冷秋泉和多名将领,想要压倒冷家,羽林军和宗室手中的京畿八大营,也是限制冷家的重要手段。
冷秋泉一个月就安排人占据了原来纪南国三成的势力,还有不少相府旧部投靠他,因此上在朝堂上也有不小的权威。
按常理说,皇帝的继承都是父死子继,实在不行,兄终弟及,尤其讲究嫡长子继承,赶巧的是,策奉庭虽然好色贪淫,但是孩子还真不少,他有四个儿子,八个女儿,但都没有成年,十年换了三个皇后,前两位都没有生儿子,他原配连孩子都没生过,第三位生了儿子后封的后位,但是孩子早夭,由于他是暴毙而亡,没有来得及留下遗诏,所以才引出这么大的麻烦。
经历数日的朝堂争论,各方终于妥协,由太傅提议,立先皇幼子为新皇,于是,五岁的皇子策泽元被抬上了皇位,免除一切繁文缛节,于策奉庭灵前讯速登基,太后郑氏临朝,垂帘听政。郑氏出身平民,其父本是长都城外一个开野茶摊的,郑氏年轻貌美被出城打猎的策奉庭选中,郑氏生下长子,皇帝不听劝称劝阻,一意孤行,扶郑氏为正宫,郑家摇身一变,成了当朝国丈,皇亲国戚,显赫一时,在长都嚣张跋扈。郑氏在策奉庭那吹了不少枕边风,也只求下来个安乐侯的爵位,还是没有官职,第二年皇子夭亡,郑氏失宠,郑老头也被削了爵位,不敢嚣张跋扈了。因此上郑氏在朝中无权无势。
宗室不满,提出由宗室长者摄政,直到皇帝成年亲政,冷秋泉竟然表示支持,大出朝臣意料。几番妥协后,终于选出一位,年高有德,众人信服的摄政人选,此人就是穆宗皇帝的幼弟,岐王策纪长,也就是老皇叔。
宗室会选出这么一位老人来,也是有原因的,思宗皇帝的弟兄,多数被裁决,剩下几位没有权势的也被发到边远封地,朝中无人信服,宗室有意收回政权,所以就得选出一位有实力能扛得住太傅和冷家压力的重臣来。
再来说说这位岐王殿下,他是穆宗最小的弟弟,聪慧豁达,也算是文武兼备,深受其父睿宗欣赏,三十年前,策纪长本来就是朝臣们支持的皇帝人选,但不知道为什么,老皇帝睿宗的遗旨还是选择了穆宗,穆宗封策纪长为岐王,不准其回封地,也不准其参与朝政,专门选择宗室子弟和平民建立京畿八大营,让其执掌四营兵马,有人说穆宗是压制岐王,对他始终不放心,也有人说是扶植岐王,让他钳制冷家在军中的实力,众说纷纭,一时不辨,数十年下来,岐王越来越被边缘化,数年来,除了宗庙大祭,和红白之事,策纪长从没踏足朝堂,甚至也放开了对八大营的掌控,几个月才去一次军营,慢慢的众人都几乎忘记了这么一位身份尊贵的亲王。
如今宗室提出由这位亲王摄政,百官皆是茫然,有些年轻官员都没听过他的名字,甚至冷秋泉和牧汉经都有些惊讶,牧汉经已过古稀,参与过曾经那段历史,知道些别人不知道的秘辛,冷秋泉没参与过,但还是听其兄述说其实,只能说当年曲折,某些手段腌臜不堪。但是如今岐王却得到所有宗室的支持,其中定有缘故,但看牧汉经如何处理。
牧汉经端坐一旁,闭目不语,听着朝臣们纷纷议论之语。喧喧嚷嚷了半天,终于安静下来,众人目光看看冷秋泉,冷秋泉嘴角上挑,旁若无人地斜靠案几,发觉众人目光,面带讥笑看了看牧汉经。牧汉经知道百官讨论结束了,都在等着自己拿主意,冷秋泉如果知道当年之事,恐怕也等着看自己笑话。
牧汉经一睁眼,果然看见冷秋泉那玩世不恭地嘲笑,深出一口气:“启奏陛下和太后,老臣同意,岐王殿下摄政,统率朝纲,位同丞相,请陛下和太后下旨。”
此话一出,大殿上又是一片喧哗,众臣不解太傅为何会同意让一个名不转经传地王爷来分自己的权力,很明显,宗室想以此为契机,重新把控朝政,所有的力量都押在这上面了,太傅就如此有把握能压制住这位出头的宗室亲王吗?
冷秋泉还是那副看戏的表情,不管不问,丞相洛臣道明白,朝臣都是太傅门下,如今相权名义上分给了冷秋泉,实际上自己还是有很大的掌控权,但如今又要来一位亲王,看来这相位恐怕自己做不稳当啊,不由得钦佩当年纪南国雷厉风行,刚毅果决地手段。看了看太傅脸色,看来他已有决定,如今太傅提议,自己也只好附议了。
“启奏陛下、太后,先帝新丧,陛下年幼,当有一位重臣辅政,效法周公辅佐成王,太傅所言极是,臣附议。”
众臣面面相觑,就在此时,只听一人高声喊喝:“陛下“
众人就是一惊,纷纷看来,太傅也不由得侧目,说话之人正是冷秋泉。
就见冷秋泉正身施礼:“陛下,臣亦附议。“
说完侧身一看太傅牧汉经,二人目光相对,各自心中明了。
百官纵然不解,还是异口同声:“臣等附议。“
太后郑氏战战兢兢坐在帘笼后的凤位:“众,众……众卿,没,没有意见,哀,哀家当然……”
话还没说完,冷秋泉又大声喊到:“请陛下恩准!”
郑氏吓得一跳,差点从凤座掉下来,赶紧回答:“是是,陛下当然同意,当然同意。”
当天圣旨下到了岐王府,岐王接旨不奉召,第二道圣旨到了,依旧如此,朝廷连下三道圣旨,余槐荫亲自带着羽林军前去下旨,策纪长还是不肯任职。
余槐荫皱着眉头:“你不做还会有别人做。”
但是策纪长仍然满不在乎,“那谁想做就让他去做吧,应该不少人都盯着呢吧。”
余槐荫不再理会,转身就要走,二人相背,策纪长补充一句:“比如,和将军有联系的几位宗室近人。”
余槐荫走了两步,到了门口,听见他终于能说句实话,又转身走到策纪长身前:“你不想做也没关系,有没有人做都没有关系,结果都是一样的,可能与你预想的有些出入。”
压低声音,贴近他的耳朵说完最后一句:“你和大景最后的机会。”
随即余槐荫转身大步离去,留下心惊肉跳的策纪长慢慢消退余槐荫的杀意。
第二日,策纪长上朝领受所有的封赏,随后归座,位在冷秋泉之上,四人成为名义上的辅政大臣。众人开始安排大行皇帝丧事,策奉庭停尸半月终于得以入葬。登基大典应策纪长要求,隆重举行,延用年号,次年改元圣治,百官朝贺。
远在隋州的隋王收到消息,勃然大怒,秘密派人到长都面见余槐荫,相谈十分不愉快,这些年暗中与余槐荫联系多次,送了不少礼物,但余槐荫每次都拒绝,所以每年都为余槐荫添置产业,照顾余槐荫属下旧部和远方亲属。余槐荫每次都汇报冷秋泉,隋王也知道,这也是变相收买冷秋泉,这次隋王想要借势,长都宗室已经接受他,但是被牧汉经插手,始终不退,与帝位失之交臂,冷秋泉更是直接拒绝他,找什么睿宗嫡系血脉,如今选摄政宗亲,连宗室都直接放弃了他,选一个老头子,这是把他当成弃子了啊,而且他每年给朝臣送礼何止百万,这帮人也把他当成收租佃户了。
冷秋泉让余槐荫送一封信给隋王,打开有一看,只有两个字: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