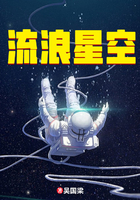苏联红军在向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上千英里宽的地方撤退,这里也是苏联的核心地带。在德军的猛烈追击下,苏军士兵在向后方撤退。苏军的许多战壕都是匆忙间挖出来的,其中一些还没有使用就被迫放弃了……任何地方随时都会遭受德军坦克和飞机的攻击。
1941年6月 士兵
苏联红军在向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上千英里宽的地方撤退,这里也是苏联的核心地带。
然而,最绝望的撤退莫过于在白俄罗斯了。
在德军的猛烈追击下,苏军士兵或走或跑或爬,在向后方撤退。整个后方的制空权已经完全丧失,对此,士兵们颇感震惊。
飞机库和机场还在熊熊燃烧,机场空无一人;部队大院已经被丢弃了,还冒着烟。当地许多人,特别是犹太人,把这里当成他们的家。田地或森林里到处都是战壕,有的非常必要,有的只是预备性的,还有些战壕根本就没有用处。战壕都是匆忙间挖出来的,许多还没有使用就被放弃了,更不用说人们的恐惧和损失了。
道路上都是一派恐怖的景象。
公路上有一架德军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完好无损。三个农民正急匆匆地从飞机的机枪上卸子弹。受伤的德军飞行员把头盔丢在路上,躲进了森林。
一个赤手空拳的匈牙利士兵站在十字路口,正在指引撤退的苏军到一个宽敞的地点去集合。前一天,这个士兵被他的上司丢在这里,他就一直没有离开。
一位刚刚离开医院的年轻女飞行员,得了胸膜炎,还发着高烧。她在寻找一架没有飞行员的飞机,要“飞到某地”。一处乡村公墓被炸弹击中,路人能清楚地看到暴露在外的尸体。有个精神错乱的士兵正在告诉人们,他们都已经当了俘虏,周围的军官实际上都是德国人。但没有人愿意停下脚步听他讲话。
实际上,每一个亲历者都注意到了那个夏天:天气炎热,阳光高照,小麦和黑麦长得都很高。
恐惧升级为恐慌,扣在扳机上的手指丝毫也不放松了。听到远处的枪炮声,一个技术兵紧张得要命,大声喊叫道:“祖国被出卖了!”然后,随意射杀,他的两个同事被打死。第12空军师的同事听到枪声,以为德军装甲车来袭,慌忙撤退。他们一口气开车跑了40英里,直到被一个检查站拦住。
这时,一个平民被巡逻的一队士兵截住,要他出示身份证。这个人近乎歇斯底里地喊道:“你们要我的身份证?你们想要抓住希特勒?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被士兵近距离开枪打死。
越来越多的士兵自杀了。尽管在军官的严密监视下,还是有许多士兵离开了连队。当被追击时,他们就向后面的人开枪。
一个掉队的军官,偷偷藏在别列兹纳河桥下的水里,用树叶和草做伪装,当有空袭时,他就借机向贝利亚的警察开火。但最后还是被发现了,他顽固地抵抗,直到被打死。
最大的威胁来自空中,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德军飞机的袭击了。
掌握绝对制空权的德军飞行员,熟练而又肆无忌惮地射杀着后撤的苏军和难民。德军飞行员沿着拥挤的公路低空飞行,用机枪扫射苏军士兵和难民,而把炸弹省下来炸坦克、汽车和火炮。德军空军的袭击非常自如,没有受到任何反击。有时,当飞机的弹药用完后,飞行员甚至把飞机飞得很低,要用机身下的轮胎把地面上的行人压扁。侥幸逃脱的人,背上都会留下一道很宽的青痕。
政府官员或军队的指挥官都不清楚,到底有多少难民离开了家园,他们或躲在森林里或正奔波在逃难的路上。
在白俄罗斯,难民特别多。
几个世纪前,白俄罗斯就被俄国和波兰瓜分了,现在多数地区还是不发达的农业区,不像他们的对手波罗的海国家。在白俄罗斯从未形成过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许多人认同莫斯科,少部分人对德国抱有希望。所以,和立陶宛人不同,更多的白俄罗斯人在逃往东部。同时,白俄罗斯的城市还有许多犹太人社区,这些犹太人并不相信斯大林的宣传,但也不相信德国正在发生的种族屠杀,所以,他们选择留下来。还有成百上千的犹太人也上路了,加入到难民队伍中。
难民向东走,要到更安全的后方。后撤的红军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也有一些部队,被命令反击德军,只好向西移动,这又加剧了公路的拥挤。公路上、小道上,到处都是混杂在一起的难民和士兵。
德军飞机肆意射杀他们。很快,难民就意识到,即使德军飞行员没有把他们当作靶子,自己也会成为这支庞大的移动目标的一部分。然而,难民要想到达后方,就不得不走公路。要想从森林穿过去,那几乎不可能。带着孩子,还有包裹,不管多么少,要想穿过浓密的丛林,非常困难。
白俄罗斯的森林素以充满危险的沼泽而著称。南部边界的普里皮亚季沼泽地面积很大,就连红军和德军都要绕着它走。即使有人确信,毗邻公路的地方结实、安全,但那里的混乱局面对逃亡的妇女和儿童来说也是一个威胁。
偶尔,也有机翼上带着红星的苏军飞机在头顶飞过。只是这些飞机数量很少,飞得也很慢。这时德军的飞机往往会从它们的后面追近,然后就是一阵准确的扫射,这样,不费什么力气就击落了苏军的飞机。有时,出于恐慌,或是忙中出错,苏军飞行员也会误扫射自己的部队。
很快,撤退也教会了人们许多生存的技能,这是他们在新兵训练营里从未学过的知识。其中之一,就是绝不能躲在一所房子里。当遭受轰炸时,建筑会轰然倒塌,里面的人都会被埋在瓦砾下。任何地方随时都会遭受德军坦克和飞机炮火的攻击。
1941年夏天,天气异常干燥,河水水位降到最低,德军坦克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过河的渡口。
人们很少能在同一个地方过夜,所以也不必再找一个合适的露天宿营地。
军需负责人也带着那些本该由他们保管的好东西消失了,每个士兵不得不自己带着那点可怜的生活用品,如香烟、干面包和罐头食品——都是些咸凤尾鱼罐头。
事先准备这些配给品的人,显然对人体生理知识一无所知。吃咸凤尾鱼要喝水,而饮水又供应不上。在村落里,只有深水井才有水,水又冷又咸。在森林里逃亡的人们只能喝泉水,如果连泉水也找不到,就只好从溪流、水塘或河里取水喝。在炎热的夏季,水里布满了虫子,要把水煮沸喝才会更安全。但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来煮开水,许多人因此得了鞭毛虫病。
泥泞的春季之后,道路就变得干燥了,甚至连一些原本难以行走的道路也可以走人了。但往往一场雷阵雨之后,几分钟的时间,道路又会变得泥泞不堪,成为坦克的陷阱。暴风雨过后,当泥泞的路面逐渐干燥时,司机不得不特别小心,不要破坏了路面;否则,后来者会陷入坚硬的车辙中。
尽管喝水有困难,但对士兵来说,从森林逃跑不失为一种最好的选择。西部边境一带分布着大片的森林,那里长满了栎树、松树和白桦树。茂盛的树叶为士兵提供了掩护。
在炎炎夏日,许多沼泽地都干涸了,士兵们可以找到狭窄的小路,甚至可以在沼泽中发现一块结实的地方。坦克还是不能通过这里,它们会辗坏小路,陷入沼泽底部。
森林里有时很安静,有时也很拥挤,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撤退的士兵队伍,零散的掉队者,落伍而又急着赶上队伍的军官,几个小时前刚刚入伍的新兵……还有难民。多数人看上去疲惫不堪,也很难看出他们的年龄。
一旦有德军飞机飞过头顶,人们就会立即冲向密林深处。森林里的每一处开阔地都可能遭到轰炸。茂密的森林里充满了蚊子,许多人因为蚊虫的叮咬或喝了沼泽地的脏水而拉肚子。还有人因高烧而发抖,这是因为蚊子传播了疟疾。
最糟糕的是,没有人知道,当一个人从东边的森林走出去时,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人们挣扎了好多天才活了下来,但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已被德国人占领,或者是还在边境线上。
当西方方面军的残余部队向东部缓慢移动时,仍然还有部队在向西部进发。已经没有几支新部队可以派遣了,只好把许多级别较高的军官紧急派往白俄罗斯,去处理那里的军机事务。那些破旧的公交车辆把军官和将军们匆忙运到火车站,然后向西驶去。火车都是从莫斯科火车站出发的。火车站一片漆黑,只有隐隐闪亮的绿灯使车站显得更加阴森恐怖。车站里,难民和军人混杂在一起。警察架起了钢制路障来保证道路畅通,这反而使车站变得更为混乱。
人们骂声一片,跳过路障,到处寻找自己要乘坐的火车。没有一列火车能正点。
6月26日,人们已经无法前往明斯克了。没有人知道那里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所有的火车,不得不在离明斯克100英里远的东北城市奥尔沙火车站停车,然后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这也是最容易遭受容克轰炸机袭击的时候。这时,没有几个人能分辨出到底是德国飞机还是苏军飞机,只有当空中充满火球和浓烟时,人们才意识到,遭德军轰炸了。
奥尔沙是个铁路枢纽站,铁轨上停满了蒸汽机车。车站的负责人事先就得到德军要轰炸的警告,他们命令蒸汽机车鸣放汽笛。汽笛声听上去像是在咆哮,抖动的机车笼罩在浓浓的白色蒸汽中,火车周围的人们说,不知为什么,这个景象甚至比空袭还让人紧张、不安。
奥尔沙西边的道路已经塞满了车辆。向西增援的部队车辆和向东运送伤员的车辆搅和在一起。路上到处都是难民。痛苦、绝望的人们,明显流露出对红军的失望情绪。这在一个星期前是不可想象的。
最受罪的是孩子们。空袭中,许多孩子失去了父母。红军军官把他们安排在开往内地的卡车上,嘱咐驾驶员把他们送到一家正在转移的孤儿院里。这个主意听上去不错,有许多孤儿院正在白俄罗斯的路上向东转移。1937年的大清洗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孤儿,现在当局正在疏散这些人的后代。一些新的孤儿年龄太小,有的连自己父母的名字也记不住——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在包里放了孩子的出生证明。当他们最终被送到一家孤儿院时,不得不给他们起一个新名字。孤儿院院长有时会以孩子被发现的火车站名或地名来命名。
许多在外过夏令营的人也变成了难民。德国的入侵太突然了,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把孩子送回家。现在,他们只好带着孩子离开前线,脑子里一片混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许多夏令营也成了德军飞机袭击的目标。这可能并不是有意识的攻击,因为从空中看下去,夏令营的帐篷会被误认为是士兵的营地。夏令营没有汽车,孩子们只好走到最近的火车站,想搭上一列火车。考虑到火车司机更容易为一群受惊吓的孩子们停车,夏令营的工作人员就把孩子们安排在铁路边,让他们站在那里,每当火车经过时,就向司机挥动红领巾。有时,有的火车会停下来,有的也不停车。当司机减速慢行时,工作人员会把孩子们扔到平板车厢上,那里挤满了人。
公路的交通状况更糟。烧毁的汽车,还有弹坑,都给各种汽车通行造成障碍。夜里,不允许司机使用车前的大灯照明,这样又发生了许多交通事故。天一亮,轰炸就开始了。就像一群受到惊吓的绵羊,卡车纷纷钻入森林中。也有许多卡车被卡在树中间,或是陷入沼泽中。德国人好像神通广大,无处不在,人们想象,德国人能在远离前线几英里的地方看到他们。从防空火炮中冒出的一股股白烟,让人们相信,德军正在不远的地方。
国防委员会向前线紧急调运部队和军需物资,但铁路不足以容纳所有的火车通行。通信系统被破坏,也不能把增援部队的进展情况及时反馈回来。
国防委员会向西部派出26列专列,但有10列火车不知去向。有几列火车不得不改道,但却走错了方向。在奥尔沙,两列装满坦克的专列,已经被推到另一条铁轨上好几天了。其中的一些坦克是要装备第4集团军的。此时,第4集团军正在沿着普里皮亚季沼泽的边缘向东南方向后撤。
6月26~28日 西方方面军,第4集团军
6月26日夜,第4集团军军长科罗布科夫(Korobkov)少将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幸灾乐祸。从战争爆发以来,他就一直在想,他不会在战略中心地带的白俄罗斯指挥第4集团军,而是要指挥他先前的部队,那是驻扎在维尔纽斯附近的一支名不见经传的部队。
那天夜里,助手报告,维尔纽斯的苏军损失惨重。他们的撤退,给进攻明斯克的德军留下了一道大口子。这个坏消息对科罗布科夫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所有的边境部队表现都很差,这让他为自己的部队感到有些宽慰。对参谋人员,他一下子变得友善起来。科罗布科夫告诉他们,如果第4集团军不能马上得到增援,他们还得后撤。此时,第4集团军已后撤至华沙公路,这是通向明斯克和莫斯科的战略要道。现在,科罗布科夫公开承认,仅靠第4集团军,很难守住这里。
科罗布科夫的看法是正确的。
6月27日夜,第4集团军的防线被突破,指挥部只好再次后撤。搬迁后的指挥部也不安全。那天中午,古德里安的坦克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司令部附近。科罗布科夫几乎是跳上车,然后一溜烟地沿着华沙公路狂奔。德军坦克开火了,科罗布科夫的司机设法越过了普季奇河(Ptich River)上的大桥,这才摆脱了德军的追击。他们一过河,科罗布科夫就让汽车停下来,他下了车,命令立即炸毁大桥。他沉着脸,看着士兵把汽油泼在桥上。正当士兵要擦着火柴时,德军的坦克突然就出现在桥的另一端。桥上的火还没有着起来,德军坦克碾碎了桥上的路障,成功地越过了大桥。
那天稍晚些时候,科罗布科夫发现自己来到了博布鲁伊斯克(Bobruisk),这是别列津纳河(Berezina River)边的一座城市。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就是在这里遭受致命打击的。科罗布科夫明白,第4集团军守不住这里。但他还是命令部队占领河的东岸,正好位于博布鲁伊斯克市的近郊。
士兵们把炸药放在一座座桥上,参谋们主张立即炸毁桥梁,以免再出现像普季奇河上的溃退景象。科罗布科夫有些犹豫。
“还在河西岸的部队怎么办?他们怎么过河?”他问道。
“还有渡口和船。”
“这些桥都很重要,也很值钱,”科罗布科夫说道,“我们应该得到方面军指挥部的允许。”
军官们都沉默不语,此时,无声胜似有声。
科罗布科夫感到惭愧。“是的,和方面军指挥部的通信已经中断,”他有些不安地说道,“而且敌人随时都会占领这些桥梁……我授权炸毁它们。”
他忐忑不安地看着大桥倒塌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但至少在目前,华沙公路是安全的。
不久,他们和巴甫洛夫的通信联系恢复了。前线指挥官命令第4集团军驻守在别列津纳河。巴甫洛夫说,第聂伯河沿线的下一道防线还没有建好,因而第4集团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那里。他还要求科罗布科夫明天要亲自向他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