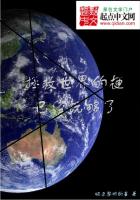十年未变。
一直以来都那样冷漠骄傲的女子,就这样在漫天的白骨劫灰中,毫无掩饰地失声痛哭。
轰隆的巨响继续从高处传来,巨石沿着台阶滚落下来——那是天心月轮被摧毁后、引起的神殿全面倒塌。
一切都摧毁了……无论神力还是恶灵。
今日,是清算所有罪孽的一天吧?
巧儿祭了圣湖,母亲被恶灵撕咬致死,而她的哥哥却在灵鹫山顶,镇压了万世的恶灵。
整个世间,只有她一个人了。
干枯的圣湖一片雪白,那是无数的骷髅和骨架铺满了地面,带着几百年来不见天日形成的幽暗,那些骷髅带着黑洞洞的眼窝、张大了口静默地仰对苍天,那凝固了几生几世的怨毒终于在一刻的尽情宣泄之后永远平静。
最尽端处、那一道万斤闸门死寂的封在那里,阻断了阴阳两界。
神殿还在继续坍塌,不时有碎石落到她身上,然而阿婧毫不闪避,眼睛空空荡荡。
不过幸好的是,月神像上面月神的灵力还在,除了神庙坍塌而已,其他的地方还是完好无损的。
那一个长的可怕的夜终于逝去,天色已经微微透亮。
淡蓝色的天光透过薄云散落下来,那些苍白的劫灰在光里飘转着,消弭毁灭。
我们都是能狠下心来的男人,彼此都能为了自己的想要的东西而不惜一切——但是,唯一牵挂的就是那些会为你哭泣的人。
知道她们即使能洞彻过去未来、拥有举世罕匹的力量,却依然是个女子、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样惨烈的计划——所以,你才会让沈绛带走阿婧吧?
不让她亲眼看见这样的一幕,那便是你所能做的最后的回护。
然而,终究这一切、都还是不得不在我们最不希望看见的人的眼前进行——如今阿婧这样的痛哭、这样的死寂,在幽冥那一边的你、还能感觉到么?
你的心底,是否也会感到一丝的歉疚和绝望?
原来,就算尽了全力,还是有些东西终究无法守护。
天色刚刚蒙蒙亮,苍白一片,天光穿透了那些漫天的劫灰射下来,在光影中,阿婧看见了还留在地面上的护花铃。
那是她哥哥的护花铃,跟自己脖子上带着的是一对,阿婧缓缓拿出自己颈间的铃铛,上面一个刻了“夏”、一个刻了“媚”,兄妹二人,一人一个,此生说好的不离不弃,她的哥哥还是骗了她。
还是走了。
一切都忽然沉寂下去了,天光从云层后透出,丝丝缕缕照射下来,笼罩天地。
那些劫灰依然在空中飘浮着,然而不等落到他们衣襟上,就纷纷在半空的光与影中湮灭了踪迹。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沈绛站在山门外,四顾白骨累累,一眼望不到边际。
眼前是第一次在他面前恸哭的阿靖——而他一个人站在这茫茫的白骨荒原之间,陡然间仿佛有什么极度悲凉辛酸的利剑,一分分刺穿他的心脏。
蓦然感到说不出的痛苦,雪羽楼主捂着心口弯下腰去,却依然不说一句话。
当所有的语言都已经无能为力,他已不求再在她的面前分解一言一语。
在灵鹫山顶听到凫晨合盘托出最终的计划,并开口请求他的援手时,他内心瞬间的震动无以言表——对于一个已经操控天地、俯仰古今的人来说,有什么还能值得他为之付出这样放弃永生、永闭地底的代价?
或者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然,那是佛家的慈悲,却不料却在这样操纵邪术的大祭司举止中真正的实现。
她即使了解了真像,无法再责备他什么,但是心里那样的阴郁却永远不会再散去。
——那将是他们之间永远无法再逾越的鸿沟。
阿婧、阿婧……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这样毫不掩饰的痛哭,放下了一切刺人的骄傲和自卫的矜持,就像一个迷途小孩一般的恸哭。
你的真性情,从未在我面前这样的流露过。
那个人……对你来说很重要吧?
风里不再有那个温柔的声音,只是渐渐远离,消失无踪。
“神女!神女!”出神之际,耳边忽然听到了人声——这一次,是确确实实的有人在叫。
熟悉的声音,那是——?
“神女,祭司大人他......”
“死了......都死了......冥星,我还是躲不过了。”小榭只是占卜到了凫晨的星蕴陨落,但是没想到竟然是真的是冥星照名,交合的一切都不得好死。
眼神冷凝,忽然,右手中刀光一闪,左腕中已被割了一道,殷红的血一滴滴急速渗入圣湖地底的泥土,沈绛仰头苍天,一字一字对着天地说出誓约:“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沈绛在此立誓:有生之年,听雪楼人马不过澜沧。”
听到这话,阿婧只觉得可笑,人已离去,再立誓还有什么用呢?
眼前白骨森森,天高地广,然而阿婧忽然间不知该说什么。
阿婧站在神殿里,手指间握着一片镶嵌着蓝宝石的玉石碎片——那是天心月轮的残片,如今灵鹫山上月沉宫倾,神殿坍塌圣湖枯竭,一切,仿佛都是末世般的景象。
当神已无能为力,那便是魔渡众生。
那一句话,她在大祭司书房的一个神龛上看见过,如今,她才明白其中的深意。
即使化身为魔、也要渡尽众生——凫晨、或者说息止夏的心里,居然还有这样隐秘而坚定的愿望。
漫地的悲苦中,只有这个阿婧的眼眸是明净的,那是没有经历过真正幻灭和复生的婴儿的眼睛,纯白得有如那朵梦昙花。
“神女,就这么放他们离开吗?”
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是她母亲给她的最后的忠告!
可是拜月教今日的耻辱,今日的遭遇,雪羽楼就当真不留下些什么吗?
“什么独步天下、无上灵力,即使有了这些又如何?那样睥睨的一生、最后还不是难逃那一日——哥哥就是最好的明证了。”
然而沉默许久,看着如血的夕阳,沈绛的声音却是萧瑟的:“从未开始,何谓完结?”
回去吧——
中原大举北上返回洛阳,沈绛在离开的最后一刻,还是忍不住回头望了望,他的阿婧,他的妻子,永远都不会跟他回去了。
暮色笼罩大地的时候,圣湖底上却是一片火光,宛如红莲盛开。
夜色里,那些火堆宛如一朵朵莲花。
焚尽三界邪恶的红莲烈焰。
教中子弟尚未从悲痛中恢复,而小榭却已经赶来,站在火堆旁,默默念起了超度经文。
阿婧一袭白衣如雪,火炬明灭映着她苍白清秀的脸,眉间的神色却是复杂的看不到尽头,怔怔望着那一堆堆的白骨在烈火中焚烧为灰烬。
夜风吹来,绕着火堆旋舞,有片片的飞灰吹到人脸上,宛如劫灰一闪而灭。
——这其中,有无母亲宛然长逝、湮灭入轮回的芳魂?
原来,一切,都不过如此而已……都不过如此而已!
“教中没了教主和祭祭司,还情请神女能够主持大局。”
将火把扔入最后一个白骨的堞堆,阿婧再也不看那些死去的骨殖一眼,回首对着小榭招呼,眼神冷冽,“白曛.....命号,白曛。”
她已经不能够为她自己活了。
有一滴热血,从额角流下,淌了很久很久,才划过她清丽苍白的脸颊、停在腮上,在晨曦的冷风里渐渐冷凝如冰。
“出发。”拨转马头,雪羽楼主冷然下达指令,马蹄声得得响起,人马开拔。
离开灵鹫山。离开南疆。离开这片碧蓝天空下、纷乱的过往一切。
然而,在头也不回地领着队伍离开的时候,心里却有深入骨髓的痛意,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丝线、将他的心生生系在了这里,每策马离开一分、就被血淋淋的扯裂开一分。
“陡彼高岗,汝剑铿锵。
“溯彼深源,草野苍黄。
“上呼者苍,下俯者莽。
“汝魂何归?茫茫大荒!”
“……”
隐约间,听到有歌咏之声从灵鹫山顶的云雾中飘来,悲凉凄切,仿佛回声一般缥缈不可琢磨,一阵一阵随风吹散入耳畔。
沈绛猛然勒马,回首看向隐入云中的月宫——那是…那是拜月教子弟,在为死灵唱挽歌祭奠?
“呼彼凫晨,其音朗朗。
“念彼肢干,百热俱凉。
“岁之暮矣,日之夕矣。
“吾欢吾爱,得不久长?”
“……”
果然。
果然是凫晨的葬礼吧?只是这样的歌词,深味其中哀苦悲凉,又是出自于谁之手?
那朵蔷薇,命运的纺锤?
——然而那人心丧如死,目前应该依然几不可思想和行动,又如何能再执笔写出这样的挽歌……
想及此处,他的手几乎握不住缰绳,在天风浩荡中,黯然策马北归,耳边那诵唱的声音如缕不绝:
“水色深瞳,已敛已藏。
“招魂不至,且玄且黄。
“上仰者苍,下俯则莽。
“岁月淹及,失我迦郎!
“岁月淹及,失我迦郎!”
永失所爱……然而,死别比之生离,又不知那个更为残酷?
但在他们离去的瞬间,有琴音绝壁而来,前方的路被震起,马嘶,一片混乱。
右无数灵蝶出现在他们面前,徐徐晃晃,渐渐清晰,直到看清楚来人之后,凫晨才懂了最后一刻的心思。
“你们当我拜月教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那个刹那,他忽然觉得无法呼吸。
“阿婧,最近的事情都是我的意思,你要是想报仇,找我就是,不要滥杀无辜”
“无辜?你也知道什么是无辜?”
“阿婧,你哥哥的事儿.....”
“不要叫我阿婧......你的阿婧,在你选择花溪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了,你听清楚了,我是拜月教的白曛教主,名号息媚允!”
这一刻起,她真的是做回她的拜月教主,不再是中原人,不再是沈绛的妻子,一切从头开始。
“母亲告诉过我,冤冤相报何时了,让我不要报仇......可你们当真不给我一个说法吗?”
不知道是勉力压抑着内心什么样翻腾着的情绪,阿婧缓缓拿出袖中的冰弦剑,这把冰弦剑杀人无数,早就已经不是什么好的神兵利器了。
包括她的哥哥也是死在这把兵器之下,哪怕是血契,哪怕是逆反,她也宁愿毁了它。
只是瞬间,阿婧手中幻化的红莲圣火就将那把剑化为齑粉,在场的无数人都看在眼里。曾经的人中龙凤,曾经的湮祭冰弦,拜月教一一之后,永远的失去了。
“我把东西还给你......今日起,澜沧为界,你我南北不再往来!”
阿婧将头上的凤钗拔了下来,那是沈绛成婚那日送她的东西,包含了他们曾经十六年的光阴和青春的回忆,难道真的回不去了吗?
在沈绛正准备接住的时候,阿婧的身体渐渐虚化,灵蝶开始飞舞起来,沈绛还没有拿到那支朱钗,阿婧便已经幻化成了灵蝶,那只簪子也徐徐落在了地上。
曾经的一切,现在终于浮烟,再也回不来了——
——想来,回去正好是洛阳鲜花盛开的时节,然而那样的繁花和繁华,在他看来却已是死灰。
南疆天高云淡,碧空如洗,透出一种奇异的鲜艳的蓝色,风里有落花和歌声。
他策马缓缓而归。
拜月教大祭司死了,神殿毁了,圣湖枯了,白骨成灰,母亲解脱……他所有出征的意图都已经得到了满足,一切仿佛都已经圆满。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或许这句话,永远停留在了他们成婚的那一刻,再也回不去了。
然而,有谁能知道他在这里输掉了什么?
他终其一生想守护的东西、却最终如同指间流沙一般划落无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