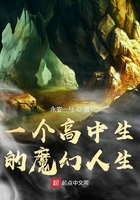蜀郡-月拾城
“王爷,晨间门口来了个乞儿,说是要将这封信交给王爷,门房初里没在意以为又是什么不入流的把戏,方才属下出门听他们说起,便多看了一眼那信,”近侍黄正递过来的信,打断了黄子砚的回想。
月娘接过信,一转身又坐回他腿上,把信往他面前盈盈一递。
那信的左下角有一处小小印痕,这印痕七位郡王都很熟悉,这是歃血堂的令印。
歃血堂是个神秘的杀手组织,在江湖上势力颇大,做些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买卖,顶级的杀手好比墨白、藤、丝线、红绡几个,都是江湖上响当当令人胆寒的名字,没人能说出这几个人的样貌,见过的人皆是死的不能再死了,现任堂主只听说是姓李,更是仿佛只是个姓氏摆在那里,不存在一般。
只有大宣最高处的几个人知晓,李堂主真实存在,而这个表面上的江湖组织,事实上直属大宣最高姓氏楚家。
知道归知道,黄子砚也没有真正见过这位李堂主,可能这世上,也就只有皇帝陛下一人知晓此人究竟了。
黄子砚盯着那个小印看了一晌,慢慢拆了信。
“若已定夺,便有一晤。”短短一行,却是那位李堂主的做派。
“云间舫收拾一下,三日之内不做生意了。”黄子砚交代黄正道。
黄正领命去了。
黄子砚松开搂着月娘柔软腰肢的手,勾了勾美人小巧的下巴:“我见个人,你还是不见的好。”
月娘小嘴一扁:“是甚么人奴见不得?”
黄子砚笑着刮了下月娘的鼻子:“据说见过这人的都没什么好下场,我就罢了,月娘可值得一个好下场。”
-------
息郡-琅环城
“星天。”苍老的声音从空旷大厅的四面八方传来,男孩微微缩了缩脖子,抬起脑袋四处看了看,最后眼神定在头顶的那一小片仅有的夜空。
这是一座很高很高的塔,塔的最高处是用这世间最通透的琉璃砌的,此时琉璃里的那一片夜空里漆黑一片,没有一颗星星,映得男孩墨黑的一双眼瞳更加沉寂。
“我很老了。”苍老的声音又道,“好在在我死之前,息家总算又出了一个墨瞳子。”
男孩转而看向大厅深处,依旧是漆黑的一片,看不出有没有什么人在那里。
“你是谁?”男孩问。
“我是谁?”苍老的声音似乎有了些慌张,“我是谁?我是谁?”他不断重复着,回声在大厅里来回碰撞。
“我记不得了,我太老了。”苍老的声音最后说。
“你认识我?”男孩又问。
“息家的墨瞳子,你的眼睛,不要只看向这片天下,这天下太小了,你要看的东西,在头顶上,这星野,星野之外的那个天下。”苍老的声音说。
“我见过那个天下。”男孩说。
苍老的声音哈哈大笑起来,笑了很久很久,久得男孩觉得他这辈子都不会停下了。
但是男孩没有动,他依旧看着漆黑的大厅深处。
“你要回去了么?”很久后男孩又问。
大厅里的笑声戛然而止,接下来是长久的安静,就仿佛这里从没有什么人一样。
男孩往前走了一步又问:“你要回去了么?”
依然没有回答,男孩墨黑的眼瞳深处动了动,他忽然跑起来,在大厅的四处奔跑,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最后他什么也没有找到,这座塔里只有他一个人。
男孩默默走回大厅中间,抱膝坐下来。
今夜之后,他是息星天,却也不再是息星天了。
-------
蜀郡-云间舫
云间舫是名副其实的云间舫,它是一条天上的画舫。
它原本是山谷里的一根擎天石柱,山谷终年云谷缭绕犹如仙境。相传前朝有两位建造匠人相约比试,其中一位看中了这绝妙的地形风貌,在石柱顶端打造了这座石舫。
舫体以整块巨石雕凿而成,全长127米,舫上建有三层木楼,皆以金漆覆之,顶部为砖雕装饰,造型奇特,与前朝的飞檐斗拱都有所不同,极尽精巧华丽之能事。
通往这座石舫的只有石柱壁上一条盘旋的石阶,常年隐在雾中,因此远看这石舫,仿佛是悬浮在山谷云间的一条小船,故名云间舫。
云间舫位于月拾城外三十里,所在山谷入夜后便有瘴气,建成后仅是那位匠人独自居住,少有探访者,匠人去世后便荒废了。
到了大宣天府年间,上上代蜀王也就是黄子砚的爷爷将云间舫重新修缮,石阶皆以理石覆盖并完善了围栏扶手,加固了石舫结构,重新装饰了石舫内部,用以收藏及售卖古字画,故有“云间舫画中有仙“一说。
云间舫有最好的字画鉴赏大师,收藏的皆是顶级作品,是天下古字画爱好者的向往之地,但画作标价却令寻常人望尘莫及。
而舫里不定期举办的拍卖会却反其道而行之,简直是给机会捡漏,画作经常是一个铜子起拍。
用黄子砚爷爷的话来说,当真让你一个铜子拍走,那便是此画与你有缘。
此时云间舫的天字一号师傅正站在船头看着脚下万丈云海皱眉头。
云间舫不问出处,只要通过入舫的测试,便能尊称你一声师傅,给你一个牌号,此后便舍弃之前的名字和身份,忘却前尘往事,终身服务于云间舫。
没人知道天字一号师傅的真实姓名,也没必要知道,单看牌号便能瞧出这位在云间舫的身份地位了,意外的是此人看起来年纪却并不大,皱着眉头的样子似乎还带着点孩子气。
天字一号师傅今日心绪不佳,本来约好今日要收上舫来的一副据说是两千年前贲朝的古画,因为蜀郡老大的一句话云间舫歇业三日,鬼知道三日后那画儿又流落到哪里去了,怕是日后再无缘相见了。
想到此处,天字一号师傅的眼里竟是雾蒙蒙的盈满了泪水,他狠狠吸了吸鼻子,倔强的盯着面前云海,就好像他身后并没有站着什么人一样。
黄子砚讪讪的摸了摸鼻子,话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此人两头儿也没沾着什么边儿,却是没见过如此不好商量的人。
“豆豆。”黄子砚耐着性子又叫了他一声,“今日若是顺利,明天云间舫便正常开张可好?......”
“入云间舫者无姓无名无前尘往事,王爷该称在下为天字一。”没等黄子砚说完,这位叫豆豆的天字一号师傅便生硬的说道,话语里竟还带着些鼻音。
黄子砚走上前去与他并肩而立,天字一赌气转过脸去,黄子砚看着翻滚的云海叹了一声:“你要忘便忘了吧,只是今日之后蜀郡的太平日子也没剩下多少了,我还能保得了云间舫几日?我知道有人来找过你,也知道你那九头牛拉不回来的倔脾气,我只提醒你一句,若以后有一日蜀郡再不是黄家地盘了,你就尽快将那画处理了吧,人都不在了,你留着个空屋子还能等回来个什么?傻不傻。”说到此处黄子砚抬起右手呼噜了下天字一的头发。
天字一偏了偏头也没躲开黄子砚的手,犹豫了一晌,最后斜着眼睛看向黄子砚:“你什么意思?”
黄子砚却是转身摆了摆手说道:“你要的那幅贲朝的古画,我已派人盯着了,明后日我回雍都了,自有人带他上舫来找你。”说罢慢悠悠的离开了。
留下天字一独自站在船头,眉头皱的更深了。
-------
昨日上得舫来,今晨先生便吩咐她除了脸上人皮面具,楚泝兀自对着镜子发了一阵呆,额角花苞状的红色胎记活灵活现,似乎要破了皮肤直接长出来似的,像是见了什么极度厌恶的东西,女孩猛地合上镜子。
平复了一阵,门外传来整齐的三声扣门声,这是墨白扣门的声音,永远规规矩矩不慌不忙。
楚泝站起身来,又想起什么似的拉过镜子,用额前的碎发徒劳无功的遮了遮那胎记,最后没奈何的一叹,起身给墨白开了门。
她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那胎记上,这让楚泝心里稍舒服了一些,墨白和平时一样平静的看着她的眼睛,淡淡说了句:“走吧。”
这云间舫是楚泝第一次来,事实上她有生之年都没走出过王域,父君常说她身体不好,不能远游,十五年来她皆是乖乖的呆在那几个地方,看着那几个人。
但是几个哥哥还有阿芷都经常和她说起外面的世界,提起大宣广阔疆域里的名山大川、风物人情,她一直心向往之。
此番跟着李先生出得王域,有的地方兵荒马乱,有的地方遍地焦土,似乎与哥哥和阿芷说的风光霁月出入甚巨,但月拾城却是与他们描绘的一般无二,这座城和这城里的人,皆是如皎皎月色般美好,若能终老此处便好了,楚泝不禁想。
离开她住的小间,穿过一条古朴的走廊,墨白领着她进了一处小厅,小厅陈设很简单,细微处却见主人的品味,便是随意小几前两个蒲团的麻布罩子,细看之下竟是当代著名画师叶卿老师的手笔。
据说叶老师画虽妙,脾气却甚坏,曾经因为妻子递给他作画的毛笔分了岔,就留了一封和离书,愤然出走大半年不见踪影,能让他情愿为两个蒲团罩子填笔,几乎可称上一句天方夜谭。
那蒲团楚泝是不敢坐的,看着厅里也无其他人,便踱步看起墙上的画来。
不愧为云间舫的会客厅,楚泝心里叹道,这一眼望去,历朝历代的名作琳琅满目,曹学的《豫川狂雪图》,薛为的《青冥》,那幅左向尧的《池中窥》是她父君也百求不得的名作,究竟是在这里了。
看画讲究“观纸、看印、究题跋”,说的是要鉴赏一张古画的真伪价值,要先观察作画所用的绢或纸,再看古画上留的章印,最后研究或是作者本人或是后人鉴赏的题字,但楚泝向来颇不以为然,觉得这一套规矩简直本末倒置,在她看来,一张画是真是假并没有多重要,很多仿作或是代笔的作品水平甚至要远远高于原作,只要能给观画者带来或美好、或悲伤、或愤懑等等心灵上的冲击和体验,那便可称一副上上佳作了。
楚泝随便走了走,最后在一副奇怪的画前停下脚步,这画上空空如也,只在左上角有两行小字,题的是“色授魂与、心愉一侧”,题字旁依稀有一方鲜红小印,挂的高了,以楚泝的身量尚看不清楚。
“是不是很奇怪,这画上不着一笔,竟比旁边那些千万笔描摹出的名作震撼千万倍。”悦耳的男生在她背后响起,楚泝惊了一跳,回头打量,见是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男子,一身简简单单的白麻袍子,看着画的样子有点发痴。
“失礼了。”意识到自己不该注视个陌生男子这许久,楚泝垂下眼睛半侧着身子行了礼。
“无妨。”男子的目光始终没离开过墙上的画,“我看你在这幅画前站了这许久,便多嘴了。”男子也行了礼,“在下是云间舫天字一。”
“原是先生。”楚泝再行了一礼,“月息叨扰云间舫了。”
男子哼了一声:“来的是客,既是黄家狐狸吩咐的,月姑娘是上舫买画还是卖画啊?”他的目光终于从画上移到楚泝脸上来,先是一愣,随后这位天字一先生哆哆嗦嗦的举起手来指着楚泝颤声问了句:“你是谁?”
“天字一先生你且旁边稍坐吧。”没等楚泝回答,听得厅门口有声音传来,带着些促狭的笑意,但见白色广袖一跹,那声音道:“李堂主里面请。”
楚泝见李千袭进得厅来,依旧是面无表情的瞥了她一眼,随后进来一名大约三十年纪的男子,面白无须,嘴角一道浅浅疤痕上挑,似乎随时都是一脸挑衅的笑意。
那男子进门见了她便行了大礼:“臣黄子砚拜见泝殿下,请殿下金安。”
“蜀王请起吧,楚泝一介庶民,当不得郡王一拜。”楚泝道。
“你你你,你是......”天字一仍旧是哆哆嗦嗦的道。
黄子砚没搭理他,请楚泝上座,亲自看了茶。
其余一一落座,墨白仍是门口一靠,一双美目看着门外某处,不知是在看什么。
“今日公主没戴面具,说真的本王很意外啊。”黄子砚道。
“蜀王让天字一先生作陪在侧,李某也很意外。”李千袭道。
黄子砚一笑:“很公平了。那本王便不和李堂主废话了。”他押了口茶,继续道,“元家毁了,青郡估计已经让李堂主彻底失望了,西南息、商、阑三郡想必李堂主心中有数,早就是我黄家的人了,因此黄子砚斗胆和李堂主谈一笔买卖。”
李千袭淡淡看着他并未说话。
“黄家可以是公主的人,蜀郡一切资源也可为公主所用,但黄家是生意人,祖宗交代,可不能做赔本儿买卖,因此本王有一个条件,”黄子砚眯起眼睛,“只要殿下和李堂主能北上说动氿郡那头狼,四郡就皆为公主马首是瞻。”
“慕容岳应该早就找过你。”李千袭说。
“本王对那些个神话故事没什么兴趣,在世一生,不过是桌上押注,有利可图而已,”黄子砚呵呵笑了,“况且黄子砚年轻时在殿上对老陛下说了些昏话,虽说黄家从没有青郡那些忠君爱国的情结,但丈夫一诺,总还是得负些责任。”他下意识的用右手拇指抚着嘴角,“李堂主不必信我,只当是买通了本王就是。”
李千袭喝了口面前的茶:“虾子的船何时启程去氿郡?”
“月前就备好了,随时可以走,”黄子砚道,“但是殿下得先去趟琅环城,”黄子砚撇了撇嘴,“虽说本王不信这些,但姓息的日前给本王写了封信,请殿下务必去一趟。息家的人向来神神秘秘,不过有时还得多听他们一句的好。来回不过三四天,天字一路熟,他陪你们一道去。”
忽然被点到名的天字一一脸震惊的站起身:“我去?”
黄子砚翻了个白眼:“那不然我去?”
“甚好。”李千袭说,说完起身飘然离开小厅。
楚泝看着李千袭的背影,在心里默默记下一笔,尴尬的站起身向黄子砚道:“那楚泝也不打扰了。”
“殿下此去琅环城,务必要说服息星天随你一起北上氿郡,那家伙十分懒,轻易难得离开息郡,能否说动他,就凭殿下本事了。”黄子砚笑着说。
“我上次见你,你还是个小娃娃,”话锋一转,他忽然道,“我殿上说了那昏话,下来老陛下却独召了我去禁宫,我还当是要问我的罪过,当真吓得不轻。”黄子砚嘿嘿笑道,“你幼时不太好近人,我只远远看了一眼,十分可爱喜人。”
楚泝看着黄子砚的脸,这张脸上此时笑容温暖,看不到一点算计。
“你受苦了,”她听见黄子砚轻轻说,“这天下本不该你担着。”
云间舫外云海舒卷,晨间的烟气渐渐散去,金色的光先是跳跃在云朵的缝隙里,倏尔穿透了这世间所见洒满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