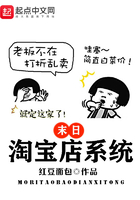洪河村是个不算太大的村子,常住人口大概三千人左右的样子,这里环山绕水,景色十分宜人。而关于村名的由来,村子里历来有很多种说法:有说是截取了一个其他地方一个地名,有说是早年间村子发洪水淹没了整个村子,洪水退后,这里才逐渐的又有了些居民重新居住等等。但在众多纷繁复杂的说法中,有一种说法却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据说早年间,大概也就是抗战前期吧,具体时间也无法考究了。村西岭上面有一片林子,很是茂密,那时候的土地还没有实行责任承包,到处都是荒山野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比较出名的是酸枣叉和野石鸡。相信生在黄土高原一带或者是居住在北方的一些朋友都知道酸枣这种野生植物,它和家枣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核比较大,但皮肉却比较少,确实令人很郁闷,所以它的食用价值远远比不上家枣,当然也有另类几乎可以媲美家枣的那种,我们这称之为‘大青枣’,却不是说那种还没有熟透的家枣。而野石鸡就是野鸡,就是漫山遍野到处乱跑整天‘咕咕达、咕咕达’乱叫的那种,还能像鸟儿一样进行短距离的滑翔。
而且见人就朝它居住的地方相反的方向跑,以保护自己的家园和雏儿,这种野鸡的肉相当可口,而且营养丰富,是大补之物。呵呵,当然前提是你能抓住它们。这个不用解释。上面说了,村西岭上有很大一片林子,如果小孩子误入其中很容易迷路,那时候家长吓唬不听话的小孩经常这样说:再不听话把你扔到西岭的树林里,小孩子马上就吓的不敢言语了,可见其杂乱的程度。林子的深处就有一株很大的酸枣“树”姑且称之为树。因为大凡酸枣这种野生植物一般都是以叉的形式存在,年长一点的可以长成儿臂粗细,称之为藤。而如果能担当的起‘树’这个称谓的,大概全村乃至全县甚至全国有可能就只有这一株了。它的直径大概有三尺左右,需要两三个成人才能合抱的过来,也不知存在了多少年月了。据村里的老人讲;这树是有灵性的,它能保佑全村的平安,五谷丰登。那个时候,老人们的话是很有威慑力的,因为但凡长者都是智慧和经验的象征,所以一直以来,那颗树都被村里的人敬若神明,以至于逢年过节都要上香叩拜以祈求平安。但世事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俗话说的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就是这样一株被村民敬若神明的吉祥物,有一天有人居然拿着斧子去砍树!这不是顶风作案么,这不是对神灵的亵渎么,这不是不把全村人的信仰放在眼里么。于是村民们愤怒了,呼应着相继赶来,质问的,谩骂的,呵斥的,有几个村民当场将他的斧子夺了下来,一脚将他踹跪在树下。砍树的人村里人都认识。姓胡,30多岁。生的煞是魁梧,因在家里排行第二,大家都称他他为胡二。当问及为什么砍树的时候,胡二声俱泪下:“我娘病了,很严重。罗婆婆说只有用这树的树皮做药引研制成药才能救我娘。我也是万不得已才来的,你们也知道。我爹和我哥死的早,家里就我和妹妹,我娘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我希望这时候能为她做点什么,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希望,不然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村民们沉默了,罗婆婆是村里岁数最大的人。今年已经96岁。这还是其次,据说她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跟一道人学过7年时间的道法,后还俗,一身本事神鬼难测,药理测命驱鬼抓妖无所不通,据说已到了近神的地步。村里什么大小决定,红白喜事几乎全都请她拿主意,就连村长都敬她三分。
这样一个人说出来的话能有错么?更何况胡二说的合情合理,农村人都特别注重孝义,此刻胡二一番话说出来,全场的人都沉默了。最后村长站出来,村长是一名70多岁的老者,佝偻的身体,满是褶皱的面孔,拄着一支杨木拐杖,上面镌刻着一些奇怪的图案,象人鱼,象飞鸟,更象稀疏的丛林下洒下的斑驳的残阳光:“让他砍一点吧,救人要紧,但只是一点,明白么?哎……”“谢谢村长,谢谢村长,谢谢大家。”胡二站起来忙不迭的给大家鞠躬,而后拿起斧头照那颗酸枣数砍了下去,“锵‘斧头落处,却仿佛砍到了极为坚硬的金属,震得胡二的虎口都发麻了,但树身还是被砍出了一道口子,胡二没有停息,继续举起斧子准备一举将这块树皮砍下来,但他举在空中的手却突然停住了,惊愕和惊恐的表情挂在他的脸上,一瞬间他的脸变的苍白,冷汗不断从他两鬓渗出。这时。大家也都惊恐的注意到了:只见树身之前胡二砍出的那道裂口正在汩汩的往外流出树液,如果只是这样倒也罢了,只是那树身体流出的液体竟然是淡淡的红色,仿佛被稀释了的人的血液!“哗”的一声人群全都跪下了,胡二更是吓的斧头掉地上都没发觉,随后也随人群跪下去。
村民们都认为这是触犯了神灵,马上就要有灾难降临到村子了,于是都不断祈祷在祈祷;大仙莫怪,小人们愚昧无知,求大仙原谅,求大仙原谅……村南坡至高点的一间小草房里,此时烟雾缭绕,细看之下,只见屋里供着一张八仙桌,桌上点燃了16注香,香火断断续续的燃烧着,上面的香灰也拉越长,却始终不肯掉到下面的香鼎内,这一幕煞是奇特。旁边端坐这两个人,一脸肃穆的紧紧盯着香火。终于,‘啪嗒’一声,一束香灰掉落在了西南方。“罗婆婆,这个该怎么解释?”问话之人却是坐在一边的村长。“西方主大吉,南方主大凶,哎,看来是上天注定的,我王家后代依然破不了那个诅咒啊,不过从香火的燃烧阵型来看,这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吉凶之间,充满了变数,一切全看他的造化吧,但愿他们今夜不让我失望。
”“娘,你真打算把他们……”“混账,说过多少次了,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叫我那个称呼!我不是你娘,你现在难道还不明白么?“可是……”“没有可是,为了我们王家的香火气运,我也不得不做出一些遭天谴的事了,但愿你那老不死的爹泉下有知,能理解我的一片用心啊,哎,现在说这些干什么……”罗婆婆看向香鼎内相继落下的几束香灰,脸色异常肃穆,眼睛里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仿若洞穿眼前的一切,进入一个别样的空间一般,一边缓缓起身走近香鼎双手合十虔诚的祈祷:“诸神保佑,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保佑我王家后代能早日走出那个诅咒……”“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破解那个诅咒么?难道非要用如此残暴的方式来换取我家族的平安,您有没有想过,这样我们心安么,我们的后代如果知道他们的幸福是建立在这样的方式之上的话,他们该作何感想呢?那个什么五代之内必出贤士的预言如果真的是他说的,那我们又何必多此一举呢?难道仅仅就是因为那一点家族的气运和那不知道存不存在的什么狗屁诅咒么?况且这样做也不见得就能够破解得了那个诅咒!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村长情绪开始激动,村长就是村长,什么事情都为大局着想,从点滴考虑,他是个称职的村长。“一将功成万骨枯,大丈夫成就大事从不婆婆妈妈,该牺牲就牺牲,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你就是不明白,你别忘了,如果不是我,你现在连村长都做不了,就你那点妇人之仁迟早害了你!其实从一开始我知道这样的结果,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尽可能的改变这个结果,打破这个宿命,往大了说,是为了全村,往小了说,是为了我们王家的后代子孙!只要我们家族兴旺了,全村乃至全县都跟着沾光你懂么!”罗婆婆情绪开始激动,浑身都颤抖起来,语气也越来越激昂。“如果我的老师现在还在的话也许情况会好点,该死的,都是当年那场赌注,害得我们家十代之内动荡不安,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应该阻止师父拿我们全家的命运去和那老不死的较劲,你们什么都不懂,哎,这些年我容易么。我一妇道人家却比你们大老爷们抗的担子还要重,你们没有为我想过,一直以来,我默默的为这个家付出,我不求什么,只要你们活得好,只要我们的后代活得好。”罗婆婆哽咽了,村长沉默了。是夜,本来月朗星繁的夜空突然几声炸雷凭空响起,惊动了村里所有人,但由于是腊月寒冬,大家都躺在暖烘烘的被窝里,所以倒也没有人起来看看是什么情况。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上山砍柴的老黄头路径神树突然发出歇斯底的喊叫:“快来人啊,出事了快来人啊天呐”村民们起的早的纷纷赶了过去,等村民们走近一看,却被眼前的情景吓懵了——树下横七竖八的躺着五六个人,浑身是血,景象惨不忍睹,有人眼尖,一下认出了那几个人不是后山上的那几个令村民谈之色变的‘草寇’么,其中居然也有胡二!其实说是草寇过分了点,其实都是被生活所迫而致的一些外乡人,虽然平时没少打家劫舍,但基本没怎么伤害过村民,所以严格来说他们本性也算不是太坏,而此时突然一下以这种方式出现在这里,多少有点令人费解和心惊。“哎,人心不足蛇吞象,善恶终有报,他们亵渎神树,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也算报应……”不知什么时候,罗婆婆出现在了人群中,人们自动分出一条道给罗婆婆走上前去。罗婆婆看了看躺着的几个人,又看了看树,无奈的摇了摇头。人们顺着罗婆婆的视线看向那颗神树,只见好好的一个树此时居然从中间裂开了好大一条缝,象是硬生生的被什么东西劈开一般,而树的端部更是其刷刷的少了一根巨大的分支。断面平整,像是被什么利器一下干净利索的削断一般,淡红色的树液不断的涌出来和地上几个人的血液混合在了一起越积越多……罗婆婆抬头望天,喃喃自语:“天要哭了,人也要哭了。”村民们疑惑的望着她,良久之后,罗婆婆步履蹒跚的离开了现场,而就在此时,天空一个惊雷,仿若亘古不变的大自然定律,乌云霎时凝聚在了一起,大雨瞬间滂沱而下。天,终于哭了,大雨混合着泥土混合着树液混合着鲜血,奔腾而下,席卷了整个村西岭小路,最终分散于田地间。那景象震撼了所有村民的心,村民望着那红色的河流,喃喃自语:红河,红河……历经多年岁月沧桑洗礼,因‘红河’这个村名过于单纯直白,很容易勾起村们那可怕悲惨的回忆,红河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洪河——洪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