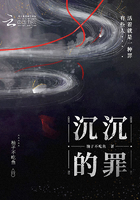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沙扬娜拉》
他怀念“那一低头的温柔”,他以为他找到了,并且一生都会拥有,到头来却发现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但是他不会承认,因为一颗赤忱的爱人之心献出去就不可能再收回,他到底是爱着这个任性妄为的妻子的。
轻易希冀轻易失望同是浅薄。
费了半个钟头才洗净了一支笔。
男子只有一件事不知厌倦的。
女人心眼儿多,心眼儿小,男人听不惯他们的说话。
对不对像是分一个糖塔饼,永远分不净匀。
爱的出发点不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一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
——《爱眉小札·日记》1927.1.6
作为一个丈夫,看着妻子与别人暧昧不清,外面流言蜚语早已铺满了整座城,亲朋好友忧心忡忡,父亲已决意与他撇清关系,不再提供经济上的资助……这一切令他身心俱累。更心灰意冷的是,创作灵感的枯竭。但即便如此,他亦没有在口头上责备质问过妻子,顶多是将自己关起来,一腔愤懑与伤感隐晦地发泄在日记当中。
他对陆小曼的容忍与放纵比之第一任妻子的挑剔与偏见来,真是天壤之别。他以前嫌弃前妻是“乡下土包子”,如今娶了个十足十的新潮女子,他又不堪重负起来。这算不算是自讨苦吃?
“爱是建设在忍耐与牺牲上面的。”
志摩也知道,他不可能用一个封建专制的丈夫角度来看待整件事。何况,他自诩新派,又留洋欧美,信奉西方的一套绅士做派,他自己也是绅士,绅士要大度、谦和、礼让,最重要的是疼爱并且体谅妻子。这一切,他都做到了。但陆小曼根本不在意,或者说她故意忽视了志摩的用心。她的心中一直憋着气,从嫁进徐家伊始,徐家长辈就没有正式承认她媳妇的身份,在吃穿用度上一度苛刻至现在彻底断绝。她从内心嫉妒张幼仪,她虽然不再是徐家的媳妇,依然享有媳妇的地位与权柄,反之,她这个明媒正娶的儿媳算什么。
陆小曼的叛逆与骄纵致使她不会隐忍婉转地博得徐家的接受,反而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与封建古板的大家长较量——花钱,拼命地花钱。她自己本身出手阔绰,再加上有心为之,不久没有给徐家起到示威的作用,反而苦了夹在中间的志摩。他每个月至少开销五百大洋,而当时的人均年薪不过五块大洋。
如此还不算。当时据闻有一个恋慕志摩的女学生,早在他在北京教书时就已经芳心暗许,直至志摩与小曼结婚,迁居上海,她仍不死心。这个女学生叫俞珊,当时有过这样一段记录:
有俞珊者,健美大胆,话剧修养很高,是余上沅的学生,她崇拜志摩也崇拜小曼,她为演《卡门》,常住徐家,向志摩请教。……志摩是无所谓的,小曼却说她肉感,论俞珊却有一种诱人的力量。因此,小曼常和志摩吵。志摩说:“你要我不接近俞珊很容易,但你也管着点俞珊呀!”小曼说:“俞珊是只茶杯,茶杯没法儿拒绝人家不斟茶。而你是牙刷,牙刷就只许一个人用,你听见过有和人公用牙刷的吗?”
当时俞珊来上海,先找到老师余上沅参与话剧《卡门》的排演活动。这时候,志摩已从原来的环龙路花园别墅11号移居到了福熙路613号,他在新居接待了阔别许久的学生。
俞珊的来访给这个原本沉闷的家增添了一丝活力,不料却引起女主人的不满。她觉得这个女学生别有意图,暗地里很是吃味。她是千金大小姐惯了,见不到有人比她娇,比她年轻气盛,更见不得有人当着她的面与志摩亲近……向来好胜的她,再一次不顾是非地与志摩争吵起来。
他们不是没有过温馨快乐的时刻,缘何如此短暂呢?他曾与她合写剧本,《卞昆冈》,希图将她从纸醉金迷的堕落世界拉回他所向往的纯净家园。但是她却不理他的苦心,反而处处表现得咄咄逼人。他的“爱、自由、美”的理想一旦碰到冷冰冰的婚姻牢笼便化为了一团泡影,抓也抓不住。
是春倦吗?这几天就没有全醒过,总是睡昏昏的。早上先不能醒,夜间还不曾动手做事,瞌睡就来了。脑盘里几乎完全没有活动,该做的事不做,也不放在心上,不着急,逛了一次西湖反而逛呆了似的。想做诗吧,别说诗句,诗意都还没有影儿,想写一篇短文吧,一样的杂,差些日记都不会写了……
难道一个诗人就配颠倒在苦恼中,一天逸豫了就不成吗?而况像我的生活何尝说得到逸豫?只是一样,绝对的苦与恼确是没有的了,现在我一不是攀登高山,二不是疾驰峻坡,我只是在平坦的道上安步徐行,这是我感到闭塞的一个原因。
——《爱眉小札·日记》1927.4.20
身心疲惫的志摩感到,再在上海这个“销金窟”待下去,不但救不了小曼,反而连自己也要搭进去。本来,他心里有出国的打算,像康桥、翡冷翠这样风景宜人适宜居住之地作为他和小曼以后的爱巢再好不过了。他尝试说服小曼,与他一道出国定居,无奈,小曼怎么也不肯答应。她在上海住惯了,这里有她奢侈的寓所,有她纸醉金迷的夜生活,有她终日缠绵的烟塌,还有一个日日相伴不离不弃的“蓝颜知己”,她凭什么要放弃呢?
志摩见说服不动,便想独自一人出国散心。他写信给泰戈尔的助手恩厚之:“我哪一天不想往外国跑,翡冷翠与康桥最惹我的相思,但事实上的可能性小到我梦都不敢重做……只是叫我们哪里去找机会?中国本来是无法可想,近来更不是一个世界,我又是绝对无意于名利的,所要的只是‘草青人远,一流冷涧’。这扰攘日子,说实话,我其实难过。”
说到底,他是为了逃避如今国内的困境,想到国外走一走,寻找新生。他不可能抛弃陆小曼,正如当初他们爱情遇到最大波折时,他前往欧洲,辗转多个国度,心中最为惦念的始终是千里之外的她。志摩的心情很沉重,沉重得透着一股无可抑制的酸软,1928年6月,他以看望老朋友泰戈尔为由,再一次踏上了出国的旅程。这一走,就是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