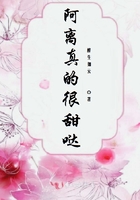停止了一切,像是落入了一个一个冰窖之中,冰冷且静,气氛凝固,只有旁边的小炉子上烧火的噼啪声。
案上的檀香还在燃着,我看见杨坚看我的眼神一沉,无比地悲哀,无比地伤感,亦是无比地绝望。
门外一只云雀的鸣叫打破了这静,蜿蜒地传到屋子里。
我这才蓦然惊醒方才发生了什么,那样的姿势与举动,我当然能感觉出来,他是想要干什么。
杨坚再而瞥了我一眼,我怀疑我是看错了,好像有无数往事明灭着闪过我的眼前,像是跌入了遗落的瞬间。
惶惶然,我心里没由来地慌乱起来,我有些害怕再看见杨坚,有些害怕想起些什么,我连忙离开了案桌,每走一步,我仿佛就更加清醒一分。
萧岿是萧岿,他是萧梁皇室与神族结亲也是可能的,他说的那与他有幼时婚约的未婚妻也许就是我。而杨坚就是杨坚,他与独孤伽罗年少相知,夫妻情深,我脑海中不时忽然出现的那身影一定不是他。
云雀飞走了,一片静默之中,我走到门边,冷了声音,“今日之事,望郡公好生琢磨,晋国公若是亲自来便不是如我这般询问的语气了。”
刚刚说完,在打开房门的一刻,一个通报的声音忽然响起!
——恭迎陛下,晋国公,随国公。
我心中一紧,宇文护居然这时候来了,还把宇文邕一起叫来,这是要干什么?我连忙出了房门,杨坚也眉头一皱,迎了出去。
室外的光有些刺眼,到了院中,只见独孤伽罗已经跪好迎驾,杨丽华也乖乖巧巧地待在母亲身边。
看见宇文邕并未着龙袍,宇文护,杨忠也没有穿官服,都是一身便装,并没有兴师动众的感觉,我心中巨石忽然落了下去。
宇文邕看见我也在这里,有些诧异。
我刚跪下,宇文护就先说了一句。
“阿嫣,你为孤白跑一趟,辛苦了,你起来。”
他根本没有给宇文邕开口的机会,纯粹当皇帝不存在。
宇文护既然叫我阿嫣,那就说明他此来随国公府,是在套近乎的小聚,又把皇帝喊来,是想不费力地就要了宜州布防。
我抬头看着宇文护,笑道:“义父厚爱,为您办事,不辛苦。”
说着,我刚要自己起来,宇文邕居然走了两步过来,也是一副极为关怀的表情,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微微俯身,朝我伸出了手,“嫣儿,起来吧。”
在我没看见的地方,杨坚的表情很是僵硬。
我很快地搭上他的手,他稍稍用力地捏了一下,我明白了,便顺势走到了他身边,微笑点头道:“微臣多谢皇叔。”
宇文邕启声让其他人都起来之后,我又对杨忠行了个礼,杨忠根本不想理我,摆了摆手作罢。
“孤今日来,没其他意思,只想和随公聚聚,恰逢让陛下也出宫透透气。当年在武川,我俩可是并肩作战的同袍啊,哈哈。”宇文护笑里藏刀道。
这时候,他走了两步,经过独孤伽罗的时候,眼里忽然发了狠,故意道:“哦,当年独孤信也是骁勇善战一代名将,没有他,便就没有太祖,没有大周啊。”
闻言,我看见独孤伽罗狠狠地抓住裙角,她抬头,竟是不惧地迎上了宇文护的目光。
三年前,独孤信先是被贬谪,再被宇文护以谋反罪相加赐死。
世家大族中的独孤氏就这样树倒猢狲散,污名至今。
独孤伽罗若不是当时已经嫁给了杨坚,得杨家庇佑,她也便是要承连坐之罪吧。
我看着她,生了敬佩,面对杀父仇人,要以怎样的坚强,强忍住眼里的恨意与痛苦。
我见他们的气氛剑拔弩张,宇文护分明是故意来找茬的,便决定要她解个围。
“义父啊,您看这阳光这般烈,照久了容易搅得人脑子不清醒,说话也不走心。既是叙话,我想我们进屋应是更好的。”
宇文邕看着我,眼神痴迷,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只接了我的话,“堂兄,我觉得嫣儿说得对。”
听他在宇文护面前居然连朕都没有称,心中不禁更觉难受,克制得演成这样,也是难为他了。
“就依阿嫣。”宇文护道,他兀自进了屋,从独孤伽罗旁边离开时还颇为不满地拂了袖。
独孤伽罗是聪明人,她虽不解我为何要这样插话,还是投来了满是感激地目光。
入了席位,宇文护让我坐在了宇文邕身边,虽然是在较高的台子上,可宇文护才是关注的重点。
听他与杨忠又开始说客套话,我便也是细细听着。
这时,我与杨坚的目光接触的那一瞬间,我不由得一颤,很快地移开了眼睛,故作自然地端起了茶。
宇文邕看着我,眸光一冽,直接抬手,我盯着他,他却把我发间的那琼花簪子取了下来,再而放在我的手里。
“萧岿送的?”他低声在我耳边问,又在暗处捏住了我的手。
我猛然想起了姚僧垣的话。
——那小子倒是看起来对你是动了真情,到底是帝王性子深沉,强势霸道,眼里容不得沙子。
我笑盈盈地望着他,担心他一直问萧岿,刨根问底地问得我不好作答,便讨好道:“您若是不喜欢我戴这个,不戴了便是。”
不过,宇文邕的接话我倒是始料未及。
“朕会送你比他这个更好的。”
“什么?”
“长安繁花如何比不上南朝春色了?”他又道。
宇文护的声音忽然打断了对话。
“国师之前与大兴郡公谈论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