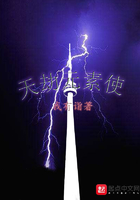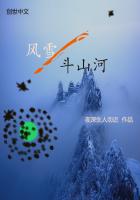到了伦敦,我得到一个口信,要我吃过晚饭尽早去史崔兰太太家。我发现她正和麦克安德鲁上校夫妇在一起。史崔兰太太的姐姐长得和她很像,但面容更灰黄。她长了一副精明强干的模样,好像要把大英帝国都揣进她的口袋里似的。高官的妻子知道她们高人一等,总摆出这副德行。麦克安德鲁太太精神熠熠,有着良好的教养,却几乎掩盖不住她那顽固的偏见:如果你不是军人,倒不如就当个站柜台的。她讨厌近卫团,觉得他们太傲气,并且不屑于谈论他们的妻子,觉得她们出身卑贱。麦克安德鲁上校太太的长裙样式老土,价格却很昂贵。
史崔兰太太显然很紧张。
“嗯,快给我们说说你得到的消息。”她说。
“我见到你丈夫了。恐怕他已决定不回来了。”我停顿了一会儿,“他想画画儿。”
“你什么意思?”史崔兰太太惊叫道。
“你从不知道他很喜欢做那种事吗?”
“他肯定是疯了!”上校嚷道。
史崔兰太太微微皱了皱眉头。她正在她的记忆中搜寻着……
“我记得我们结婚前,他总带着个颜料盒子四处闲逛,可他画的那些东西太难看了。我们经常取笑他。他在这种事上真的没有任何天赋。”
“当然没有啦,这不过是个借口!”麦克安德鲁太太说。
史崔兰太太沉思片刻。她显然对我宣布的这个消息完全摸不着头脑。她把客厅收拾了一下,她那勤俭持家的天性已战胜了她的伤心。她家出事以后,我初次到这里来的时候,屋里有一种荒凉感,就像是带家具出租的房子很久都没有租出去的感觉,而现在这种感觉已经没有了。如今,我在巴黎见过史崔兰了,很难想象他曾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过。我觉得他们几乎不会想到史崔兰身上有些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东西。
“不过,他要是想当画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史崔兰太太终于问道,“我觉得我怎么都不会对那种——那种志向不施以同情的。”
麦克安德鲁太太的嘴唇紧绷着。我想她从来也不赞成她妹妹和搞艺术的人交往。她说“文化”这个词的时候,总是带着一脸鄙夷。
史崔兰太太继续说:
“不管怎么说,如果他有天赋,我会第一个鼓励他的。我不在乎牺牲。和股票经纪人相比,我更愿意嫁给一位画家。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什么也不在乎的。在切尔西住破旧的画室,和住这栋公寓一样,我都会很快乐的。”
“我亲爱的,我受不了你了!”麦克安德鲁太太嚷道,“你不会已经相信了这些鬼话吧?”
“但我觉得真实情况就是这样。”我温和地说。
她又好气又好笑地瞟了我一眼。
“一个40岁的男人,倘若不是为了哪个女人,是不会丢掉生意,抛下妻子和孩子,去当什么画家的。我认为他肯定是遇到了一位你们——艺术界的朋友,她让他神魂颠倒了。”
史崔兰太太苍白的脸颊上突然泛上一层红晕。
“她长什么样?”
我犹豫了一会儿。我知道我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的。
“他没有女人。”
麦克安德鲁上校夫妇脸上露出不愿相信的神情,史崔兰太太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是说,你没见着她?”
“连个鬼也没有。就他一个人。”
“简直是荒唐至极!”麦克安德鲁太太喊道。
“我知道我该亲自去一趟。”上校说,“你放心,我肯定会把那个女人尽快搜出来的!”
“我也希望你去。”我有些尖刻地回答,“你会发现你当初的每一个猜想都是错的。他住的旅馆并不时髦。他住的是一间无比肮脏破烂的小屋。他离家不是享受生活去了。他几乎没什么钱。”
“你觉得他是不是干了什么咱们不知道的事,为了躲避警方抓捕,这才藏起来的?”
这个想法让他们每个人的心中升起一丝希望,但我觉得这纯粹是异想天开。
“要真是这样,他就不会傻到把他的地址给他的合伙人了。”我尖刻地反驳道,“不管怎样,有件事我是确定的,那就是他没有和哪个女人私奔;他没爱上谁。他脑子里根本没想这种事。”
谈话中断了一会儿,他们在思考我说的话。
“好吧,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麦克安德鲁太太最后说,“那么事情并不像我想得那么糟。”
史崔兰太太瞧了她一眼,却没吭声。此时,她的面色非常苍白,秀眉显得很黑,向下垂着。我无法理解她脸上的这种表情。麦克安德鲁太太继续说:
“倘若只是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他迟早会把它丢掉的。”
“你为什么不去找他,艾米?”上校试着说,“你完全可以和他在巴黎住上一年。孩子们我们来管。我敢说他很快就会厌倦,迟早会非常愿意回伦敦来的,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失。”
“我就不会这么做,”麦克安德鲁太太说,“他想要什么样的自由我都会给他。到时候他肯定夹着尾巴回来重新过他的舒服日子。”麦克安德鲁太太冷漠地瞧了妹妹一眼。“或许你有时候并不理解他。男人是奇怪的动物,你得知道如何驾驭他们。”
麦克安德鲁太太和多数女性的看法一样,认为男人把依恋他的女人甩掉是畜生所为,不过倘若男人真的这么做了,主要过错应由女人承担。感情有着理智所解释不了的理由。
史崔兰太太的目光从我们中的这个人身上慢慢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他永远不会回来了。”她说。
“呃,我亲爱的,记住我们刚才说过的话。他已经习惯了舒适的生活,习惯了有个人照顾他。你觉得他能在那家破烂小旅馆的破烂的房间里待多久呢?再说了,他又没什么钱。他肯定会回来的。”
“要是他和哪个女人私奔了,我觉得他还有回来的可能。我不觉得这种事会有什么结果。不出三个月,他就会烦死她了。不过倘若他不是因为爱上了哪个女人走的,一切就全完了。”
“呃,我觉得你说得太深奥了。”上校说。因为职业习惯,他对她这么说感到很莫名其妙,所以就把他全部鄙视都放进“深奥”这个词里头了。“别相信这一套。他会回来的,而且,就像多萝西刚才说的,我觉得他胡搞一阵子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可我不想让他回来。”她说。
“艾米!”
史崔兰太太突然愤怒了,她被气得面色苍白。她现在语速变得很快,中间还伴着微弱的喘息。
“如果他疯狂地爱上了哪个女人,并和她私奔了,我还能原谅他。我觉得这种事挺正常的,我不会太责备他。我会想他是被骗走的。男人心太软,女人又太没有道德,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但并不是这么回事!我恨他!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
麦克安德鲁上校夫妇俩开始一块儿劝她。他们震惊了,都说她疯了。他们都觉得纳闷。绝望中,史崔兰太太将身体转向我。
“你也不明白我的意思吗?”她喊道。
“我不确定。你是说,如果他是为了哪个女人离开你,你还能原谅他,不过倘若他是为了某个理想离开了你,你就不能原谅他了,对不对?你觉得你和前者势均力敌,却无力和后者较量,是不是这样?”
史崔兰太太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我在她的目光中没有看到太多的友好,或许是因为我的话击中了她的要害。她继续用低沉、颤抖的声音说:
“我从未想到我竟能像恨他那样恨一个人。知道吗?我一直在安慰自己。我觉得无论这种事持续多久,到头来他也会需要我的。我知道他临终时会派人来叫我,我也愿意去。我会像母亲那样照顾他,最后还会告诉他,我不在乎这件事,我永远在爱着他,并原谅他所做的一切。”
女人们总热衷于在她们所爱的人的临终床前进行优雅的表演,这种嗜好让我觉得有点儿不舒服。有时候,她们好像嫌弃男人活得太久,推迟了她们上演这动人一幕的机会。
“但现在——现在一切全完了。我看他就像看陌生人那样冷漠。我真希望他穷死,饿死,孤老而终!我真希望他染上恶疾,浑身溃烂!我们之间完了!”
我想不如趁此把史崔兰的建议说出来。
“如果你想和他离婚,他什么都愿意做,以促成此事。”
“我为什么要给他自由?”
“我觉得他并不想要这种自由。他只是觉得这样可能对你更方便些。”
史崔兰太太不耐烦地耸了耸肩。我觉得我对她有点儿失望。当初我还认为人们不像我现在认为的这样差劲,但当我发现这么有魅力的一个女人竟有这么强烈的报复心时,我觉得十分丧气。那时我还不知道人性竟是如此复杂,如今我很清楚了,卑鄙与高贵、恶毒与慈悲、恨与爱都可以在同一颗心中存在。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说些什么,以减轻此刻正在折磨史崔兰太太的那种屈辱感。我觉得还是试试看吧。
“知道吗?我不确定你的丈夫是否应该为他的行为负责。我觉得他已不是他自己了。他好像被某种力量控制,这种力量正在利用他以达到它的目的。他在这种力量的控制下,就像一只投入蜘蛛网里的苍蝇一样无助。似乎有人对他施了妖术。这让我想起了有时会听到的那些奇怪故事:另外一种性格进入一个人的躯体,将原有的性格赶跑了。灵魂并非很安稳地存在于一个人的躯体中,它能够发生神秘的变化。这事儿放在过去,人们会说查尔斯·史崔兰被魔鬼附体了。”
麦克安德鲁太太将她长裙的下摆抚平,胳膊上的金镯子滑落到了手腕上。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事太不可信了!”她尖刻地说,“我不否认,或许艾米对她的丈夫有点儿太放任了。倘若她没有埋头于自身事务,我觉得她不可能觉察不出她丈夫有些不对劲。我觉得,阿莱克将某件心事深埋了一年的时间或者更久,我还没能把它搞得清清楚楚,这种事根本不可能。”
上校目光茫然,我想知道是否有人还能像他那样纯真。
“但这无法改变查尔斯·史崔兰冷酷无情这个事实!”她神情严肃地看着我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为何要抛弃自己的妻子——纯粹是因为自私,再没有其他理由了!”
“这肯定是最简单的解释了。”我说。但我觉得这句话等于没说。后来,我说我累了,便起身告辞,史崔兰太太也没有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