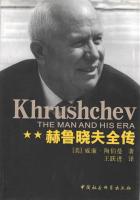范文甫生性刚直,不拘小节,不畏权势,常因他人之事而累及己身,有古侠士风范。
这是范文甫的为人,也时常体现在行医上。
地方富豪、官僚虽不满他的言行,但因信慕他的医术,不仅没有进行干预、遏制,反而以座上宾之礼相待。据《范文虎先生传》载,人称“混世魔王”的“三不知”将军——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的山东督军张宗昌,曾慕名请范文甫出诊。
戒备森严的府第,内外岗哨林立;高贵奢华的卧室,众医肃然环立,唯范文甫不卑不亢,如面对普通病人那样望闻问切,循序渐进地诊视了一遍,然后挥毫处方,谈笑自如,泰然自若。
处方毕,张宗昌拿过来一看,嫌范文甫医案太简单、用药太少。范文甫竟当面嘲讽说:“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
闻者骇然变色,均以目视张,以为张宗昌一定要发作。谁知,张宗昌虽然恼怒,但碍于范文甫医名,且是自己邀请而来,也无可奈何。
1919年,创建于清宣统初年的宁波医学研究会因主持乏人、人员星散而名存实亡,范文甫“起而耆柱之”。以自己的门徒为基础,以邻近的镇海、象山、宁海、奉化和慈溪、余姚等地域的同仁为主,以“加强团结,反对当局非难,激励同仁,研究学术,求发展”为宗旨,重建宁波中医学研究会,自任会长。
1920年,会稽道(俗称宁绍台道,设鄞县城区)道尹黄庆澜公开倡言取缔中医,试图先以考试难倒中医医生,逐步达到取缔、消灭中医的目的。在黄庆澜主导下,宁波警察厅命令辖区内的中医医生集中考试,以考试成绩决定去留。甬地中医界反对声一片,然而无人敢于站出来抗争,范文甫拍案而起,带领医界同仁与警察厅进行辩斗,并针对考试官朱某的命题错误,撰文驳斥。朱某的命题是“《金匮》论痰饮有四,其主治何在?”其实,应该是“《金匮》论饮有四,其痰饮主治何在?”朱某自知理亏,无言对答,宁波警察厅的中医考试就这样不了了之,取缔、消灭中医之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范文甫疾恶如仇,而最看不起的是重财轻医之人。传说,那时候宁波南乡有个土财主李某,平素体健,很少得病。一次生了病,乡下医治无效。听人说,宁波城里有个名医叫范文甫,主诊内科,但疮疡、骨伤、妇儿等各科精通,用药针对性强,多的五六味,少的一二味,服他的一剂药,一般毛病都能痊愈,而且挂号金还比一般医生便宜……听了这一说,李某立马乘夜航船连夜上宁波。在新河头客栈住了一宿,清晨即去范文甫处就诊。
李某怎么也没有想到,找范文甫看病的人竟会有那么多,好不容易轮到自己就诊,可范文甫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一边与人说话,一边察舌、切脉,几句话问过,一张处方就开好了。李某心里很不踏实,既担心范文甫因病情没问清楚误诊,又恐怕范文甫心不在焉投药马虎药不对症,以致花了冤枉钱,但又听别人说范文甫脾气大……思虑再三,还是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范先生,我家住在乡下,来去不大方便,药头能否用得重一点……”
范文甫乜斜了李某一眼,随即挥毫另处一方:石狮子一对,破捣臼两只,石磨一具。然后将两张处方一并交给李某,并叮嘱:“去药店,先用药头重的那一方。”
李某接过处方连声说是,但又问了一句:“范先生,吃了这些药,我的病会好吗?”
范文甫的回答很干脆:“要死的,人迟早是要死的!”
在城里药店买药时,自然也闹出一场笑话。因为李某虽然识字但识不了几个,加上医生书写在处方上的字大有特色,就是满腹经纶之人,也一下子认不清多少,所以尊重范文甫的“医嘱”,先将“药头重”的那一方递交给药店倌……
药店倌不但熟知范文甫为人,还熟悉他的字,大笑一通之后,问清原委,让李某拿出另一张处方。药店倌一边抓药、称药,一边告诉李某:“你呀,既然去范先生处就诊了,你就应该相信他,尊重他。你可能不了解他吧,不过可以放心,这药不会错。”
果然,忐忑不安煎服一剂,病情大减,李某才知药店倌与村人所言均是大实话。
就是因为这一类事例的疯传,还有添油加醋的,久而久之就把这个艺高胆大、医德盖世、秉性耿直的范文甫传成是性情古怪、不通情理、装疯卖傻的“范大糊”。
但是,与上述行为相反,对贫贱之交、贩夫走卒,范文甫深为同情,常倾力相助。其友王崐玉家贫,嫁女无妆奁,范文甫以10天门诊所得予以资助。
一年除夕,风雪交加,范文甫雇了一辆黄包车去澡堂洗澡,因路滑难行,黄包车夫不慎跌了一跤,摔伤了自己的膝盖,也摔疼了范文甫的屁股。
恐怕拿不到车钱,还可能赔偿损失,又加上膝盖的疼痛,黄包车夫坐地仰天号啕大哭。范文甫虽也有伤痛,怀表也摔得破碎,但得悉黄包车车夫的家里尚有老小四口时,不但不责备,而且掏出了身上仅有的5元银元相赠。还免费为黄包车车夫敷药疗伤,直至痊愈。
范文甫为医,收费也不同,诸医要么分文不要,要么狮子大开口。在范文甫为医的年月,宁波中医号金普遍收6角,而范文甫只收4角零6个铜板。又加上,常对贫病者“慷慨解囊,一掷百金而不吝啬,致使家中常无余资……”因而范文甫自奉甚俭,不摆排场,不讲究衣着,终年一身对襟长衫,一顶卷边铜盆帽,一双草编织的芒鞋或鞋前缝起一条硬梁的布做僧鞋……
不过,范文甫的出诊费昂贵。据说,到慈城出诊一次收48元,去上海等地以天数计算,除了出诊费300元外,逗留1天加100元。问起个中原因,范文甫说:“门诊之人,贫病者为多,出诊则多殷实之家。倘非富有,断然不会有如此排场。”
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出诊就如此收费”。
据说,在20世纪20年代,宁波泥水匠、木匠的月收入有七八块银元;上海的技术工人月薪16~24块银元,体力劳动者8~12块银元,大米每担(100斤)3~4块银元,范文甫出诊费的昂贵程度可见一斑。
当然,对于去贫病家庭出诊、急病邀诊自当别论。如当时有一名如今称之为理发师的“剃头佬”,家徒四壁,因劳成疾,范氏获悉后,不但免其出诊金,还赠送人参给以滋补。
从医以来,面对贫病患者,范文甫不但不收医金,还常在处方上加盖自己的印章,嘱病家去特约的药店买药可以不付钱取药,所赊欠的药款由该药店在端午、中秋、岁末之时分三次向范文甫结算,届时往往罄其所有。一些贫且病重不能行动的患者,其家人常常在范文甫必经之路等候,向他诉说病(贫)情,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去诊视。
对此,范文甫不厌其烦,不以为忤,总欣然前往。不但不收出诊费,免费给药,还屡屡回访,直至病愈。
一年除夕,有感而发,范文甫手书对联一副,挂于自家堂屋正中。联曰: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